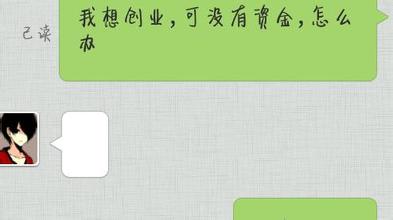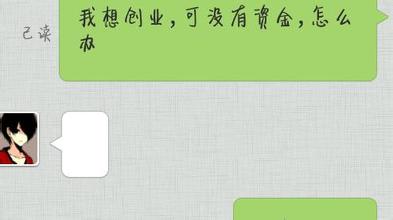1
二十一岁那年的春天,我度过了近三个月的抑郁。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严重到抑郁症的程度,但是每天就是沉浸在专心致志的悲伤里,动不动就哭了出来。
如今想来,当时的生活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变化,全是心底里的迷茫,全是精神上的自苦。
一个刚过二十岁的年轻女孩,最想得到的,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认可和赞同。可我,既达不到导师对我的要求,也不知道漫长的读研生活究竟有何意义。
所有人都跟我说:“你上学早,年龄小,应该继续读博士的。”却没有人问我:“你真正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只知道自己厌倦了所有经济学论文中难懂的数学推理。
一直以来那么喜欢学校的我,竟然想尽了一切办法逃课。
逃课也没什么地方可去,还是背着书包在校园里闲逛,满脑子想的都是——未来该做什么呢?是考博读博还是继续工作?该不该放弃对我来说如此艰难的经济学?我要不要去重读一个中文的学位?我究竟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过的满足又快乐?
这些问题哪里能找到答案。
导师仍然在课堂上讲着我完全听不懂别人却频频点头的理论,其他同学仍然过着好像和我截然不同的目标明确、毫无忧虑的快乐人生。
只有我,像一只被沼泽吞没双脚的人,眼睁睁看着日光大好,却控制不住得下坠。
最沉郁的那几天,我在苏州旅行。那么暖又热烈的春光,那么长又曼妙的清溪,都没能治好我心底的隐疾。
住在山塘街的那一夜,白墙黛瓦的老房子都睡了,星光隐退,月色如醉,多适合与老友倾杯,或者独自安然沉睡。
可我看着远处河岸边摇摇曳曳的灯笼一盏盏熄灭,只觉得我心里的光好像永远都不会再燃起了。
四年之后,我二十五岁了。相比于四年前,我的人生,其实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可能性。让当时的我每天忧心忡忡的各种选择,早已被定格,甚至再也无法更改了。
可我终于学会了好好拥抱自己,享受年轻又热烈的生命。
不再忧心尚未发生的未来,不再遗恨已经定格的过去,而是去寻找当下这一秒的美好。
我是慢慢地度过了那三个月的抑郁。在图书馆找各种心理学的书看,用尽了一切方法自我调节。
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好好写东西了——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了然了自己在阅读和写作中获得的无限快乐。我不再忧虑未来该获得什么专业、什么等级的学位,也不再忧心以后的工作。

那之后,我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写作者。一路写到现在,竟然冥冥之中,走入了自己最喜欢的生活。
回想当年,那个时刻谨记着“别人的意见”,想要达到所有人标准和要求的自己,竟然从未有一秒愿意看看真实的自己。
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自己以后该怎么办。我总是跟他说:“不要去听别人的声音,要去听你内心的声音。如果暂时还听不到,也别害怕慌张。你要继续往前走,多尝试,甚至多摔跤再爬起。你要付出一切真挚去感受一个真实的自己。”
找到真实的自己,找到真正的热爱,比任何“别人的意见”都重要,比任何“别人想要看到的你”都重要。
2
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也是处于焦虑的状态。一方面,我日日抱怨着自己无字可写,另一方面,我像所有的宅女一样,几乎不接触外界任何新鲜的东西,还恼怒生活真是又无聊又没劲啊。
过年无事,我在家里翻看去年的日记,发现那么多周末,纸页上都是空白,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也许昏睡一天,也许刷完了所有综艺节目,却什么都没有留下。
那些空白扎在我心里,不是遗憾,而是可惜——可惜大好时光都被辜负。
所以年后,我才决定再也不要当一个死守在家里的宅女,要尽可能得出走、旅行、认识新的人、体验新的事情。
所以上周末我急急忙忙得飞去了南京。和朋友走在初春的秦淮河畔,河水青绿喜悦,周围路过的姑娘有着惹人注目的花瓣一样清丽饱满的脸颊。
就在坐地铁去机场之前,我还路过了一个当年国民政府官员的旧宅。那个院子如今已无人居住,却变成了一个深沉的诗社。二楼的房间被改造成了免费的图书室,柔软的淡绿色地毯,复古台灯下的灯光映照着窗外碧绿的枇杷叶,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安静得守候着一块文艺的精神角落。
而我回忆起那年四月春光最盛时的苏州城,只觉得自己辜负的不仅是自己,还有这个世界盛装以待的惊喜。
就这样,一步一步,我不仅走出了四年前的抑郁,还走出了一年前的焦虑。
苏州河畔那些曾经熄灭的光,我以为永远不会再亮起的光,一盏一盏地重新亮了起来。
谁能想到呢,我竟然在二十五岁这年,才迎来了最好的时光,并且相信——时光它会越来越好。
那天,朋友问我,你最近过得如何?我想了想,大概只有“完美”二字能够概括吧。话刚说出口,我在心底深处也有点惊讶。
要知道我仍然没有像年少时梦寐以求的那样——读名校,进名企,拿高薪,过着光芒万丈的人生。可是我竟然第一次觉得生活充满安宁和喜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