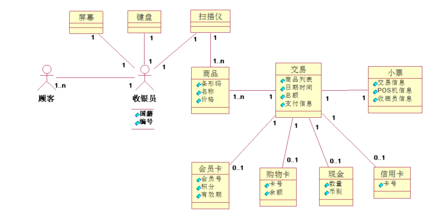全球就业形势告急的今天,或许从古今中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兼职史里,你能找到一些让自己发光的启示。当然,前提是你得是金子,而且还要够硬。
马尔克斯说的一个段子:1971年,聂鲁达在巴黎,听某个可靠的朋友透露,说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先生那年67岁了,离过世还有两年,当然不能像年轻人进洞房,猴急跳脚脸火烫。他很沉稳,只是遍请巴黎的诸位朋友吃饭。人问他理由,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消息出来,诸位恍然大悟,纷道恭喜。其中一位问:“那你颁奖词准备说啥?”聂先生一拍脑袋:“高兴忘了!”扯过张菜单,翻个面,就用他招牌的绿墨水开始写起来。
但这故事讲得开,前提是聂先生在巴黎。他在巴黎干嘛呢?工作,在大使馆上班。实际上,他老人家是外交官。他那些得了诺贝尔奖的诗,全是业余时间写的。
如你所知,中国文化人有这传统:本行是济世救民,业余就风流挥洒。比如孔圣人当过饲养员,当过鲁国官员,也当过老师,学生把课堂笔记一抄就是《论语》。屈原主业是楚国的公务员,业余写诗。唐朝的诗歌,若非私人抒情,便是酬答赠送之用。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们,都是一边当国家干部,一边顺手写诗、作文、画画。所以,曹操的诗,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和花鸟画,李后主的词,天启皇帝的木工活儿,康熙皇帝的拉丁文和几何学,听上去一点都不奇怪:当皇帝也得有个业余爱好不是?
而且中国人思维里,有这么回事:唐朝之后,读书人都兼有儒家和道家双属性。当了公务员,有了铁饭碗,就是儒家,济世救民。没当上公务员,不被天子待见,就决定披发入山,云烟深处去。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如此:做着好官,念叨归农,自号个什么斋主人,什么居山人,还写厚厚的诗集出来印,就是想来分富贵风流,两厢占尽。
欧洲人也兼职,但比起中国读书人来,更现实点。实话说就是,欧洲人得琢磨生活问题。古希腊诸位大贤能玩学问,是有一比四的公民与奴隶数据对比放着,不愁没人伺候;中世纪搞文艺的,若非教会养着,就是大富豪。所以,许多知识分子只好一边谋生,一边偷空创作。19世纪之前的音乐人,都得连创作带演出。巴赫在莱比锡做乐长时候,每个星期得写25分钟的新曲子,还得亲自抄谱,到周末亲自夯起管风琴来演出。19世纪的诸位也是能者多劳:门德尔松得做教师,李斯特得绕世界钢巡回,马勒的主业是指挥。真得等放了假,他们几位才有时间搞创作。俄罗斯大作曲家鲍罗丁,本行是医院院长,又是化学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处理罢,才能写曲子去。
写东西的诸位,兼职的更多。艾略特先生写20世纪最伟大诗作《荒原》的时候,本身是个银行职员。村上春树写处女作小说后来获得群像新人奖的作品《且听风吟》时,是在自家经营的爵士酒吧下班后。纳博科夫20世纪40年代在康奈尔教书,为了养家,曾经一口气开四门课,里面居然包括网球课,实在没时间,只好趁假期出去捉蝴蝶,又逢下雨时,在汽车里写著名的《洛丽塔》。当然,上班累一天,下班写伟大作品,这日子没法持久。海明威说艾略特当时在银行困得甚为痛苦,但没名没钱之前,就是不敢辞职;当时在巴黎的庞德,虽然诗稿卖不出去,穷得想去当翻译算了,但还是伙同诸友捐款,“把庞德从银行拯救出来!”村上春树写完自己第二部小说就把酒吧关了专心写作;纳博科夫一等《洛丽塔》畅销就辞职跑去瑞士,皆此类也。
最神奇的兼职是这样子:16世纪初,教皇让米开朗琪罗做壁画。米开朗琪罗说自己是雕塑家,不会画画给自己雕塑打的草稿不算。教皇不听,逼他画,激起了米开朗琪罗的牛性,花四年画了不朽的西斯廷天顶图,39米乘以13米的巨画,都是个“不会画画”的人完成的。实际上,米开朗琪罗并不爱这玩意,终其一生都在唠叨:“那些逼我完成的画,摧毁了我完成真正作品的时间”,以及,“描绘景物的工作,是给那些没能力描绘人物的家伙准备的”。换句话说,他老人家一辈子画的那些巨作包括西斯廷天顶图这样的不朽作品都是在他创作雕塑的间隙,愤愤不平,兼职完成的。
最后一个故事。

马尔克斯早年在哥伦比亚当记者。白天工作,晚上去一个下等妓女睡的大车店歇宿,乘隙写小说。到他而立之年被报纸解聘后,他先在巴黎,然后去墨西哥。在墨西哥时,他已经写完了五部小说全是工作之余写的只有一部出版了,印了千余册。很多年后,他回顾那段生涯,说过这么句话:“如果你会觉得自己总想做什么,却嫌被工作压抑,没时间……好吧,也许你对那件事的爱,还不大足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