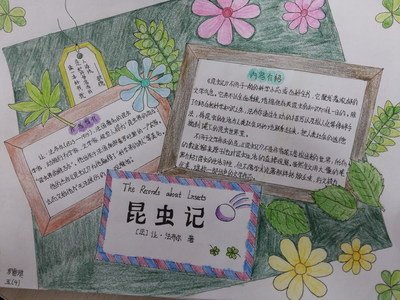《东京塔》以淡雅而又真实感人的笔触,抒发了对母亲的深切追忆,在日本一上市就成为超级畅销书,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00万册。
《东京塔》的人气之所以如此高涨。与它“哭泣小说”的身份密不可分。小说从“我”一点点长大,一直写到“我”目送着母亲因病去世,各种生活细节每每令人感同身受,因而赚取了读者的大把眼泪,也当之无愧地成“哭泣小说”的首席代表。
眼下在日本各大书店,“哭泣小说”大受读者的追捧,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更是将书中“流泪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大脑”的观点奉为时尚。
作者简介
利利·弗兰克,本名中川雅也,1963年生于福冈,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集作家、绘本作者、插画家、美术指导、词曲作家、摄影师等种种职业于一身,活跃于艺术节与文学界。主演电视剧《嫌疑人X的献身》、《龙马传》等。《东京塔》是他的首部自传体小说,用优美的文笔、深挚的情感讲述他坎坷的成长经历和与母亲相依相偎的一生,是感人的亲情故事,连续三年荣登日本各大畅销排行榜榜首,并获得多项文学大奖,几乎人手一本,被日本读者奉为过敏小说。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和电视剧,也获得众多奖项。作者因此一跃成为日本最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名人及读者点评
这就是东京:这就是吃饭、这就是医院、这就是死亡。在淡淡地进行当中,描写妈妈以及妈妈生命节奏的语言在书中跳舞。妈妈、我、爸爸。爸爸一出现的话,情况就有点混乱。一过,这个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最后才能称得上是“家族”。
——青山书屋中心 六本木店 间室道子
我为书中构建的强烈的母子亲情所感动,在不顺利的家庭关系日益增多的今天,这种执著于亲情关系的凄美令人垂泪。我迫切地产生赶快生一个孩子的心愿。
——公司职员 36岁 女
父母和儿子三个人呈现出三位一体的东京塔以有生与死,一部超级哭泣的作品。
——店员 河内清美
我哭了,在开往公司的东海道线上,眼泪不止地往下流。因为泪流不止,结果我迟到了一个小时,利利·弗兰克,你不能这样地让我哭泣啊!
——公司职员 30岁 男
这部小部中的人物有:爸爸、妈妈和我。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亲情关系,呈现给我们神奇的勇气。塑造了一个幽默而且有男人味的新形象以及家庭关系的形象。一部杰作。
——bookstore谈浜松町店 小材绫吾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那是迟早发生的事情。你会产生一种恐怖,明白了这些事情发生的恐怖。我最恐惧的事情。”我很认同这句话。对我来说,那的确是最恐怖的事情。那些事情总有一天会真正到来。我一边读,一边独自大哭。擦眼泪和算涕的面巾纸都塞满了垃圾箱。读第二遍的时候,仍旧哭泣不止。读完以后,心情豁然开朗。
——模特 田边由美
本小说的美文美句有很多,我都折页,统计下来有相当的量。很是钦佩作者温和的目光,和背后敏锐的洞察力。这是一部主题性和文学性都很强的小说。是具有口口相传价值的作品。
——纪伊国屋书店新宿南店 白井惠美子
读者书评
之前我说过,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有两位,川端康成与村上春树。今天我介绍一位在我看来不算有名,但是其作品深深打动我的人——中川雅也(笔名:利利·弗兰克)
中川雅也,1964年11月4日,毕业于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日本作家,绘本作家、插图画家、美术指导、作词作曲家、策划演出家、DJ、摄影师,也是位时尚创意人,在日本各大电视台及报纸都有专栏。拥有不同的身份和头衔,超越不同领域的壁垒,而活跃其中。代表作《东京塔》。
《东京塔》以淡雅而又真实感人的笔触,抒发了对母亲的深切追忆,在日本一上市就成为超级畅销书,荣获2006年日本书店大奖,日本全国书店店员评选出的最想卖的一本书,日本富士电视台将其改编成电视剧,2007年松冈锭司导演将其拍成电影,由小田切让、松隆子等出演。
小说的一个卖点是——哭泣。中川的文字很平淡,但具有极强的感情色彩。其实文中所描写的情节都是生活中平凡人所能经历到的,平凡的事,平凡人,却成为本书最精彩的内容。作者以一种自传的形式,描写自己从小到大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与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联系。看完这本书,足够让人觉得人情的温暖,理解什么是亲人的爱,明白作为子女的,如何爱自己的父母,如何共同维护一个完整的家庭,与亲人的幸福,胜过世上所有。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同名电影,搜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是小田切让演的,因为还有一部与其同名的《东京塔》是源孝志导演的爱情片,另外还可以关注下同名的日本电视剧。可以买到书的童鞋那是最好的,因为看书最能感受到那种情感的冲击。
读者书评——利利·弗兰克的人生
这并不完全是一本讲母子之情的书。而是作者借主人公叙述自己的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来完成某些情感表达的过程。不管是对于母亲的,对于父亲的,还是对于自己的。
当我细细的往下读时,不期然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主人公的叠加起来。渐渐感觉自己心里面的某些东西正在逐渐的剥离破碎。我很急切的继续读下去妄图通过作者的详细的近乎真实的叙述找到自己人生轨迹上所面临困惑的答案。虽然我没能最后找到我要的,但是看完全书后我仍然得到了一个。
人生中很多事是你在想珍惜的时候已经不能珍惜,能做到的时候却没有去做,不想错过的也不知不觉地错过…然而人生就这么回事啊。没有人总能在需要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需要珍惜的人和情感也总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冲动而没有好好珍惜。
突然想起麦兜的一句话,“原来火鸡的味道最美味的时候就是在将吃而未吃的那个时候,之后剩下的,就只是吃火鸡而已。”当很久之后不得不把无法吃完而剩下的火鸡倒入垃圾桶时,我又听到某些东西,某些细碎的情感逐渐剥离、破碎的声响。这种感觉麦兜在以后的人生中某些与圣诞无关的日子偶尔回想起来只有两次:一次是在自己结婚的时候;另一次是在麦太火化的时候。
“我很后悔让妈妈扔掉那些鸡……”麦兜这句话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说的。
人生是多么错综复杂而且无法把握的事情啊。不管是东京塔里的“我”,还是麦兜里的“我”,都有着会失去悔恨的东西,都有着几乎所有人都拥有的不会是完美的人生。这很像现实中的我们自己,入到社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好的事,坏的事,然后长大,然后丢失忘却很多东西,再长大。美好的东西注定无法永远拥有,所以我们才会长大成熟成人。成人后才会因为失去未珍惜而痛苦流涕。
这过程会很苦很苦,因为我们现在能体会在成人之前得到的美好太多太多,所以不要害怕。
最后,唯一一句书评:这是一本很有力量的书。
精彩书摘
那种感觉宛若陀螺的芯一般执著地刺入正中央。
在东京的中心。
在日本的中心。
我们憧憬的中心。
就像一股奇妙的离心力,从旋转的中心延伸开来。
偶尔,那些闲暇下来的神们从空中垂下双手,像弹簧丝一样层层地旋转着。
执著地,一圈圈地打转,我们也在旋转着。
我们来了,就好像聚集在院灯周围的蚊虫一般,狂热地迷恋不曾见过的光明,贪婪地吸附它。
乘着颠簸的列车,我从故乡心驰神往地来到这里。
一个飞奔的人。
一个被吞噬的人。
一个遭排斥的人。
一个眩晕的人。
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只是朝着那力量的方向行进,然后听天由命。
伤心欲绝抑或是后悔得肠子都青了的事情,都不知为何难以抵抗,只能持续地重复着。
人生就像陀螺一样。
不停地打转,旋转着,重复着。

就这样,被拽拖着,被叩击着。我们燃烧殆尽。
生命狼藉不堪。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他一边凝视着东京塔,一边说好像很荒凉的样子。
它只是装饰了白天,照亮了黑夜。他说其样子看起来很荒凉。
我听了,心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令人更加憧憬的。
这个空荡荡的城市,一点点地长大,继续着凛冽的自然形态,给人以强悍和柔美之感。
流动、拉拢、勾结、背叛以及欺骗着生活下去的我们,对那种孤独的凄美充满兴趣和欲望。
不能忍受寂寞,执著坚守的我们对之憧憬着、向往着。
每一个人都向往着这个地方,为之离开家乡,投入她的怀抱,追求生命中的某种东西。
离乡背井的父亲曾经为此带着我一起来到这里。失去归所的我们,没有抱有任何幻想,来到东京,不知何处是归宿,只能在东京塔下睡觉。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租住的能望见东京塔的小屋里,相拥而眠。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多数人几乎已经记不起孩提时代的事情了,可是我却一直保留着很多记忆。那些记忆并不暧昧,也绝非模糊,儿时空气中的味道、当时的所思所想,甚至是零碎的风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估计是因为比起别人来,我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少了吧。
这是三岁之前的记忆。我和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生活的记忆。家人一起生活三年的时间里,除了上面写的那些,就没有其他的了。我只能继续记忆着这微乎其微的童年逸事了。
“咔嚓”一声凄厉,和妈妈一起睡在蒲团上的我被惊醒了。当然,妈妈也醒了,在蒲团上弓着身子。这可是半夜时间,不仅仅是孩子,大人和街道都在沉睡中。
从大门口,传来奶奶悲戚戚的声音。奶奶连连呼喊着妈妈的名字。妈妈飞奔至走廊里,来到门口,又立即跑回房间,抱起我,像个橄榄球选手迅速跑出房间。
爸爸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今天并不是用手推开大门,而是用脚踹开的。镶嵌着玻璃的木栈格子门破乱不堪,一片狼藉。奶奶穿着鞋子走在走廊里,声嘶力竭地尖叫着。妈妈冲过奶奶面前,爸爸要追赶逃跑的妈妈。即便是调查笼城事件的特种警察部队也不会让他们变得文明优雅。
一边是想要逃之夭夭的妈妈,一边是趴在走廊里的奶奶,类似这样的“回家风景”在我的家里时常上演。不过,那天的猎物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奶奶,而是我。爸爸硬从蜷缩在角落里的妈妈那里把我夺过来,从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三角油纸包。油纸里包着的是冰凉的烧鸡,给我吃的,带着钎子他就往我嘴里塞。
爸爸想要让我这个儿子吃烧鸡。刚刚起来就有烧鸡吃,在我的人生中也就那唯一一次了。
爸爸当时喝多了,耍酒疯,到处发狂。
几天以后,我家又新装了大门。我家的门是两扇合在一起的拉门,只是把爸爸弄坏了的那一扇装上新的,那扇新门的木栈发白,我家的大门显得很奇怪。
我是个哭鼻虫,每次一哭都长泣不止。爸爸很不喜欢这样的男孩子,尽管那时候我还只有三岁。
有一次我哭着来到茶厅,爸爸穿着衬裤在看电视,他不知道我在那里哭了多久。突然爸爸就怒吼着,把我拎起来,扔了出去。于是我从茶厅横穿走廊,落进了客厅。
我仿佛漂浮在宇宙里,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着走廊和客厅的交界处。奶奶从客厅里看到了这一切,像棒球接球手一样,双手把从茶厅里被投掷出去的我接住了。
这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漂浮在宇宙中的记忆消失了。跳楼自杀的人在撞击地面之前,思维瞬间停滞也许就是那样的。如果当时奶奶接“人”失误的话,我将被摔在地上,也许就变成一个傻瓜孩子了。
我还是一个肠胃不好,很虚弱的孩子,经常拉肚子。每到犯病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附近的医院。给我看病的是个女医生,后来妈妈总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夫,如果没有她,你就死了。”每次去医院,就是往屁股上打针,女医生和妈妈就鼓励我,“忍耐一些,别哭。”我就装做不疼的样子,沉醉于她们两个人的表扬当中。
有一天,我又跟往常一样肚子痛,妈妈带我去女医生的医院,不巧那天是休诊日,就去了另一家私人医院。这家医院诊断为“一般的腹痛”。我接受了手腕注射,不停地哼哼唧唧地啜泣着。
那天晚上,甚至到了第二天,我的肚子还是痛。后来我痛得满地打滚,于是妈妈又一次把我带到那个女医生那里。结果那个医生把妈妈批了一顿,问:“为什么不早点送过来?!”然后马上帮我们写了一封给市立医院的介绍信。就这样,我马上被送到了另一家医院。
我的腹痛原来是肠梗阻造成的,而且情况似乎比较危险。几个内科、外科的大夫一起进了手术室。具体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一种通上电的灌肠药样的东西从肛门灌到我的身体里。我想不管兴趣爱好怎么特殊,也不会有人灌过这种带电的灌肠药。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承受这样的痛苦。
大夫们用仪器监测灌肠药流到了肠子的什么部位。如果药中途停在肠子的某个部位,那接下来就要切开肚子,取出肠子,然后把患处摘除掉。
不过手术前大夫曾解释说,如果必须切除一部分肠子,很可能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障碍,希望我的父母做好心理准备。
后来听妈妈说,她当时曾凝视着手术室的小窗户,祈祷通电的灌肠药能畅通无阻地流过我的肠子。而爸爸则跟我出生的时候一样,是在酒馆喝酒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中途跑过来的。不过那次他倒是跟妈妈一起守在监视器旁,观察着灌肠药在我肠子里的动向。
幸运的是灌肠药顺利地流过了我的肠子。这样一来,通电的灌肠药打通了我肠子中堵塞的地方,所以我就不用做剖腹手术了。据说妈妈当时高兴得哭了起来,而爸爸只是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就继续回酒馆喝酒去了。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我因为疼痛而满地打滚时闻到家里榻榻米的气味,看到了墙壁的颜色,还有妈妈那忧心忡忡的表情。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当时并不在身边。
除此之外我还能记起的,是有一次爸爸正在画画时的背影。当时爸爸把玻璃棒放到圆规叉开的两只脚中间,正在用毛笔或者鸭嘴笔画线。他好像在设计什么东西。我们家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爸爸以前画的几幅石像。当时我站在旁边看着爸爸画画,于是爸爸把装着蓝色颜料的陶质碟子和毛笔递给我,让我在一张废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在画画的时候,爸爸嘴里好像发出了“咦”“啊”之类的声音。画画时的爸爸让我感到很亲切。
这些就是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事情了,是我三岁之前发生的、还能清楚想起的几件小事。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我为什么连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不过这些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时的回忆了,是全部的回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
我出生在福冈县一个叫小仓的城市,据说我是在紫河沿岸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每当我和妈妈走在那条河的河岸时,妈妈就会指着那家医院,对我说:“你就是在那儿生下来的。”
现在,小仓的单轨电车往来穿梭,不过那时候只有有轨电车行驶在市区里。当时附近的八幡有新日本制铁公司下属的一家大型炼铁厂,现在没有以前热闹了。当时街道上人很多,很有生气。炼铁厂里竖着高高的烟囱,有长的,有短的,白色、灰色的烟从各种形状的烟囱里往上冒。这些烟囱的对面有一个小型的港口,常常有小型蒸汽船浮在水面上。
到了我手里有教科书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提到原子弹爆炸的事。
“其实落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本来是准备投到小仓的,准备投到八幡的那家炼铁厂。不过那天小仓的天气不好,是个阴天,在飞机上看不到下面的道路。所以飞机飞到了附近的长崎,在那儿投下了那颗原子弹,可能是长崎有造船厂吧。那天小仓要是晴天的话,可能就没你了。”
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可是每次听到妈妈的话,我都会这样想:天气好还是不好,就因为这点小事,就决定投不投原子弹,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太任性、太浑蛋了。
妈妈的一个叔叔住在长崎,我曾经有好几次在暑假去他家玩。叔外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一直到最后一次,他都是躺在床上。叔外公虽然身体残废了,却很开朗,经常给我吃带壳的海胆。
不过妈妈老是这样对我说:“你叔外公都是因为原子弹爆炸才变成这样的,真可怜啊。”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感到很痛苦,好像本来应该是我遭遇的不幸,最后却发生在了叔外公的身上。
现在小仓的市里已经看不到有轨电车了,那家大型炼铁厂,以及并排的那些烟囱也都不见了。炼铁厂的那块土地上现在建了一座主题公园,好笑的是据说里面展览了美国的航天火箭。
我们家离市区很近,附近有一个游乐园。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栋木制的两层楼房,是我的祖父盖的。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和外公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从来没感受过祖父、外公的疼爱。我知道的祖父仅限于佛龛上放着的一张遗照。
爸爸、妈妈、我还有奶奶,以及爸爸的妹妹敦子姑姑住在祖父盖的这幢房子里。祖父去世以后,这幢房子开始出租给人住。附近牙医大学的几个学生租了二层的四个房间,每天的早饭和晚饭也由我们家提供。我想那个时候每顿饭肯定都很热闹吧。租房子的那几个大学生经常哄我玩,敦子姑姑也会给我买那个时候时兴的一些东西,如法式面包、西式糕点店的冰激淋,所以我很亲近他们。不过后来敦子姑姑跟其中的一个大学生结了婚,离开了这栋房子。
妈妈嫁到这个家之后,过了一年生了我。妈妈比爸爸要大,在日本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5年),这样的新娘子很少见,而且妈妈还是晚婚。结婚的时候妈妈三十一岁,爸爸二十七岁。
生于小仓的爸爸曾经在当地上过高中,不过因为品行恶劣,到二年级的时候怎么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祖父把他从那所高中转到了东京的一所高中。当时爸爸只是想去东京看看新鲜,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可是祖父却考虑到爸爸去趟东京之后,经历些人世的艰辛,可能会变得成熟点。不过祖父想得有些天真了,殊不知品行如果刚开始就不好的话,那以后是改不了的。
爸爸进了一所东京的高中,后来自动升进那所高中隶属的大学。不过独自生活、无人看管的爸爸经常逃课,净想着干坏事,不久就从大学退学了。可能是受那时期所结识的一个艺术学校大学生的影响,爸爸从大学退学之后,进了一所专门学习“帽子设计”的职业学校。
不过像爸爸这种干不成正事的人,即使进了那所学校,结果肯定也跟以前一样。
爸爸进了那所学校没过多久,热情就冷却了,然后就腻了,放弃了。不必多说,他肯定没能从那所学校毕业。不过我很奇怪爸爸当时为什么会学习帽子的设计。虽然我跟他在一块儿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不过也算接触了近四十年,这四十年里我没看到他戴过一次帽子,他也从未对我戴的帽子做过任何评价。我很怀疑爸爸当初是不是对帽子一点都不感兴趣。
爸爸上了很多学校,然后不停地退学。在那之后他就成了匹无笼头的马,游手好闲,酗酒、行窃,什么都干,甚至还染上过性病。在跟一个朋友一起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爸爸突然喜欢上了石佛。不过他的这种喜欢好像并不是看到木雕佛像那种大慈大悲,然后洗心革面,被引导到佛教道路上。
后来爸爸徒步去各地参拜石佛,并且把这些石佛画了下来。当时兴起了一股“印度热”,所以爸爸不断地去各处流浪,画了很多素描。他一边筹划着移民到印度,一面跟朋友创了一份同人报纸,同时继续酩酊大醉。边讲述自己的精神世界边冥想,可能爸爸日日夜夜就在重复这两件事吧。就在他快成为东京的一个废人时,接到了爷爷的讣告。
结果爸爸被强行送回了九州。
爸爸回到家乡之后,开始到当地的一家报社工作。这个工作是托爷爷的门路得来的。不过虽说有门路,可是连爸爸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品行也能进报社,由此可见昭和时期的关系威力真是非比寻常。
“我在此之前一直在东京耽于玩乐,生活颓废。不知不觉中双亲和长辈都上了年纪,而且疾病缠身,我自己也都到了二十好几。这次我因故回到故乡小仓,回到这片故土,得到了诸位的照顾,使我能够就职于这家报社。从今以后我一定不辜负诸位的好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坚持不懈,三年、五年、十年,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我要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
爸爸那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他这种人做什么事都不成,所以很自然地不久就从那家报社辞职了。我们可以看到爸爸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了多久,马上就会放弃。后来奶奶好几次说到爸爸的工作,每次都是目光迷离、满是感慨地说:“那个时候你要是不从报社辞职,现在也肯定功成名就了。你为什么要辞职呢?真是让人懊恼死了。”
妈妈出生于筑丰市的一个煤炭镇子上,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家里开个布庄。据说妈妈从当地的高中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想想,我对妈妈高中毕业到结婚之间的这十年一点都不了解。甚至她那段时间是一直待在家里,还是到了别的地方我都不清楚。
不过妈妈曾经给我看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对妈妈的那段生活产生了一些猜想。
那张照片已经褪色了,变成深棕色。照片上的妈妈穿着一条连衣裙,白色的,上面有水珠图案。妈妈的头上包着围巾,戴着一副太阳镜。她坐在一辆白色敞篷赛车的发动机罩上,一只手的两根手指之间夹着一支烟,摆了一个姿势。
妈妈年轻时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
妈妈这个人很喜欢跟人交往,经常微笑,喜欢快乐的事。她经常为周围的人考虑,喜欢做家务,是个很规规矩矩的人。
而爸爸正好相反,他性子很急,不苟言笑,也从不慌张。总之爸爸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对西装和朋友倒是很认真,对其他的就极其马虎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