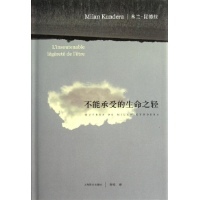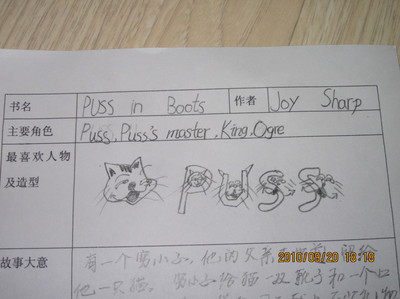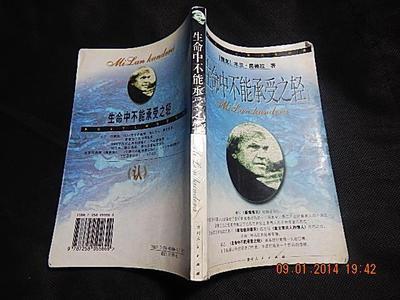青春照相馆是一间照相馆,照相馆的主人是我以前的男朋友宋冬野。必须要说的是,和那个胖胖憨憨的歌唱家没有一厘钱关系。不过的确,他也很胖很憨厚。
爱华配图
说起来已经很久了,好几年前我开始学习拍照。那时候还在学校,平时没有课的时候就和几个朋友跑到学校附近那栋已经停工很久了的烂尾楼去拍水泥墙面和杂草丛生的工地,从前的我们,潜意识里面那是在考证一座城市某一段的繁荣兴衰,而等到很久以后,当我们回首,再翻看那些一直被存储在相机里舍不得删除的旧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无论哪一张,记录的都只是在一栋再平常不过的废弃建筑物底下满脸傻笑的我们,那表情简直像是发现了某个被埋葬多年的宝藏一样。细细想来,倒也真算是青春的记忆,即使在我们长大了的今天再说起来的时候连路人都觉得矫情,尽管那些照片作为珍藏记忆的方式,像个小孩子一样不依不饶地将这份情感保留了下来,且等到多年以后我们再拿出来时将它放大。
想起儿时被父母拉去照相馆拍照,一个人站在镜头前,等待着那一声“咔擦——”想起的瞬间,拍照师傅说小朋友头往右偏一点,胸再挺一点的时候,很怪,心里冥冥中有个直觉在说,以后站在那个小小的取景框前喊一二三的人会是我。
应该是2008年,当时还在我们老家一个小城市上中学的我偶然一次在POCO网上遇见了当时还生活在北京学习摄影专业的文艺青年宋冬野,我作为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还没去大城市以前,被他晒在网上的一堆北京奥运会的照片给深深吸引住,那些构成了我们最初对彼此生活有印象的照片,后来一一被这个死胖子用他那丰富多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想象力加以了改造,他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P在那些有他的照片里,他说这样就像我们注定要携起手一起走过我们的人生。
2010年,我去北京,到的那天,他来接的我。我跟着一大群从全国各地涌向京城来的人一起,提着比自己体重多几倍重量的行李,匆匆忙忙地走出蚂蚁窝一般的火车站。我眼尖,看到在出站口不远的一个麦当劳餐厅门口站着一个戴着圆圆墨镜、穿了粉红色T恤的胖子,我二话没说走过去,站到他面前,说了声你好,当然初次见面,我还是很礼貌性地在“你好”前面加了“帅哥”两字。
那天来接我的除了宋冬野,还有他一个朋友,叫李志。自然也不是唱民谣的那个李志。
接下来的四年间,我们从相逢、相识、相知到相爱,这其中,我们从各自的学校里搬出来住到了一起,我们约好每一个双休的下午,在四号线的安河桥北站见面,他拉着我的手穿过人车川流不息的马路。
每一次被他肥厚的手掌拉住的时候,我都想很不客气地说一句,死胖子,不能减减肥啊。
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多余的钱,有时候为了改善伙食就去路边的苍蝇馆子多叫两个菜,我们住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我们从各自的生活费里拿一小部分出来交每个月的房租。
老宋平时最大的兴趣就是喜欢游走于城市里的角角落落,拍下那些即将消失建筑的外观,他说废墟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尽管更多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种力量是什么,在我们活着的现实生活里找不找得到实际的案例。
他将那些他称之为“心灵影像”的照片投给一些杂志社,有时候会收到一笔稿费,便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去下顿馆子。
有一次李志问他,胖子,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谁知他先是有半分钟没有说话,端起眼前桌上的杯子将里面的酒一干而尽,说,现在都没顾好,谈什么以后,想多了。
李志说,是人总得有一点计划吧。
老宋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句话。
我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老宋像是看出来点什么,就搂搂我的肩膀,说,我觉得现在就挺好啊,美酒和佳人相伴,夫复何求啊。
说完他便兀自地笑了,反而留我和李志两个在桌上不好意思,不知道说什么来缓解气氛。
我没好气地狠狠捏了他一把,死胖子,给我正经点。
我们攒钱去长途旅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住青年旅舍,过着太过悠闲的生活。我们在异乡的郊外行走,站在路边招手搭顺风车。我们在陌生小旅馆的房间里席地交谈,拥抱,亲吻,相拥而眠。很多文艺青年做过的事我们也不例外,一一地在我们那前程未知却又满腔热情的路上像个疯子一样不知疲倦的奔驰着。
最远的一次,我们去了尼泊尔。坐在舷窗的位置,望出去,云层上的雪山群一望无际,目及之处,莫不如此。我从没见过那么壮丽的景观,天地之间,凯凯雪原漫向天边,让人会有一种以为自己到了天堂的错觉。我不禁想,在这宛如童话世界里的场景里,那些山谷里,是否真的有像童话故事里所描述的一样,迷路的小鹿在山林深处被小木屋的老奶奶收留,平安的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抑或是专在雪天里出现的大脚怪,结局是遇上了英勇的取它性命的猎人。彼时我方才理解,什么叫做旅行的意义。
在加德满都的小镇,我们和同行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十天的时间。
那是从我们2010年相遇开始,走过的所有地方,装满了好几张存储卡,持续了整整四年的照片日记。我将它们放到网络上,让很多很多人看到了我们的故事,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热心的回复,其中难免不乏因为宋冬野这个名字而向我发来讯息询问的人。回头来看,它的确像一部长长的纪录片,以照片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一路上走过的风景,我们的喜怒哀乐。后来看到这个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讨论着,他们在留言里对我说,谢谢你和你的宋冬野,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走下去,继续你们的照片日记,你们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在任何时候不管有多糟,但仍有很美好的一面。说实话,有时候,看得多了那些陌生的鼓励,连我自己也慢慢变得开始沉醉于其中,像我和老宋这样,乍看之下文艺青年们的爱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了。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和续写着相同的剧本,并也从未怀疑过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真实。即使我们更多时候要面对的,远比照片里那份单纯的美好要多得多。
2014年8月28日,距我毕业刚好两个月,我们分手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进行不下去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从前心心念念的现在变得不想了。我说我从不相信什么细节打败一切、励志故事之类的话,也因为我生来就不相信,于是就没有。
那天我回我们的出租小屋收拾东西,在此之前我认真听取了身边一些朋友对失恋的建议,所以我在打包行李的时候,除了我的衣物和一些必要的东西,凡是能让我在今后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带走,曾经那些登刊过他拍摄的照片我负责文字撰写的杂志;网络上我们共同的博客;去某个旅游地好不容易淘回来的纪念品,以及过去我们通过的每一封E-mail,全部,所有。该扔的扔,该删的删。老宋甚至还为此和我大吵一架,他说没必要做得那么决绝,不管做了什么,但你否定不了那些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事实。但其实我丝毫没有想过去否定它,就像在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台词多年以后想起来我依然记忆如初:如果想要根除记忆,就将你来过的路再走一遍,新的印象就会代替那些让你不敢触及的旧的印象,你就好了。不管它是否在现实里得到具体的印证,但我就笃定的相信了,我甚至就做了那句话的信徒,在我们分手后不久,我又去了四川,云南,广西,厦门,上海,香港……去了尼泊尔,彻底地将我们来时的路再走过一遍。
离开北京的时候,李志送的我,老宋要来,我没让。没有什么多余的离别的话,我不想把气氛搞得太过浮夸。
我对李志说,你回去告诉胖子,让他减点肥,别成天没事一出门就戴个墨镜在脸上装什么独立艺术家,搞得自己像个明星一样。
李志笑笑,哈哈,死胖子,这么些年,不知说了他多少回了,就是改不了。
分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我某天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一个名叫“青春照相馆”的博客,我点进去,赫然间发现这个博客里的所有照片,都是我和宋冬野以前在一起时候的照片,尽是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于是我迅速翻到博主的ID,果然,也是我们以前的。是时我坐在电脑面前,看着那些照片发呆,我曾经费心费力地去编辑那些照片,上传到网上,为我们的故事随心所欲地添加一个我自己觉得美好的结尾。
那时我也像现在一样,坐在一间由昏黄的瓦丝灯泡照着的房间写这篇东西。之前有一两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把照片里的故事拉长,写成一本心灵治愈系的故事,我拒绝了邀约,大概也是我从那之后再也未完整的翻过属于我们的文字和图片。记忆对我来说,也许不过就像从前拍拍过的那些烂尾楼,它见证了我生命中的浓重,自然也会见证生命的让步。
就现在,让我首先想起的是,是我们在快要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我曾偷偷跑去当地的跳骚市场,在一个手工店买下来一本尚可算作精致的相册,后来那本相册一直放在老宋那里,到现在也是。里面每一页都贴了一张从我们相遇开始到最后一次旅行结束时所拍的照片,其中的每一张,都是被我那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从一大堆照片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那有指可数的一些照片并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作品,但却是能让我们彼此产生共鸣的画面的寄主。
那本相册的第一页,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的那天,傍晚来临之前的黄昏。我们坐在火车站旁边的麦当劳,当然一起的还有李志。点了三份儿童套餐,想起来都好笑,老宋和李志两个举起加了很多冰的可乐杯子和我轻轻地碰了碰杯,说,北京欢迎你。

第二页,是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安河桥北站。这里着实见证了我们太多,和无数对小情侣一样,我们手拉着手,唱着只有我们自己听得懂时不时会招来异样眼光的歌,一起走进马路对面一家我们常常会去那里改善自己伙食的路边馆子,老板一看是这两个人,也不拿菜单便问,今天来点什么。
第三页,在云南。我们整日都绕着洱海边上环行骑车,照片里的我们笑得像花儿一样,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双手环住他水桶似的腰,他对着镜头做鬼脸,露出他一排整齐的白得像泡过漂白水的牙齿。后来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有一段没有路灯,我心里害怕得要命,只知道牢牢抓着他宽大结实的手臂。
第四页,在我学校的教学楼下,他一个人抱着吉他。在那照片之前还有一张,是我很生气,气得整个脸都变成了猪肝色,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提到分手,因为我们不清楚为了什么而在一起,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是否有共同的未来。那天这死胖子不知道去哪里找来一把吉他,老土的在教学楼下唱起了五音不全版的莫文蔚的《宝贝》。那张照片是当时班里的同学被他奇异的歌声统统吸引到窗边,啪啪啪啪一阵手机快门的闪光拍下来的。
第五页,是他一个人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厦门去。晚上十二点左右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突然不想回来了,随后我在电话里又哭又骂,骂着骂着听见“噔—”的一声,电话挂断了,再打过去就不通了。次日一早收到他发来的延时的E-mail,邮件里说,台风来了,我想回来了。
第六七八页,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当时刚刚上了各大娱乐报纸头条的某某摇滚歌手唱了一首和这里并没有多大实际关系的歌曲。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共同的信仰,我们背着相机神游在街道上,拍下那些让自己觉得感动的时刻,记录自己的旅行故事。
第九页,我在老家的生日。清早醒来正打算和母亲一道出门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我去车站接他,飞机之后再转汽车,一路风尘仆仆,他说不管怎么样,有多远,你的生日还是要来的。那时他站在我面前,我想他是懂我的。
最后一页,是一部经典影片中的画面。被太多人称赞过的《廊桥遗梦》。电影中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在分别的几年之后,偶然一次在街上的超市门口短暂的一瞥,男主人公强忍着奔上前去相认的冲动,漫天的雨成了他们再次诀别的泪。
……
当那天我再次看到那个博客,底下有很多人留言评论,有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像中国的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甚至还有人说你们就是中国版的杰克和罗丝。我笑笑,还是匿名在底下回复了一条,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最终还是各自上路,杰克和罗丝到底给我们留下了《我心永恒》。当然这些名字,无论哪个,都代表了幸福,记载了传奇,创造了神话,远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故事能承担得起的。
况且就算是传奇,也终会有被遗忘的一天。再深刻的记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淡去,照片会褪色。然而当你日后因为某个曾经似曾相似的细微动作,或是零星片段,再想起来,那么我们就是默默地跟着岁月在自己的人生中匍匐前进,我们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
2014年10月28日,这天,老宋在北京某个胡同旁边的“青春照相馆”正式开业。李志告诉我,我们的那些照片中的场景,被这死胖子说要拿去做前去照相的客人所拍的照片里的背景。问我可不可以,但是我无法回答,照片、回忆和现实,究竟哪一个更适合一些,于是我说,随便吧,都行。
亲爱的正走在路上的人们,如果有幸被您看到了这篇文章,我是“青春照相馆”的主人,如果您某一天在北京的某条街上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一间叫做“青春照相馆”的照相馆,希望您能走进去,替我向他说一声,宋胖子,其实我也有一点儿想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