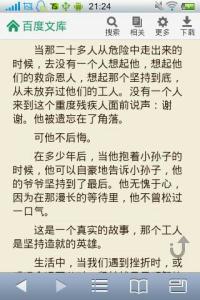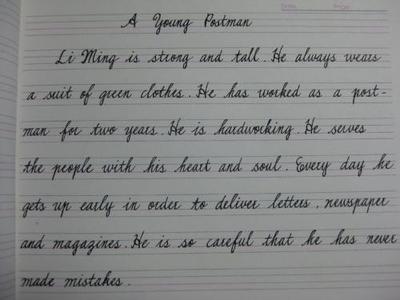还记得么,那条波光粼粼的河。
河很清,映着快乐的你我;船很小,也只能容下你和我。木船随波逐流,载着你我,还有那段记忆。第一次相识的场景,已被我一一拾起镌刻在心上,只要心仍在跳动,便一刻不能忘记。记得河水汩汩流淌着的清脆,欢畅的声响;记得温软的阳光在水面碎裂成晶莹、细碎的波浪,河畔摇曳的翠绿的芦苇,还有船头美丽、羞涩的你。记得棉软的风送来河水的湿润,麦田的香甜,还有对面的你散发着的淡淡木槿花香。整个心都醉了、碎了,不是因为清澈的,欢畅的声响;不是因为晶莹细碎的浪;不是因为河水的湿润,麦田的清香,只因为对面的你,我心爱的姑娘。
还记得么,对岸那座鬼屋。
那是一直想去但家人不允许你去的地方。那里,每片台阶上应当还印着我们细碎的足迹,每间破败的房间中应当还荡漾着你我快乐的笑声。还记得那场不期的雨么,细细密密织起的帘,笼罩着鬼屋,笼罩着河畔摇曳的芦苇,也笼罩着我们归去的路。那遗失的木船,在雨帘中隐了又现了。这与似秋晨的雾,朦胧又迷茫。我相信,这一切应当是上天刻意的安排,丢失了木船,让你我困在河边一隅。
还记得么,我背着你拨开一帘又一帘凌乱的雨。雨很凉,风很狂,但我的心似乎燃起了熊熊炭火,很暖。是肩膀上的你,为我点然心中那团雨水浸湿的柴草。是你,让暴虐的雨成了船桨上激起的水滴,闪烁着清凉;是你,让肆虐的风成了苇尖细碎的阳光,闪耀着温暖;是你,让我不再惧怕所谓暴虐的雨,肆虐的风。是你让我明白我的宿命:幻化出一双宽大的羽翼,为你挡风,遮雨。那天风很大,雨很烈,但我们却很幸福。这剧烈的幸福,如同这场不期而至的雨,一帘又一帘。
还记得么,瓜田边支起的草屋。
雨依旧下着,屋檐上坠着晶莹的雨珠,一颗一颗滴落在瓜田上,绽开一朵朵泥土的芬芳。西瓜次第躺在湿软的土地上,像一个个安睡的精灵,他们在等待着,等待喝饱最后一口雨水。不会忘记那座茅草屋,就如同忘不掉那西瓜的甘甜。我脱下衬衣拧干给你,然后一旁静静看你拭去额头些许雨滴。你对着我笑了,那么开心;我也笑了,那般幸福。多希望屋檐的雨滴一直坠在那,不要落下;多希此刻的时间停滞,让我多看一眼你的笑容;多希望……
还记得么,我为你捉的萤火虫。
雨后入夜的池水冰凉,我挽起裤腿,在池边的枝桠上为你捉起一只绿莹莹的精灵。它不停的在我掌心跳跃,就如同我此刻心口跳跃的心。我手捧着绿色精灵递给你,连同我跳跃的心。
美好就如同落日的余霞,绽开的再绚烂,再赤红如血,依旧抵挡不住黑夜的降临。
分别,你我的眼眸中开出的是难舍的苦涩。望着你远去的背影被整个黑夜吞噬。我久久矗立在原处,像一尊冰冷的雕塑。脖上悬着你送我的项链,在风中摇摆,像枝桠上那片即将坠落的叶。
篇二:眠辗转反侧,脑海里充塞着浓密的黑暗。眼睛和心都倦了,却也滑不进哪怕只清清浅浅的睡意。越是渴望睡着,越是睡意全消。事事又偏偏开始浮上脑际,枝枝叶叶向着四面八方纵横蔓延。这种时刻宁愿只是聆听时钟镌刻时间的声音,只是静静凝望黑暗一点点变浓,再一点点变淡。
很久没有紧贴着心搜刮出什么。也许深深浅浅的快乐与忧伤在那儿仍旧是片片剥落着。
是在逃避吗?我想这恰恰是一种面对吧。是一种避开所有人,独独直视赤条条不加任何遮掩的自己的面对。但其实有时候,心像被一只略带冷意的手轻轻握着,微痛却警醒。
一言不发地盯住过往与黑暗,白眼珠上浮现的红色血管也清晰可见了吧。如同唱针划过唱片的声槽,思绪清清楚楚划过某些故事的细节——历历都还深刻着的就是那些终不如过眼云烟,风过即散的存在。那些存在,躲躲闪闪却又纠纠缠缠。
那些存在就像未曾时时感觉得到却又像须臾不曾停止的呼吸一样真实。那些存在不在身边扩展,却悄悄在心里深厚。那些存在就像雨水从天而降,细细密密地落在我的头发上,手心里,打湿我的眼睛。
不再是一团可以随意揉捏的黏土,让每一种新的体验留下痕迹。不再是黑白分明在眼中,绝无调和之地。但并不是没有精精致致的傲慢,只是不敢用心地的干净去挑战世界的浑浊了。所以浑身上下置身事外的抽离感多的是。淡然,淡漠,淡到让那些存在崩溃的声音在耳朵里不断回响。
习惯面具一般缺乏表情的脸。不是喜欢,只是习惯,只是任性的习惯,只是放纵自己任性的习惯。如此而已。只是,平静背后,也会有满心的屈辱,震惊,迷茫,绝望。所以每每也都期待能有一种淡,稳住我几乎泛滥的感触。它当是滤掉一切杂质后的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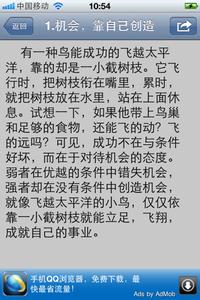
清晰吗?世界总在我不知晓的地方发生着变化,直至无可挽回。
眠——眠心,再眠眼。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