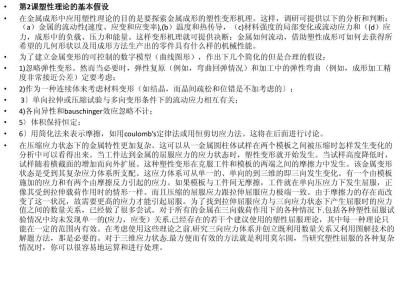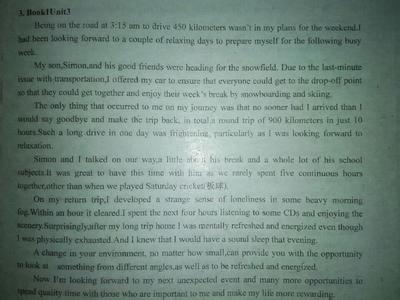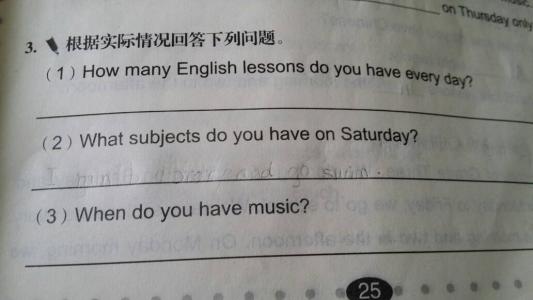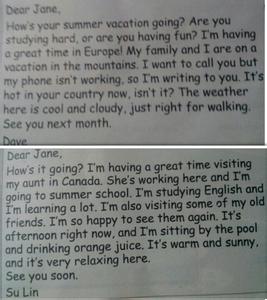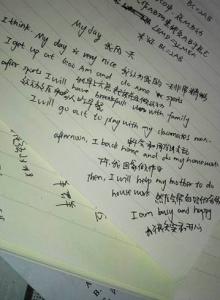随着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发展,英语正跻身为一种国际语言被广泛使用。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大学英语文章翻译,欢迎阅读!
大学英语精读第三版第三册课文翻译第四单元一位球迷的评论 比尔·普拉施基
这封电子邮件在某些方面与我收到的其他刻薄的信件相似。它痛斥我对洛杉矶道奇队的评论,并争辩说我把一切全都搞错了。然而,这个评论与其他的评论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同。
与通常那些“你是个白痴”的评论不同的是,这一评论含有更多的细节。它包含了该队比赛表现的关键数据。写这篇评论的人对洛杉矶道奇队的了解绝不亚于我自认为对它的了解。 而且这一评论是署名的。作者的名字叫萨拉·莫里斯。
我被深深打动,于是给她回信。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封信引出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来往。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两年来,我一直经营着我的道奇队网站。你是怎么成为一个棒球评论专栏作家的?这可是我的梦。
这是萨拉的第二封电子邮件,它的到来一点也不意外。我每次对人微笑一下,人家就向我要一份工作。但是另一个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信的最后一行字里的拼写错误,是关于“我的梦”那一部分。
也许萨拉就是一个打字很糟糕的人。但也许她真的是在寻找某个目标,但就是一字之差,还没有找着。
这就值得再回她一封信,于是我让她解释。
我今年30岁。„„因为我身有残疾,花了5年的时间才读完大专拿到文凭。„„在棒球赛季,我每个星期平均花55小时写球赛报道,写评论,做研究,听比赛或者看比赛。
萨拉称她的网站为“道奇地”。我搜索了一下,什么也没有找着。后来我重读她的电子邮件, 发现在她的电子邮件最底下挂了一个地址我点击该地址。网站并不花哨。但是她以一个作家的严肃态度对该队进行了详细报道。不过,我还是不禁要问,有人读吗?
从来没有人在我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我一个月收到一封信。
所以,这里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妇女,她对道奇队的报道之广泛不亚于美国任何一个记者, 可
她却在为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写作,网站的名字很怪很难记,读者大概有两个人。 我想她那个梦所缺的远远不只是拼写里头少了一个字母r。
我建起了自己的网站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不过运气不佳。因为我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最高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8个字,可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的脑子挺好使,我对工作非常专注。这才是人们成功的关键。
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
我问她要用多少时间写她那通常为400字的文章。
三到四小时。
我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做过的事情。
我让萨拉·莫里斯给我打电话。
我说话有障碍,无法使用电话。.
这就证明了我的怀疑。这显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一位所谓女性作家很可能是一个45岁的男性管子工。
我决定结束与此人的通信。可就在那时我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残疾是脑瘫。„„它影响肌肉神经的控制。„„当我的脑子告诉我的手去敲击字键时, 我会挪动我的腿,碰击桌子,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碰击六个其他的字键。
当我的母亲解释我的残疾时,她告诉我说,如果我比别人努力三倍,我就可以成就我要做的任何事情。.
她写道,她在帕萨迪拉长大的时候成了道奇队的球迷。她上布莱尔高级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校少年棒球队的教练叫她去做球队的统计员。她做了,用的是一个打字机和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
她说由于她跟棒球结了缘,她才得以留在学校里,尽管她成绩不好,每天还有数小时的令她脖子酸痛的家庭作业。
棒球给了我努力的目标 „„我可以做别的孩子做不了的事情 „„我想为给了我这么多的棒球做一点事情。
不错,我就这么相信了她。有几分信吧。在像她所称的那种情况下,有谁能没有最好的设备和帮助而报道一个棒球队呢?我很好奇,所以我问她我能不能开车过去看她。 她同意了,并详细告诉我路怎么走,其中提到乡下的泥路和没有名字的街道。
我开车向东驶去,穿过得克萨斯的荒凉地带。在一条蜿蜒曲折布满小动物大小的坑洼的泥路上,我看到了样子像旧工具棚的屋子。
但这不是一个工具棚,这是一所房子,一个被高高的杂草和废弃物包围的正在朽烂的小棚屋。 是不是这个地方呢?
一位身着旧T恤衫和裙子的妇女从棚屋里走了出来。
“我是萨拉的母亲,”洛伊·莫里斯一边说一边用她那粗糙的手握着我光滑的手。“她在等你呢。”
我从太阳光下走进去,打开一扇破烂的屏门,走进了阴暗的棚子,棚子里蜷缩在轮椅上的是一个87磅重的躯体。
她的四肢扭了一扭。她的头转了一转。我们无法拥抱,甚至也无法握手。她只能张大眼睛看我,向我微笑。可她那微笑里充满了光芒!它穿透了由破烂的木地板、旧躺椅和结满蜘蛛网的窗户围起来的黑暗空间。
我不忍心看别的任何东西,所以我的眼睛只盯住她那微笑,它是那么清晰,那么自信, 它甚至令我的多数怀疑一扫而光。但我还是要问,这就是莎拉·莫里斯吗?

她开始在轮椅里摇晃,嘴里发出声音。我以为她在咳嗽。
可实际上,她是在说话。她的母亲为她翻译。“我要给你看点东西。”萨拉说。
洛伊把她推到搭在煤灰砖上的一张旧书桌前。桌子上放着一台计算机。计算机旁是一台电视机。她的母亲将一根小棒绑在她女儿的太阳穴上。
萨拉趴在计算机上,用绑在她头上的棍子调出道奇地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她开始一啄一啄地在这篇报道上添字加句。
她抬起头看我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低头看她,心里充满了惊奇──还有羞愧。 这真的就是萨拉·莫里斯。 这个伟大的萨拉·莫里斯。
几个月前我与萨拉·莫里斯联系的时候是想跟她干一仗。现在看着她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吃力地打着字写一篇或许根本没有人看的文章,我明白了这一仗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这一仗不是跟萨拉打,而是跟自己打。这一仗和体育界在现今玩世不恭的年代里每天都在经历的一模一样。那就是要相信运动员仍然可以是英雄的搏斗。
在一个远离这种怀疑的地方,一个心智充满神奇的萨拉·莫里斯帮我找回了信任。
大学英语精读第三版第三册课文翻译第五单元妈哭的那天
在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天,我放学回家,心中充满了期待。我腋下夹着一期新的我最爱看的体育杂志,再者9家里没有别人打扰我。爹在上班,妹不在家。妈刚找到新工作,还得过一个小时才下班。我跳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嗒一声打开电灯。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妈双手捂着脸,身子紧缩成一团,坐在长沙发的那一端哭泣着。我见妈哭这还是第一次。
我小心地向她走去,轻轻拍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啦?”
妈深深吸了一口气,强作微笑。“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我这份新工作要丢了。我字打得不够快。”
“可你上班才3天,”我说。“你会熟练起来的。”我这是在重复她讲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或做一件与自己关系重大的事情而遇到因难时,她总是这样跟我说的。
“不成,”妈黯然神伤地说。“过去我总是讲,只要我下决心,什么事都能干成。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多数的事我都能做。但打字这件事我干不了啦。”
我感到无能为力,而且十分尴尬。我虽然1 6岁了,但仍然以为妈什么都能千。几年前,当我们卖掉农场,搬到城里住的时候,妈决定开办日托所。她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她写信要求参加幼托函授课程,学习了6个月就正式获得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不久她的日托所招生额满,而且还有不少小孩登记等着入托呢。我觉得凭妈的能力,办成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无论是托儿所或是我父母后来购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收入供我妹妹和我上大学。两年后就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了。再过3年,妹妹也要上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妈拼命想办法积蓄钱。很清楚,爹已尽了最大努力——除了一份全日工作之外,还耕种了80英亩地。
我们卖了汽车旅馆没几个月,妈搬回来一台旧打字机。这架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吃晚饭时,我把这台机器说成是“废物一件”。
“我们只买得起这样旧的,”妈说。“学打字用是够可以的了。”从那天起,餐桌一收拾9盘子一洗,妈马上到她的缝纫间去练习。有几天,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妈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奇,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妈却欣喜万分。
星期一,妈第一天上班回来,我发觉妈的高兴劲儿已经烟消云散。妈绷着脸,看上去很疲劳,
我没对她作任何表示。
星期二,爹做晚饭,收拾厨房。妈呆在缝纫间练习打字。“妈还好吗?”我问爹。
“妈打字碰到丁点因难,”他说,“她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在家里多帮一丁点忙,她会很感激的。”
“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马上警觉起来,说道。
“我知道你做得不少,”爹心平气和地说。“说不定你还得再多干一丁点。你要记住,她现在工作主要是为了能供你上大学。”
老实说,上不上大学我并不在乎。我真希望妈一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星期三,当发现妈哭时我所感到的震惊和窘迫,完全表明了我对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不理解。我坐在她的身旁,慢慢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们都不免有失败的时候,”妈平静地说。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也感觉到她在极方抑制着由于我闯进来而被打断的强烈情感的发泄。突然,我心里一酸,伸开双臂,把妈搂在怀里。
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贴着我的肩膀,抽泣着。我紧紧抱着她,没有说话。我明白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和我所能做的,这就够了。妈非常激动,我感到她的背在颤抖。就在那一时刻,我第一次明白妈也有弱J点。她还是我的妈,但又不仅如此: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会害怕,会受到伤害,会遭到失败。我感觉到她的痛苦,就像我千百次在她怀里寻求安慰时,她感到我的痛苦一样。
一周过后9妈找到一个卖纺织品的工作,工资只有原先电台的一半。“这是一个我能胜任的工作,”她简单地说道。但在晚上,她继续在那台绿色的1日打字机上练习。如今,每当我在夜晚走过她的房门前,听着她那一刻不停的嗒、嗒的打字声时,我的感情与过去迥然不同了。我深知,在那个房间里进行着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上大学时,妈找到一份薪金比原来高但责任也比原来重的办公室工作。使我不得不相信的是,妈不可思议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竟与我所学到的一样多。因为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自豪地受聘担任报纸记者时,她已在我们家乡的报社里当了6个月的记者了。
那台绿色旧打字机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修理过。它是一件纪念品。但它所勾起的我的回忆与妈的不尽相同。每当我写文章遇到因难想打退堂鼓时,或是自叹不走运时,我就往那台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像妈当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打着。这时,我回忆起的不是妈的失败9而是她的勇气,她那一往无前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