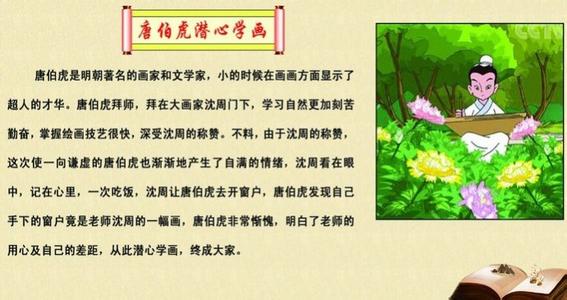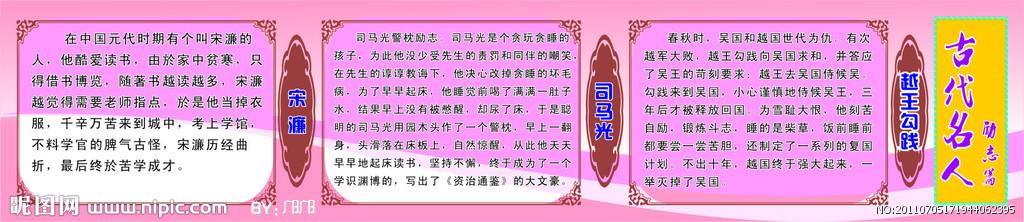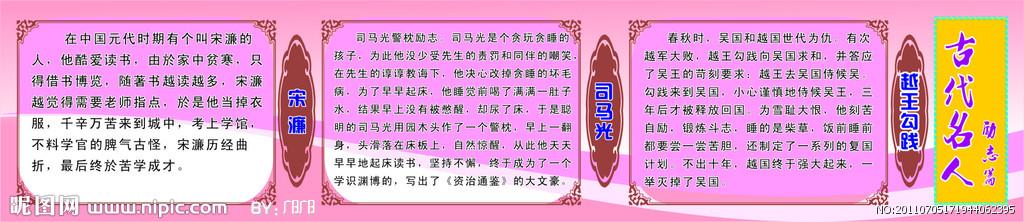有很多关于名人的经典励志故事都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花时间去品读的,那么关于名人的经典励志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名人的经典励志故事:玩摇滚的好学生
作者:大鹏
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连我爸爸妈妈都很惊讶,因为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忙着开饭店,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他们也没太为我操心,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差。
初中的时候,我是全班的前三名,到了高中,成绩也稳定维持在前十名左右。
只有让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成绩很好的“好学生”,老师和家长才会给你空间,才会让你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我在弹琴唱歌这件事情上就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如果硬要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合适的平台展示自己。那时候,学校很少组织文艺活动,我有技艺在身同学们却看不到,让我很没成就感。
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在集安市举办一场演唱会!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学姐,她叫钱环宇,那一年我高一,她高二。
钱环宇听了我的想法很兴奋,她愿意帮我,不过前提是她要参与演出。她决定去少年宫学架子鼓,因为只有架子鼓是初学者可以短时间内学成的乐器,而且顺其自然地,我们在演出时可以从少年宫借一套架子鼓出来。她说:“我马上就上高三了,再也没有这么多的业余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妨组建一支乐队,演唱会结束以后就解散,也算给高中生涯添些亮点。”
哪有一支乐队组建的目的就是解散呢?有,就是我和钱环宇组建的这支。我们俩给乐队起名叫“见证乐队”,也给那场演唱会起了一个名字——“告别的见证”。
见证乐队的第三位乐手是一个弹电子琴的小女孩儿,她是隔壁班的。我和钱环宇打听了很多人,才找到一个自己家有电子琴,而且会弹,关键是家长还不会反对的人。我们还缺一位贝司手,我想起了我表叔,他已经从吉林农大毕业回到集安政府工作了,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我说:“那正好,忘了吉他吧。恭喜你,你现在是贝司手了。”
乐手凑齐了,我开始借乐器,我让我妈帮我去她以前的单位——评剧团——问问能不能外借一些电声乐器。那时候评剧团已经倒闭了,一些老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在各种婚礼和开业典礼上助兴。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位叔叔,他领我来到一个仓库,里面果然躺着一把受伤的电吉他和一把电贝司。叔叔说评剧团买了这些电声乐器,还没有开始排练,剧团就倒闭了,他现在把它们借给我,要我好好地用。
人和乐器都齐了,我们开始排练,就在钱环宇学架子鼓的教室里,每个周末都练。大家都没有乐队演出的经验,所以一开始进度非常缓慢,但是随着每个人对自己手中乐器的熟悉,乐趣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几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合奏十几首歌曲了,大部分都是Beyond的,我是主唱。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唱出了自己的理想,台下的观众伸着脖子看我,就好像当年我妈唱评剧时那样。我终于明白了那是怎样一种感受——很幸福,幸福到唱着唱着自己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很想流泪。
我看到站在角落里的父母,他们事先并没有说过要来;我还看到了我的班主任,她那天格外漂亮;还有评剧团借给我吉他的叔叔,肩上扛着他的孩子,眼里分明也有泪光。最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听,到后来变成全场大合唱,直到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人们还不肯离去。我们的同学、朋友、不认识的人,陆续上台唱了几首歌,我们的乐队伴奏,一片狂欢,我甚至都忘了那场“告别的见证”演唱会到底是怎么结束的了。
那场演出除去成本,我们还赚了几十块钱。几个乐手在附近下馆子,我第一次喝了酒。第二天乐队就解散了。那时候没有录像,关于那场演出的一切被我封存在一个档案袋里,里面有海报和门票的设计稿、我们的排练单、我们演出时的照片,还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我写的字条。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那是我的第一支乐队,不成熟,但是无与伦比。
关于名人的经典励志故事:吴宓的大度
作者:张勇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夏,钱钟书清华即将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1938年钱钟书从欧洲返国,西南联大正式延聘他为外文系正教授,这在当时是破格聘用,因为他只有28岁。如此礼遇可谓厚矣。但钱在西南联大并不愉快,只教了一年即离开了。他离开时曾扬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久,好事之人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他笑着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在吴宓的眼里同辈人文史学问最出色的当属陈寅恪,而钱钟书则是晚生中的翘楚。所以,吴宓以自己的爱才惜才之心,包容了弟子的狂妄和傲慢。
后来钱钟书分别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西洋文学。在这期间,恩师吴宓痴狂地爱上了32岁的美貌才女毛彦文,并幻想享有齐人拥有一妻一妾之艳福,遭到了好友陈寅恪等的极力反对。为此,陈寅恪还曾集杜甫的文句和李商隐的诗句为联,巧妙地嵌进“雨生”(吴宓之字)二字,打趣此事,其语为:“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几经周折,痴情的吴宓还是不惜与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可是当决定娶毛氏为妻时,毛彦文却嫁给了六十六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绮梦破灭后的吴宓依然痴心不改,为毛彦文写下了大量的情诗。远在海外游学的钱钟书特撰文一篇,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刻薄地调侃恩师的“梦中情人”为“Superannuated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1937年,钱钟书还将题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寄给吴宓,并在附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还这样描述老师:“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这些带有嘲讽的语句深深刺伤了吴宓,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自己的弟子在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coquette”。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吴宓自然伤心至极,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
1940年春,钱钟书从国外学成回国。许多知名学府想聘请他,这其中包括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可是,陈福田、杜公超竭力反对。吴宓得知此事后,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2年后,钱钟书辞职他就。在钱钟书离去之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了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多年后,钱钟书的学术、人格日趋成熟。一次,他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毫无芥蒂,师生两人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饮酒品茗。钱钟书内心深责,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宓淡然一笑:“哈哈,我早已忘之。”
1993年春,钱钟书忽然接到了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希望他能够为其父新书《吴宓日记》写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钟书读完恩师的日记后,心内慨然,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他在《吴宓日记》一书的序中,还恭歉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