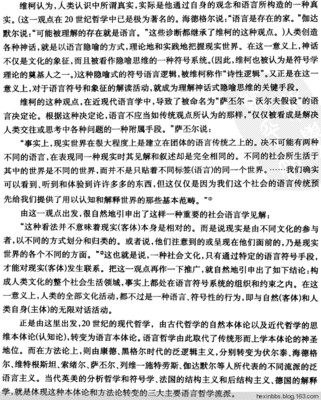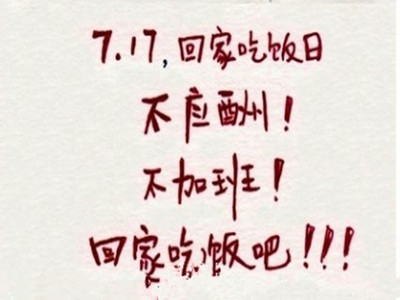哲学社会科学是尺量人类整体生存在宇宙时空中的意义的工具。是尺量指引国家文明进步道路的工具。以下是由小编整理关于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范围
同样,其它学系的学生若选修哲学课程或副修哲学,对其专业的研习亦将大有裨益。因为从深层次的角度来探讨,可以说,几乎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会引发出一些哲学问题,故哲学与很多其它学术领域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领域都有一些与之相关的但又非其直接研究的课题——例如该领域的概念及理论的基本性质为何的问题。这些课题却往往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举例说,有些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关的问题——如科学理论和我们眼见的世界的关系为何?——其本身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正好是科学哲学所探讨的。同样,政治哲学考察各种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法律哲学研究法律的性质与理论基础;美学则探讨品美的基础和提供理解文学和艺术的框架。再者,由于任何学科都需要应用推理和证成的准则,所以逻辑和知识论这两个哲学的领域与所有学科都有密切关连。
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发展
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是学术管理部门使用的概念,在当时体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是现代科学共同体使用的学术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学科分类意识的体现。这两个概念指称的对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场域的概念双轨现象就产生了。这种概念双轨现象是不同场域内部不同逻辑运作的结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场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场域实现他场域的异地统治会产生概念的场域危机,从而引发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但学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生态混乱的情形是到了历史反思的时候了。概念生态的混乱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双轨现象,也没有概念意识。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对于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问题,陈达夫说:“对于当下的思想与民众自由而言,确切地讲,在暴力占据绝对权后,自从掌握了金钱货币化的策略,人们就开始远离真理,社会从此走向深渊。”对此,他强调说:“明显禁锢思维能力的文科教学内容方面,必须在引入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全面添加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思想,必须首先建立符合历史与国情的独立的基本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内局限
主要体现在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等方面。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据郭沫若介绍:“‘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细读郭沫若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
由于1955年的苏联科学院实行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国的学部制,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学者的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只是这个学科模式在30年代的苏联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将这个学科模式体制化,到1955年成立学部时才具有可能性。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制度模仿并没有直接的体制继承关系。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陈伯达等人取消,而其他学部得以保留。后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及生物学、地学部两个学部分成了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文革”中被取消,但中国的文科总得有一个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就是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当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机构不再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而是直接叫“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体现了对“文革”中以教条化的哲学统治科学的一个反思与批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说明当时执政部门决心改正错误,逐步实现学术管理的科学化。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个时候,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设立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一个体制机构虽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看出体制与体制概念的不同社会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