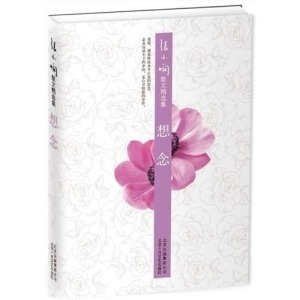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天空,洁白的光芒洒向大地,仿佛给大地洒上一层银粉。清风吹来,池塘泛起阵阵涟漪,依依的柳枝被风轻轻地拂动着……乡村的夜色是多么宁静多么美丽啊!下面是小编给大家精选的在乡村散文集,供大家欣赏。
在乡村散文集精选:儿时贫穷的记忆
说起来很奇怪,明明小时候很贫穷,没有一样从商店购买的玩具,没有每天可以吃早餐的零花钱,甚至于,衣服都是穿的又旧又大哥哥或者某个亲戚的,内心却感觉不到贫穷的酸涩和苦痛,仿佛都不曾那么穷过。
春节里能有一套新衣服穿,那是件开心的事情。很多时候,小小的心里也会带着那么一种期盼,但如果期盼落空好像也不特别觉得伤感。因为大家都是那般的贫穷。江汉平原主要的农作物是棉花和水稻,棉花和水稻都是镇上的国营单位在收购,从家里用两轮板车拉到7.5公里外的镇上卖给他们的时候,并不能当场拿到全部现金。一部分货款直接抵掉了土地税(那个时候种田需要缴税),另一部分可以兑换成油票(我们当地做菜主要的食用油是棉籽油,偶尔调料会使用芝麻油,就是香油),剩余的部分才发放现金。能让老百姓靠种田就生活富足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所以结余其实并不多。况且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加上哥哥姐姐我,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压力其实不小。
现代社会环境,有一种笑贫不笑娼的趋势,不知道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我们舍弃了人性深处的本真。事实上,我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值得取笑。前一件通过勤劳可以改善,后一件没有受害主体。社会主流媒体应该引导我们寻找生命的真相,人性的释放,真理的彰显。可惜的是,这一切没有发生,甚至有所扭曲。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没有伴随着精神层次的提升。
通常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在休闲。秋天收割了小麦之后种下的油菜,整个冬天都不需要打理,所以农田可以撒手不管。那个时期,承包责任制单干还不太久,家家都不太富裕,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来临,下海这个词还没有诞生新的含义。农村人喜欢打麻将打扑克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如果打麻将打扑克用来输赢人民币,算违法,被公安民警抓住了需要没收赌资,罚款甚至判刑。
可能是我血液里流淌着一种赌性。不好意思地说,如今,我深爱的一种扑克游戏:德州扑克,一段时间里,我曾幻想着它能成为未来的职业,每天能坐在电脑前面,通过互联网和世界各地的德州扑克玩家竞技赢钱,不断的计算胜率赔率隐含赔率,选择放弃或是跟注还是加注。国内好的职业德州扑克牌手年收入十分可观,10万美元不在话下。
春节那样的氛围里,我们当地会有一种赌博形式:色盅。色盅组织起来很快,道具也很简单,所以较为流行。就是使用两颗色子,色子是一个正立方体,有6个面,1点,2点,到6点。使用色盅,农村里没有正规的色盅,一般是使用大的酒杯或者碗来替代,倒扣在托盘上,托盘就是瓷的碟子,两颗色子就在碗下面,托盘上面。老爷(庄家在我们本地的叫法)上下左右摇动几次托盘里的色子后,所有闲家开始押注,分单双两边,两颗色子的点数加起来是单数的话,结果就是单,两颗色子的点数加起来是双数的话,结果就是双,闲家可以任意押一边。押注完毕之后,老爷就可以直接开,输的陪赢的拿走。这种博彩形式在我后来开始玩百家乐之后,仔细琢磨过,发现有个很大的漏洞。两颗色子,加起来点数的个数,一共是11个:2点到12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单和双的个数不一样,5个单,6个双。双的个数要多一个,百分比来算的话,接近10%的概率。
对于这些博彩形式,从小开始我就很好奇(不过现在想来蛮可惜,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加紧锻炼,多加专研,配合上心灵手巧,搞不好早就勤劳致富了。^_^)。那个春节也是鬼使神差,特别想要去试一试。平时零花钱都不太富余,总是等最需要的时候,才向母亲开口,更别说向母亲要钱了去赌博。有个奇怪的现象,相信大家都有,就是要零花钱,我们总会比较固定找一个人要。比如我和母亲比较亲近一些,所以基本找母亲要零花钱。向父亲要零花钱的时机屈指可数,有,也是学校特别需要交费的时候,才能理直气壮地给父亲说。看起来人也挺能察言观色,父亲比较严厉,担心他会拒绝。
因为特别想去赌博一下,刚好那个春节,小姨妈从相隔12公里远的曹市镇来我们家走亲戚,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大着胆子,向小姨妈要钱说想去赌博。喜出望外的是,小姨妈居然答应,给了我一块钱。一块钱的定义是什么?那个时期的油条是一毛钱一根,一块钱可以买十根油条,如果用油条来衡量的话,相当于现在的十块钱。
记忆深刻的是,要到的那一块钱,最终没有拿去赌博。而是放在小小的裤子口袋里,暖了好几天的心,以备特别紧急的时候派上用场。感觉自己像个富翁一样地,大摇大摆地在村里到处溜达。后来换了好几次裤子,居然淡忘了这个事情,再次记起的时候,发现已经找不到这一块钱的纸币了。
在乡村散文集精选:尼龙长裤
可能贫穷需要分为主观贫穷与客观贫穷两种情况。主观贫穷是自己觉得贫穷,以心理的感受为主,客观贫穷就是物质的绝对匮乏。80年代基本上村里所有人家的贫穷程度相差不多。处于一种基本上可以吃饱,但是没有结余人民币的一种境况。感觉不到贫富差距,相对于现在,内心里也没有生出那么多的愤恨与不满。改革开放的思想还没有普及开来,除了夏天的时候,有卖冰棍的,农村串乡的小商小贩基本上没有。

归结起来,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物质上确实比较贫乏。听奶奶讲了挺多49年解放之后,搞集体时候的事情。早上起来,村里的干部统一安排上午做什么事情,比如插秧,那么,所有的人,能赚工分的,都去插秧。力气大一些的壮年,承担挑秧(用扁担,两头各勾一个篓子,把秧苗从育秧田里转运到插秧的田里)的事情。力气小一些的妇女或者身体不太好的人,就插秧。完成的事情按工分算,比如一个壮年一天9个工分,一个妇女一天6个工分,小点儿的孩子不能做重活但可以帮忙打下手的,4个工分。月末的时候,会统计,每人本月一共赚了多少个工分,等到年底的时候,才能算工分结算收入。
按道理来说,这是挺合理的一种协作集体制。大家各自分工,做自己能做和擅长做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中,总会存在那么一些,想要投机取巧或想要通过关系权利达到某种利益的人,而体制,恰好给予他们这种操作空间。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做的多,反而得到的少。而有些人做的少,反而得到的多的不公平现象。当做的多的人得到的反而少了,于是就会去反思,为什么我要做的多,得到的少呢,在一个大锅饭集体制里面,大家都是按天数来算工分的。所以,做的多的人,没有了积极性。慢慢地形成一种氛围就是,大家都玩玩打打,不去认真地做事情。可想而知的是,年底结算的时候,大家彼此都不会得到更多的结余。没有钱去购买消费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思想上贩卖经商,从小农经济慢慢转向商业经济的思想没有建立起来。刚刚开始从集体制转成单干,虽然很多人很积极地开始做事情,因为现在种的地是自己承包的,在地里长出的庄稼是自己的。自己做的多,就收获的多。但是,作为底层的老百姓,因为思维的惯性,以及眼界的问题,还有对于动荡社会的体制是否会改回去,存在疑虑。而且,没有可以参考的成功经商的例子,所以,能放开手脚开始经商的人,基本上没有。
社会思想的风暴中心,一般是来源于学校或者是政党。一方面是知识的力量,另一部是组织的力量。农村相对来说,因为现实硬件的缺失,往往是思想普及的最后阵地。相信80年底中期,中国的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向着商品经济社会迈步了。只是它的步伐还没有到达我所在的村庄。
想起一件事,这件事好像还有点儿心酸。
应该是三年级,1988年,10岁的样子。在柘(zhè)岭村(以前是河嘴村,后来分成了两个村:河嘴村和柘岭村,关于分村的经过,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读于万全镇河嘴村完全小学。河嘴小学在离家西边700米,从家里出来,拐个湾,一条直路,向西走,步行大约7分钟。农村的小学,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本村的村民,偶尔会有一个外村的年轻老师,不过一般呆不了多久,就会被调走。乡村的老师工资不多,有家眷所以一般都有农田,自己种地至少吃的粮食不用开销去购买,在农忙时节需要回家打谷插秧割油菜收小麦。偶尔会和其他老师调换课时,本来课程表上是语文课的,临时改为数学课。
那天下午本来不是体育课的,结果,临时改成体育课。按理说这是很普通的一种临时调整,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不妥的地方在于,那天下午,我穿着一条尼龙布料的,且过长的裤子。要知道,正是因为没有体育课,我才穿的那条裤子。凭着模糊的记忆,这条裤子极可能是我三叔的,然后哥哥穿了一段时间,给我在穿。裤子有些长,裤脚需要卷几扁才不至于拖到地上。那个时期,好像没有改裤脚一说。平时上下学穿,慢慢走路,不觉得,一端走快了,卷起来的裤边就容易滑下来,滑下来之后,因为裤子长,就会被踩到脚下,容易摔跤,必须再卷一次裤边。
上体育课基本是先绕着那个小操场跑个10分钟。小学时候的自己,性格有着极为反差的两面性。在小伙伴面前基本属于孩子王的类型,指挥其他小伙伴爬树掏鸟窝,甚至打架,但自己一般不会出手。但是在有大人或其他人多的场合,却显得特别害羞。跑几步,裤边滑下来,踩在脚下,必须移到跑步圈外围,蹲下来,卷起裤边,继续跑,跑几步,裤边又滑下来,汗也下来了,不知道是热的,还是难堪的。在这样不断的循环中,让人体会到一种窒息的尴尬,要知道,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了想要在异性面前留下好印象的自尊心。但是除了继续跑下去,好像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多么希望体育老师发点儿善心,说不要继续跑了啊。但老师就是不理解我渴求的眼神,我不禁有些恨他。
跑步终于停下来,世界终于没有那么尴尬了,红着的脸以缓慢的速度在恢复正常。那天晚上回家之后,以后就再也没穿过那条尼龙裤子,到现在也想不通,怎么用尼龙的料子去做裤子的呢。换上了一条以前穿过的,右膝盖处有个补丁的那条。
在乡村散文集精选:右膝盖上有个补丁的长裤
好像,在不同的时期,都还有着一到两个不错的朋友。无论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步入社会后,因为工作地点的不断变迁,朋友基本在结交中流失。如今反思起来,最初毕业之后就应该长期呆在一个一线城市,砸锅卖铁都要买房定居。不过又感觉那大约不太适合自己,在漂泊的旅程,不断变迁的工作与城市中,慢慢发现,或者这种流浪的工作与生活,才更加适合自己永远不会安分的那份躁动与狂热。
小学那个时期,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姓杨,挺抱歉在岁月的流逝中,同样也流失了他的联络方式,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上的大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历程中,虽然我们平凡人并没有站在时代的浪尖,但不可避免地,在翻滚的河水中,想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所以,随波浮沉,为了生计和小小的理想奋斗,失去的,有些是可贵的友谊,有些是可贵的亲情。地域经济差异在驱动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们。
杨同学比我们班所有人都年长,不包括老师。因为他家境比较贫困,读书比较晚,父母在隔壁的峰口镇上一个叫做范湖的村里养鱼。在我们万全镇河嘴村里,因为是外来人口,并没有什么田地,也没有人来耕种。平时和奶奶,妹妹和弟弟一起生活,种点儿菜地,粮食需要采购。他是老大,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家务。学习成绩不太好,常被老师批评。但因为偶尔学校班级有些什么活动,都需要一些大力气的劳力,这个时候,他就派上用场了。在班级里平时存在感比较低,很沉默。但有一个特点,居然特别喜欢习武。常常打一些拳法给我看,是书摊上类似小人书一样的拳法样式,我也看不懂,偶尔会假装说打的真不错。后来据说他在温州某个商场做上保安队长,还娶了老婆。这是N年后的某天,道听途说的,这是后话。
那条右膝盖上有个补丁的裤子就和他有关。(尘世流转,如果这些文字某天能进入杨同学的眼里,记得赔我一条崭新的裤子,小学那个甚得女生喜欢的小陆同学想你了。^_^)
记得是在学校门前的地里玩耍,绿绿的草地,散发着清香。油菜花刚刚开过,已经开始结果。长条形一串一串的油菜籽像躲迷藏的孩子,被油菜荚包裹着。田野总是空旷的,这种空旷从学校门前的那片油菜地开始延伸。我们下课后,常在田里的垄沟跑来跑去,一米左右的油菜杆,正好可以遮挡住我们躬下的身躯,嬉戏正好。
我和杨同学因为喜静,常会避开那些比较热闹的地方。躲到一个很少有人的田里去玩。油菜田与油菜田都会有田埂作为分隔,我们就在田埂上,外面的很难发现。偶尔看看他打拳,或者聊聊天,至于聊什么好像不太确定,不过那个时候确定的,偶尔讨论一个住在他家隔壁的女生(这个女生可以称的是班花,后来在五年级和她还有一些有趣的童年故事)。
有一次课后休息,他说新学了一套什么拳法,要演练给我看。练着练着,可能太集中精神,居然被他推到田埂下面的沟里去,雨后的田里一片湿漉,沟里还蓄着小水坑。连人带马地滚翻了下去,衣服沾上了黏黏的稀泥。赶紧爬起来,杨同学连忙道歉,正好也听到了上课的铃声,于是洗了下手掌,清理下明显的泥渍跑到教室去上课。
上着上着课,突然觉得右膝盖有些酸痛和麻木。低下头看吓了一跳,右膝盖的裤子上开了一个口子,齐整整的,口子周边的颜色暗红,结痂了硬硬的,用手捏了一下,发现黏黏的,是血。
下课后去田埂上找了下,发现滚落的沟里,还留存着那个玻璃瓶渣,瓶渣的尖端还留有鲜红的血迹。原来是被玻璃瓶渣给扎了一下,当时因为赶着去上课,所以没有觉察到,右膝盖处的肉被深深地挖掉了一块。
留在印象中的疼,居然一点儿都没有。就是特别可惜那条裤子。那条竖条纹的草绿色裤子,是母亲新给做的,而且还是唯一的一条新裤子,穿了还不到一个月。膝盖被扎之后,没敢告诉父母,一直穿着那条破裤子在上学放学。大约半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换下来清洗,被母亲发现了。
等到再次看到那条竖条纹的草绿色裤子的时候,右膝盖处已经贴上了一条斜斜的补丁。因为小小男生的自尊,于是自己翻箱倒柜,找到了一条特别长的尼龙裤子,寻摸着可以穿,于是就穿上了。卷起几扁裤边,好像也很还不错。大大的裤管,特别像那个时期流行的喇叭裤的下端。自己还暗自得意了好久。
为着一条补丁裤子感伤的年代,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当物质逐渐丰满,我们不愁吃穿,却偶尔会发现,快乐不再那么直接和纯粹。我很难评价哪种生活更好,但我知道,我常怀恋那种生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