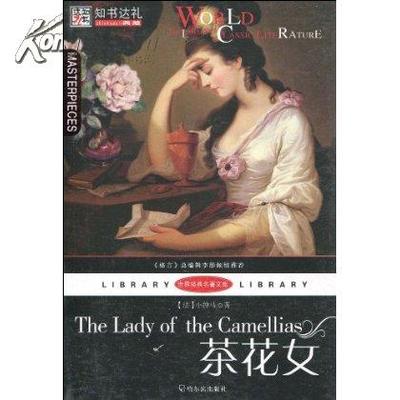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读好书,书读好,这是我读《我坦言我曾尽沧桑》之后的心得,欢迎大家阅读。
“多么遥远的年代!再现这些年代,就像再现现在断断续续传入我内心深处的涛声一样,有时哗啦哗啦地弄得我昏昏欲睡,有时又像一柄利剑蓦然闪现寒光。我将捡起这些如同起落不定的浪花般没有年代顺序的景象。”
聂鲁达访问中国时,得知自己的中文译名中的“聶”由三只耳朵组成,他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本《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正是他晚年在黑岛倾听着大海的声音写成的。他的一生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既有主动的流浪,又有被动的流亡。回忆录的结构虽然松散,各章节大体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只不过各个人生阶段有着迥异的主题。少年时代,他所追求的是诗人的身份;而之后,当他已不需要披着著名的黑斗篷来塑造自己的诗人气质时,跨越数个大洲的万千风景、无数陌生人或朋友的面貌都在他的文字中凝聚起来,迫使他寻找一种新的身份,成为别的事物的代表。诗歌、政治和爱情因而织成了紧密的网。然而在中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对聂鲁达的译介和阅读是阶段性的,并且呈现断层的状态,从来都不完整。五六十年代,人们读他的政治诗;八九十年代,诗人学习他的现代主义手法;如今,流传最广的是他早年的爱情诗集,其余的作品很少再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本回忆录恰好是一个契机,可以还原聂鲁达作为诗人、乃至作为智利政坛一员的完整风貌。
从政治诗一路读来的人,也许会认为他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非常单纯。他的颂歌热情洋溢,对革命及其领导人的崇拜也同样毫无保留。他斥责一切压迫和肮脏的手段,关心工人的解放,让这些被迫沉默的人“用我的词语和我的血说话(Hablad por mis palabras y mi sangre)”。回忆录秉承了这一贯的风格,只不过将他的想法通过各种生动的经历表达得更加具体。除此之外,回忆录中还有对与斯大林、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重要人物会面的记叙。在这些极有争议的人物周围,聂鲁达尽管也存在疑问,但他的热情和身为革命一员的自豪感让他将这些疑问摆到了次要的地位。聂鲁达自己将这种自豪感视为一种弱点,然而这弱点也是他自豪感的一部分。
然而,也许最令聂鲁达印象深刻的,仍然是政治与革命给诗歌留下的位置,是战争与冲突中因为诗歌而变得缓和的瞬间。在回忆录中,他描写了许多类似这样的场景,描写甚至不识字的工人对他的诗歌和演讲的热爱:“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名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 ...他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他认为这些时刻就是他所得的奖,比其他的文学奖项更加重要。
大概这种感情从根本上是扎根于智利这片土地的。硝石工人的手“胼胝和掌纹如同大草原的地图”,仅仅生长在南极区海滨的智利铁兰在血腥的历史变迁之后依旧开花,而至今没有名字的小花也默默无闻地纠缠生长,如同农夫、渔民、矿工、走私贩生死相继。“我于是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地的过去总会开花。只有大地长存不息,不改它的本质。”还有书中随处可见的对南美壮丽风景的描写,那些广袤的草原、山峦、瀑布、林地、无垠的天空,恰到好处低映衬着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无序、孤独、不安和沉默。
回忆录中对聂鲁达那个时代诗坛人物的描写则饱含另外一种感情。他的旅行将欧洲和南美洲的诗人联系在一起,还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对许多著名的诗人进行了评价与赞扬,比较为人熟知的包括加西亚·洛尔卡、保罗·艾吕雅、萨尔瓦托雷·夸齐莫多、塞萨尔·巴列霍、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比森特·维多夫罗等等。这些是诗人特有的具有感官性的评价,如同一个工匠对另一个工匠杰出手艺的赞扬,超出技巧而立足于微妙的品位。在聂鲁达看来,诗歌的作者如同星辰的创造者,也是从事漫长工作手艺人。在物质和精神上,诗人都有权利幸福,也应当幸福。而在这些兼具记叙性和评论性的段落之间,又穿插着聂鲁达自己对诗歌、对美、以及对成为他创作源泉的许多事物的回忆与思考,与他的诗歌作品一样广博,仿佛要将世界的一切囊括其中。而他与各个诗人与文学家之间的友谊、活泼的趣闻轶事,也是书中最可读最吸引人的部分。当时存在的种种出于妒忌的诋毁和反对的声音也无法抹消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少有诗人像聂鲁达那样,在自己的时代能够同时受到那么多文艺界人士和平民大众的喜爱。

作为一本私人的回忆之书,《我坦言我曾尽沧桑》提供了超越聂鲁达个人生活经历的丰富内容,将跨越七十载和几大洲的人、事、风景用极其诗意且热情洋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然而,为此书作结的是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死亡,为这段人生作结的是十二天后聂鲁达自己的死亡。因此这本书,在成为文学界又一珍宝的同时,保留了一道开放性的伤口的姿态。无论它的写作者是诗人还是政治家,说不定这也是所有的华丽辞藻和理想立场背后历史的真实姿态。书页结尾的空白处这意味深长的沉默,也许正是本书最恰当的句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