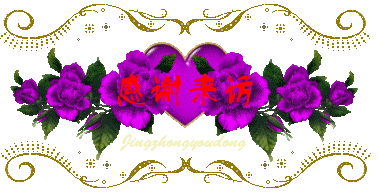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而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对着新的形势,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希望能在马克思这里找到应对问题的良方,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被充分“挖掘”了出来。如今,纵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众多,但也分歧众多,这样就不免让这一理论显得“扑朔迷离”,基于此,笔者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就现今学术界对于这一思想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一、“世界历史”理论概述“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概念,从古至今都在被人们所研究,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从对于希波战争历史的研究,论及了近20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图景,渐具了一种“朴素的世界历史眼光”;而近代“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将“世界历史”的研究从史学领域初步提升到哲学领域,并通过构思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概念来揭示世界历史的法则。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圣西门、傅里叶则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分期和发展动力的揭示,来表达对于未来社会的向往和描述;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笔下,“世界历史”则是作为一种“绝对理念”的逻辑发展,是“绝对精神”不断实现自我的过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表述过他的这一思想,而是散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后来的《资本论》和《人类学笔记》中,但是马克思通过对于前人特别是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同时,他进一步论述:“各国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p.46)这样,马克思就从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考察世界历史,形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同时,马克思还强调:“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其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于“现实的人”的关注,再者,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世界历史”的论述,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普遍交往的发展,世界历史诞生的标志—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的世界整体化,最后,马克思在晚年还集中论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过渡的必然性等问题,渐渐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真正将“世界历史”从玄虚的“天国幻境”拉到现实的人间。
二、“哲学的世界历史”与“史学的世界历史”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起初只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指与国别史相区别的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历史,也是指对这种历史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的名称。对于马克思笔下“世界历史”基本含义的界定,国内学界分歧很多,多数学者认为此概念包含四层意思:第一,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促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系所形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将来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蕴含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四,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也有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概括为世界历史成因论、世界历史时代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时代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等[3]。同时,国内众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在哲学意义上规定世界历史的基本内涵,是与以前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相区别的,这一点,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经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以及国内各学者的研究,笔者发现,马克思本人以及其后的马克思研究者都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具体而言,它指的是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2](p.119)可以看出,这一基本含义的如此界定是建立在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并没有脱离开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可以说史学意义的研究是马克思整个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后来对东方社会历史研究的著作,如《人类学笔记》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可以说他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史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结合,史学意义的研究让他排除了16世纪以前各民族国家相对隔离,孤立还没有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同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理论等。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从逻辑上进行提升,从历史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揭示出人类实践活动的进程,并且将之与“现实的人”的活动紧紧相连。
三、“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纵观现今学术界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将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划上等号,或是说世界历史是全球化思想的源头,笔者对这样的言论持怀疑态度,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什么是“全球化”。
据考证,“全球化”这个术语最早是由莱维在1985年提出的,他试图用这个术语来说明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对于全球化,如今学界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哈贝马斯在其1998年发表的《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中所界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谓的:“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业相互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与缺席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4]诸如此类的界定不胜枚举,这也说明了,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且更多的是指称一种经济上的全球化,同时对于“全球化”的态度问题,国内外学界有三种基本态度,一种是乐观态度,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给世界带来一种新的发展,每个民族国家都无法不面对他。第二种是悲观态度,认为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和“分化”的战略新手段,是西方国家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新工具。最后一种是中间派,认为全球化有利有弊。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与世界历史之间有很多相同点,即都将历史看成是一种进步的发展过程,都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看作为世界历史运动的必经阶段,同时两者都将人类相互依存,突破地域性存在,民族国家联系更加紧密作为自己的理论内核。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一个方面就是二者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不同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其最终的发展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而存在,但是,对于全球化的最终发展去向,理论界多有分歧,特别是在西方学界,更多的人主张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如学者雅克·阿达就主张:“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等。另一方面,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历史,其发展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目标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他也看到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时的作用,称其为“不自觉的主体”,而“全球化”理论的主流更多强调的还是商品,资本,技术的世界性流动,在其中主导其发展的是资产阶级。
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性,全球化理论的复杂性势必要求我们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而应该理性对待。
四、“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具有重大价值,这在国内外学界应该说是认可的,但在国外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具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例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在美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2000年春—夏季号)上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有封闭的和开放的两种历史进步观,所谓封闭的历史进步观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观点,“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或封闭的辩证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似乎把源于欧洲都市的生产力发展历史进步等同起来,因为生产力发展必然导向社会主义。”[5]类似的观点还存在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中。这里,我们不禁要替马克思“鸣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关注的是全人类,其批判的正是黑格尔眼中那种将世界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展现,并将“世界精神”从东方游历到西方最后在日耳曼达到了那种所谓充满活力、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日耳曼民族主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并不承认世界体系有特定的中心,或者由某个民族来主导,同时,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新的对华战争》,《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文更是表现了他对东方国家反殖民斗争的由衷赞赏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美国学者奥古斯特·尼姆兹在题为《所谓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相关的无稽之谈》的所认为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很早就以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进程作为自己的根本观点,从未将眼光拘限于英国或欧洲。”[6]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能被定位为“欧洲中心论”,反而,他是把人类的解放与世界历史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唯物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历史”理论,其本身充满着丰富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眼光”和“人学”的新视域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更需要我们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思维去研究,不能过分神话这一思想,也不能对其做简单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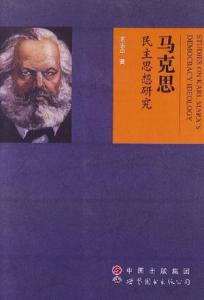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