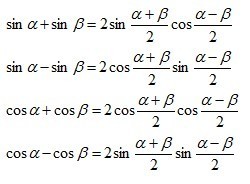认知也可以称为认识,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言语,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即个体对感觉信号接收、检测、转换、简约、合成、编码、储存、提取、重建、概念形成、判断和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对认知进行研究的科学被称为认知科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认知的具身化。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认知的具身化 全文如下:摘要:随着认知的计算隐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认知科学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的思想在认知科学中已经有了广泛的融合。具身认知的思想认为,认知不是一个先验的逻辑能力,而是一个连续进化的发展的情境性过程;身体在认知中之所以是核心的,是因为身体活动本身体现了推动认知发展的生存意向性。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内化理论、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投射理论表明了身体活动如何向高级认知发展的。目前借助动力系统理论,关于具身认知的神经建模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一个对认知更为全景的轮廓已经形成。关键词:认知|情境性|生成|具身化|动力学。 论文正文:随着认知的计算隐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认知科学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在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教育、认知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行为和思想的动力系统进路(approach)中,人们已经日益频繁地谈到具身化和情境性(situatedness)。”[1]例如,在认知发展领域有西伦(E. Thelen)的工作;在语言学领域有莱考夫(G. Lakoff)和约翰逊(M. Johnson)的工作;在机器人学领域有鲍拉德(Ballard)、黑霍(Hayhoe)、普克(Pook)、和劳(Rao)的工作;在神经科学和动力学领域有西伦、盖拉德(T. van Gelder)、希尔(Chiel)、比尔(Beer)、埃德尔曼(G. M. Edelman);在哲学领域有克拉克(A. Clark)、瓦雷拉(F. J. Varel)、汤普森(E. Thompson)和罗施(Rosch)的工作;等等。
1 具身认知1.1 关于“embodied” 和“embodiment”的译法和用法
目前关于“embodiment”和“embodied”,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译法。但从“embodied mind”和“embodied cognition”所强调的一般观点来看,“embodied”是指:心智和认知是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2],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和本质的关联。从发生和起源的观点看,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体)身(体)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因此,我们把“embodied”译为“具身的”,“embodiment”译为“具身化”。但随着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研究的深入,“embodied”的内涵已经被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它和情境性的概念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关于“embodied”的搭配用法,我们以茨马克(T. Ziemke)的列举为例:
具身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被广泛地用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文献中,诸如这样的术语:embodied mind, embodied intelligence (e.g. Brooks, 1991), embodied action, embodied cognition, embodied AI, and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而且,明显存在具身
化的不同类型和概念,如situated embodiment, mechanistic embodiment, phenomenal embodiment, natural embodimen, naturalistic embodiment, social embodiment, 另加本文中的historical, physical, organismoid, and organismic embodiment. [3]
1.2 相关的概念
在当前的认知科学中,人们对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描述使用了几个与“具身的”含义相似的但着眼点不同的概念,如:“情境性”(situatedness/embeddedness)、“生成”(enaction)。
情境性
情境性和具身化观念密切相关,它们都是在反对传统的认知主义的基础上,最初从不同的侧面提出的。认知的情境性研究拒绝认知主义的如下的几个基本观点,认知主义认为认知是:(1)个体的,即认知由孤立的个体进行;(2)理性的,即认知的首要范例是概念思维;(3)抽象的,即身体和环境在认知中是次要的;(4)分离的,即思维与知觉和身体活动在逻辑上是分离;(5)普遍的,即认知科学是寻找一般智力活动的普遍原则,它适用于所有个体和所有环境。
与之相反,情境性的研究认为,认知是:(1)社会的,即认知发生于人类构造的共同体中;(2)具身的,即身体的物理方面在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3)具体的,即认知的实现和环境的物理约束是极为重要的;(4)定域的(located),即情境依赖是人类活动的一般特征;(5)参与的,即认知是与周围环境的持续的相互作用。[4]
生成
“生成的”(enactive)是瓦雷拉等人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这部经典著作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它是一个和“embodied”同等重要的概念,在一些学者中它们甚至被等价地使用。“enactive cognition”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经验论(极端的客观主义)也不同于唯理论(极端的主观主义)的认知方向。瓦雷拉等人选择这个术语来“强调这个日益增长的确信:认知不是一个预先给予的心智对预先给予的世界的表征,认知毋宁是在‘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施行的多样性作用的历史的基础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根据“enactive”的含义,瓦雷拉等人认为,知识有赖于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社会历史——简言之,我们的具身化——不可分离的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 in a world),知识不是存储在心智中,而是在世界的交往活动中发展的,认知者处身于(situated in)世界中,认知者和其实践的世界彼此蕴含在相互生成的过程中。[5]
1.3 具身认知的含义
这里,我们给出三个对“具身的”看法:
(1)瓦雷拉等人
通过“具身的”这个术语,我们想要强调两点:首先,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出自于具有各种感觉肌动(sensorimotor)能力的身体,其次,这些个体的感觉肌动能力本身根植于(embedded in)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6]
(2)西伦
认知是具身的,就是说认知源于身体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从这个观点看,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出自于具有特殊的知觉和肌动(motor)能力的身体,而这些能力不可分离地相连在一起,并且共同形成了一个记忆、情绪、语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编织在一起的机体(matrix)。具身认知的当代观念反对盛行的认知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视心智为一个操作符号的装置,因此这个立场专注于形式规则和过程,通过它们符号恰当地表征了世界。[7]
(3)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观时提出:
理性并非如传统大多数认为的那样是非具身的(disedmodied),而是源自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经验的本性。声称我们需要一个身体来进行推理,这并非平淡无奇和显而易见,毋宁说,理性的结构本身正是来自于我们具身化的细节,这个主张是惊人的。使得我们得以知觉和四处活动的同样的神经和认知机制也创造着我们的概念系统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视觉系统、运动系统以及一般的神经绑定(binding)机制的细节。总之,理性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宇宙或非具身心智的先验特征。相反,它完全是由人身体的特性、我们大脑神经结构的非凡细节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日常活动的细节(specifics)所塑造的。[8]
1.4 具身认知范式
汤普森认为[9],生成的认知科学(enactive cognitive sciences)或具身的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涉及三个论题:
(1) 具身化:人的心智不是局限在头脑(head)中,它具身于(embodied in)整个有机体中,而有机体根植于环境中;
(2) 具身认知的涌现(Emergence)的动力学机制:具身认知是由涌现的和自组织的过程构成的,该过程通过藕合(coupling)或交互的因果性(reciprocal causality)使大脑(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相互连接在一起。
(3) 自我-他者的共同决定(Self-Other Co-Determination):在社会生物中,具身认知是从自我-他者的主体间的动态的共同决定中涌现出来的。
这三个论题表明具身认知观与表征的和计算的认知主义(cognitivism)的认知观的对立。现在,具身认知不仅是一种起于哲学的观念,而且已成为明确的认知研究进路、纲领和范式。瓦雷拉(F. J. Varela)等人区分了认知科学研究演进的三个圆环(如图[10]):认知主义、涌现(联结主义)和生成论(enactivism)(或具身范式)。与之相似,莱考夫和约翰逊区分了认知科学发展中的两个范式:“第一代认知科学”(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和“第二代认知科学”(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或者是“非具身认知科学”(dis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和“具身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11]
如果我们把“具身的”、“生成的”、“情境的”这些概念所强调的不同侧面结合起来,我们给出具身认知的一个更全面的表达:认知是根植于自然中的有机体适应自然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它经历一个连续的复杂进化发展过程,它最初是在具有神经系统(脑)的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中生成的,并发展为高级的、基于语义符号的认知能力;就情境的方面而言,认知是一个系统的事件,而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事件,因为认知不是排除了身体、世界和活动(action)而专属于个体的心智(大脑)并由它独立完成的事件。
2 具身认知的两个维度:连续的进化和暧昧的身体2.1连续的进化
认知主义将认知抽象为一个独立于身体活动和环境的内在的表征和计算。但真实的是,认知不是一个纯粹内在发生的、独立进行的事件;也许认知主义的这种抽象的和二元论的看法只有从认知的高级水平,即笛卡尔的“我思”——科学、数学和逻辑思维——上看才是“显然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进化的连续性,那么认知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处于高级水平,但传统的认识论以及认知主义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知,换言之,即只顾到认知的某些完成形态。因此,皮亚杰认为,对认知的研究必须追溯认知的发生和起源,“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 [12]从这样的角度看,认知必然有一个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历史。我们的结论是:在人类和狗之间,在猫和阿米巴虫之间,在成人和幼儿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渐进的差别和连续性。认知是一个连续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无历史的逻辑能力。[13]因此,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理性是进化的,因为抽象的理性是建立于,并使用出现在“低等”动物中的知觉和运动推理形式。这个结果是理性的达尔文主义,一个合理性的达尔文主义:理性,即便是其最抽象的形式中,是使用而不是超越我们的动物本性。理性是进化的这个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关于人是唯一理性的概念。因此理性并不是一个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质。毋宁说,它将我们置于一个与动物的连续统(continuum)中。[14]
当我们接受这样一个进化的认知观点,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同样具有广延特性的身体的认知作用。因为,认知的初级形式的演化大都表现于身体活动的能力,而且只有通过一个有广延的身体我们才和自然真正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的二元论分界才会在演化的连续性中渐渐变得模糊。
2.2 暧昧的身体
认知最初能以具身的方式实现,是因为身体已经不再是一般的物理学的物体,它是生物学的有机体,是与环境进行接触和相互作用并能完成种种动作图式的活的身体(lived body),是社会文化中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15]在认知上,身体是具有相对同一性(identity)和独立特性的一个系统的整体。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和世界接触的媒介,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有物理的特性,所以我们才能“在世存在”,我们才能与其它的自然之物同处一个世界和共同拥有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遵循同样机械生理学和生物力学的要求。我们不可能飞翔,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像鸟的身体那种适应空气动力学的身体结构。
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中,梅洛-庞蒂(Merlau-Ponty)看到了身体经验的暧昧性或两义性(ambiguity)。我们被经验到的身体不是笛卡尔二元论意义上与“我思”对立的单纯广延的物体,它既非纯粹无意识的活动,但也不完全是先验意义上的无广延的纯粹意识。我们的身体具有非二元论的双重的特性,我们身体的这种特异性在于它既是能感觉的(sensible)也是敏感的(sensitive),同一个手既能触摸也能被触。身体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它对刺激做出反应,但也赋予刺激一种意义。例如,当我们打击到一个面团和一个人的身体时,面团和身体同样的物理上的凹陷反应,但身体还有避开打击带来疼痛的躲避反射。因此,身体已经是意向性的身体,但不是纯粹“我思”的意向性,而是在世界中生存的意向性:
反射不是客观刺激的结果,而是转向客观刺激,给予客观刺激一种意义,客观刺激不是逐个地和作为物理因素获得意义的,而是把它当作情境时获得的。反射使客观刺激作为情境存在,并与之处于一种“认知的”关系中,即把客观刺激当作它一定要面对的东西。由于反射向着情境意义开放,由于知觉一开始没有确定一个认识对象,由于知觉是我们的整个存在的意向,所以反射和知觉是一种前客观看法的样式,即我们称之为在世存在的东西。[16]
因此,身体及其活动图式既满足于物体活动的要求,它也满足生存意向的认知要求:例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讨论了身体空间的扩展性(盲人的手杖)、作为性别的身体、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等。在生存的意向上,我们身体系统的结构和活动图式最初已经是藕合于世界的认知系统了。“我们的知觉范畴和形式,在个体经验之前已经确定了,它们适应于外部世界,其理由完全相同于在马出生前马的蹄子已经适应于大草原(steppe)的地面和鱼在孵化前鱼的鳍已经适应于水。” [17]
3 心智和认知是如何具身的呢我们应该不只是确信心智和认知是具身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到它们是如何具身的。为此,我们仅提示性地考察两个方面:(1)身体活动向高级认知的发展和在其中的作用,这里我们涉及皮亚杰/维果斯基的动作内化理论和莱考夫/约翰逊的概念隐喻思想;(2)认知的具身研究的动力学方法,这里我们涉及当今认知研究的动力系统理论。
3.1 动作内化(internalization)
尽管人们在直观感性上认为,身体动作或活动(action)与心理和认知发展之间具有直接密切的联系。但是直到皮亚杰和维果斯基提出认知的动作内化理论后,动作和认知发展的多学科的系统研究才蓬勃发展起来。
皮亚杰认为,身体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基础;认知结构的起源是动作的一般性协调,而动作是身体与环境在相互作用的活动中的最初的接触面和接触方式,是主客体的桥梁;主体为认识客体必须对客体施加动作,如吃苹果。在这类作用中,心理和认知结构以一个连续的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mmodation)和结构-建构的动力过程不断改变和重建;一些初级的动作以及其它许多更复杂的动作逐渐在心理水平上进行着,它们成为内化的思维活动,即形式运算。
维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最早提出了外部动作“内化”为智力活动的理论。他认为符号的运用使得心理活动得到了根本的改进。没有语言的心理活动是“直接的、不随意的、低级的、自然的”,只有掌握了语言后才能转变为“间接的、任意的、高级的、社会历史的”。操作外界事物的外部形式的活动,即从感知运动向语言思维的过渡。维果斯基强调“活动”的作用,并运用外部活动和内活动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揭示儿童思维发展的动力。[18]
3.2 隐喻投射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肉身中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开宗明义地提到认知科学的三个主要发现:心智原本是具身的;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部分是隐喻的。[19]这三点指明了身体在认知和心智中的基础性和运作方式,而第三点特别表明高级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思维发生于身体经验的一种途径,即通过隐喻投射而形成概念隐喻。
长时间人们持有的看法认为:只有人的头脑(head)才可以形成概念,理性思维同知觉和行为是无关的,与人的感觉肌动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概念一定是抽象的,是非具身的(disembodied)。但以莱考夫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推翻了这种看法。
在认知语言学看来,隐喻具有普遍性,隐喻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概念意义的获得和概念体系的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发生的过程看,它们源于人们最初的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身体经验被用于抽象概念是司空见惯的,如Affection Is Warmth,Important Is Big,Happy Is Up,Intimacy Is Closeness…[20]。隐喻投射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人类的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抽象概念之前的身体经验至少存在两种结构:
(1) 基本层次结构(basic-level structure)
“家具-椅子-摇椅”、“交通工具-汽车-赛车”,这显示了人类范畴的一个基本层次结构,即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基本水平范畴(basic-level category)-下属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y)。在这三个层级中,我们的知觉系统最容易区分出基本水平范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卡罗林·默维斯(Carolyn Mervis)和他们的合作者发现,这种中间水平的范畴在认知上是“基本的”——也就是说,与“上位”范畴,如家具和交通工具,和下属范畴,如摇椅和赛车,相比,它们有一种认知优先性。[21]。伯林和罗施发现,基本水平范畴的认知优先性有赖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基本水平和非基本水平范畴的区分是基于身体的,也就是说,基于格式塔知觉、肌动计划和心理意象(mental image)。
(2) 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意象图式结构是指那些在我们的日常身体活动经验中反复出现、相对简单的结构和空间方位关系,前者如容器图式(Container)、路径图式(Path)、力-动力图式(force-dynamic)等,后者如部分-整体(Part-Whole)、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近-远(Near-Far)等。
意象图式是通过身体来理解的。像前和后这样的概念出自身体,依赖于身体,并且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这种身体,它们就不会存在。这对于基本的力-动力图式(推、拉、推进、支撑和平衡)也是同样的。我们理解这些是通过使用我们的身体部分以及我们移动它们(特别是我们的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我们的身体是呼吸空气、吸收营养和排泄废物的容器。我们一直以容器(屋子、床、建筑)定向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把抽象的容器投射到空间的区域上,如同当我们理解一大群蜜蜂存在于一个花园里。同样,每次我们看见某物移动,或移动我们自己时,我们就以源-路径-目标图式来理解那个运动并进行相应的推理。[22]
3.3 认知具身化研究的动力学方法
我们说认知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事件,而是包含了脑神经系统在内的复杂的系统事件。也就是说,认知是认知者(agent)(身体和大脑)与环境(自然和社会文化)的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生成过程(如图[23])。例如冯·盖尔德(Tim van Gelder)说,“认知系统不仅仅被封装在大脑中,确切地说,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都持续地改变着,并且同时地彼此影响,所以真正的认知系统是包含这三者的单一的统一的系统。” [24]更通俗地说,认知是情境化的过程。但这些说法不过是一些过于“粗糙的”的定性描述。我们如何能够更实际地了解具身认知的实现机制呢?目前的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DST)的进路正在发展这种实现的可能性。
相对于认知的计算假设(Computational Hypothesis, CH),盖尔德1995年给出了一个认知的动力学假设(Dynamical Hypothesis, DH):“自然认知系统是某些种类的动力系统,而且从动力学眼光来理解是对认知系统最好的理解。” [25]应该说,当前认知的动力系统进路的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史比(W. Ross Ashby)就预见性地提出:所有的认知或许都能由动力系统模型来解释。[26]但是限于当时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和实现这种模型的计算方法,以至于在Ashby的建议之后很少有后继的研究。
应该看到,认知的动力系统研究本身不是一个范式,而是实现“激进具身认知论题”(The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 Thesis)的数学方法和工具,其观念基础仍然是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等概念。
动力学假说是以数学的动力系统理论为基础描述认知。动力系统理论(DST)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本质上是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系统演变的行为。其概念术语一般有:状态空间(state space)或相空间(phase space)、参数(parameter)、路径(path)或轨迹(trajectory)、拓扑学(topology)、吸引子(attractor)、稳定性(stability)、藕合(coupling)、分岔(bifurcation)、确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和初始状态敏感性(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等。利用这些概念,动力学家试图理解认知系统的过程和行为。他们用微分方程组来表达处在状态空间的认知主体的认知轨迹,特别是通过在一定环境下和一定的内部压力下的认知主体的思想轨迹来详尽考察认知。认知主体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微分方程的支配。系统中的变量是不断演变的,系统服从于非线性微分方程,一般来讲是复杂的,是确定的。
目前动力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动力系统模型的实例[27]。这里,我们只简述一下汤普森(E. Thompson)和瓦雷拉的神经动力学的“互返的因果关系”(reciprocal causation)概念[28],因为这个概念是关系整体论(relational holism)的动力系统中的作用的一个一般形式,即部分-整体的互返关系。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在动力系统中,局部和全局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既有局部到全局的上行的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也有一个全局到局部的下行的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应该说,这和解释学循环的结构是同型的。
近年来动力系统理论也被用到动作发展的机制上。多年以来,动作的发展曾被认为是随神经系统的不断成熟,逐渐实现对肌肉日益准确控制的过程和结果。著名神经科学伯恩斯坦(N. Bernstein)对此予以质疑,指出单有神经系统并不能解释复杂动作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动作的发展中,不仅仅是神经系统如何实现对肌肉的控制,同时也涉及肌肉活动、重心引力、活动平面的支撑等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协调,后者不是由神经系统预先设定的,而是机体借助活动经验掌握的。
[29]西伦将动力系统观引入儿童发展研究[30],她对婴儿行走和踢腿动作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精确(fine)动作模式的形成和转变是神经系统指令与身体姿势、肌肉重量、肢体长度、动作活动的环境条件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动作依赖于动作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在发展机制的问题上,动力学理论强调动作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特定动作协调和控制性的提高来源于机体对特定生物力学问题的解决。例如,学习行走必须解决重心稳定问题,学习够取物体必须保持手臂的稳定性。这就是说,不是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导致动作的发展,而是动作活动提出的生物力学问题要求神经系统借助于不断的练习和反馈,实现对肌肉的有效控制。动作活动提出的生物力学问题不同,那么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必定不同。[31]
4 结语这些研究表明,认知并不单是在脑神经系统中的表征的操作;确切地说,认知最初是在活的身体的界面上进行的,只是到了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到了符号语义的阶段,认知的内在表征方面才高度发展并成为认知活动的重要领域。在这个阶段,有赖于符号语义特性,认知不再局限于实时的(real-time)的环境,人脑的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为离线(off-line)认知准备了一个内在的、想像力的空间,认知者不再非要处于实时的环境中和实际的对象交往,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认知成了处理心理表征的过程。这也正是认知主义所聚焦的阶段,但认知主义过于孤立地看待这个阶段而无视它的发展和起源。
具身认知作为一个范式必然有其最初的观念上的变革,它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先驱,目前逼近它的研究方法更是涉及众多领域。一个对认知更为全景的轮廓正在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1] Clark, A. An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1999).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ume:3, Issue:9, September 1, 345-351.
[2] 莱考夫在和布鲁克曼(John Brockman)的谈话("Philosophy In The Flesh":A Talk With George Lakoff)中再直白不过地认为:我们是神经存在,我们的大脑从我们身体其余部份接受它们的输入。我们的身体像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在世界中发挥作用塑造了我们用以思考的恰当的概念。我们根本无法思考任何东西——除了我们的具身大脑(embodied brains)允许的那些东西。
[3] Ziemke, T. (2001). Disentangling Notions of Embodiment[J]. Workshop on Developmental Embodied Cognition, Edinburgh, UK, July 2001.
[4] 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M] /edited by Robert A. Wilson and Frank C. Keil. (1999). London : MIT Press. 244.
[5] Varela, F. J., Thompson, E., & Rosch, E.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9.
[6] Varela, F. J., Thompson, E., & Rosch, E.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72–173.
[7] Thelen, E., Schoner, G., Scheier, C., and Smith, L.B.(2001). The Dynamics of Embodiment: A Field Theory of Infant Perservative Reaching.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4: 1-86.
[8]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4.
[9] Thompson, E. (2001). Empathy and consciousness[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8, No. 5-7; pp. 1-32.
[10] Varela, F. J., Thompson, E., & Rosch, E. (1991). The embodied mind : Cognitive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7.
[11] G. Lakoff,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Basic Books, New York.
[12]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16.
[13] Riegler, A. (2002). When is a cognitive system embodied?[J] 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 Volume:3, Issue:3. 339-348.
[14]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4.
[15]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6-166.
[16]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3.
[17] Lorenz, K. (1982). Kant’s doctrine of the a priori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biology[C]. In H. C. Plotkin (Ed.), Learning ,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121–143.
[18]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上海外于教育出版社,2001. 17.
[19]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3.
[20]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50.
[21]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27.
[22]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36.
[23] Beer, R.D. (2000). Dynam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ve science[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ume:4, Issue:3., 91-99.
[24] Van Gelder, T. (1995) What might cognition be if not computation?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91, 345-381.
[25] Van Gelder, T. & Port R. (1995) It's about time: An overview of the dynamical approach to cognition[C], Mind as mo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
[26] Ashby, R. (1952) Design for a Brain[M]. Chapman-Hall, London.
[27] Eliasmith, C. (1996). The third contende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ynamicist theory of cognition[J].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4. 441-463.
[28] Thompson E. & Varela F. J. (2001). Radical embodiment: neural dynamics and consciousness[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5 No.10. 418-425.
[29] 董奇 陶沙 主编. 动作与心理发展.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30] Thelen, E., and L. B. Smith. (1993). A Dynamics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and Acti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1] 董奇 陶沙 主编. 动作与心理发展.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8.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