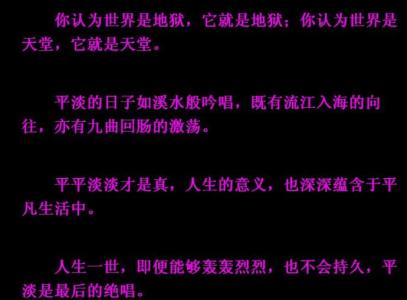夕阳在落山时的那片紫色的晚霞令人赏心悦目,麦田、桃林尽收眼底,右侧是通往北京城区的公路。斜阳照射着村庄,房顶和道边田地中泛着金色的光芒,村庄显得分外宁静、优美,远处一辆辆汽车在公路上奔驰。
我在北京郊区租的土坯平房座落在村子最西头(每月租金8元,我每月工资40。1元),两间单独的小房间,挨着院门。我的房东是个男的,四十多岁,是个哑巴,单身一人。我们之间因为语言交流困难,晚上从工厂下班回来,彼此各干各的事,避免了许多“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尴尬,落个清静。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离家,住到乡下。这里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世界,从小到大我都成长在城市,没有到过真正的农村。那时候社会上流动人口很少,很少有人会到农村去租房子住。我这个城里工作的陌生人在村里租房的消息,像新闻一样很快传遍全村,家喻户晓。每逢在村子里头行走,迎面走过的村民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
“大哥,吃饭了吗?”
“大哥,这里条件可没有城里好,住的习惯吗?”
……。
“还可以,谢谢!”我总是礼貌地回答。
我们车间的李师傅是这个村子的人。他帮我在这租的房子。他说自从我住进这个村子,村里的姑娘们一下子变得喜欢梳妆打扮,衣服也愿意穿平时最喜欢的衣裳。那个年代城乡差别比较大,挣工资的人几个月的工资比农村全劳动力,一年劳动分红时得到钱要多,找个挣工资的人把自己嫁出去,成了当时农村姑娘的奢望。
不过我可没有心思注意这些,保持一种神秘和陌生这是我在这的生活原则,许多事情都在等着我去做呢。
星期日休息,我开始安装土地电的工作。用了一天功夫,上午挖一个坑,下午一个坑,两个坑相距五十米,深2米。坑越往下挖,向上送土越困难,累得我腰酸腿疼,但总算完成了。负极是铅棒,我用工厂废旧电缆,剖开取出中间电线,再把外面的铅皮敲平,然后像消防水龙带一样卷起来,用铁丝捆绑结实。铅皮前端钻孔打眼,用螺丝螺母固定电线,再使用沥青把连接处封好防潮。好家伙!份量挺沉,从工厂运到村里一路上压得我的28型飞鸽牌自行车前把直打晃。正极是炭棒,我把它放到2米深坑底,铲土把炭棒埋起来,用脚把土踩实,顺出电线,把电线架高,拉电线进屋。拉电线必须沿着农户的房后和墙边走电线,这就需要征求邻居村民同意,我只好挨家挨户去又说好话,又递香烟的同邻居村民商量。
“这电线夏天会不会把雷引到家里来?”邻居村民问。
“不会,你看哪棵树都比电线高,放心吧!”我一遍遍地解释。
就这样,终于把测量大地电流的电线拉进家里,将电线连接在桌子上面的表头上。
第二天,我又成为村里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什么亲眼看见我在地下埋起来两台精密仪器……。
什么‘哑巴那房子’是地震局的一个观测点等等。
我在这个外界各种干扰小的僻静小村,建立起一个业余地震观测点。随后,自己又陆续制作了磁偏角和磁倾角仪,观察唐山大地震后的余震对磁场和地下电流产生的变化情况。我每天坚持使用无线电接收机,监听地震电磁波对无线电传播的干扰程度,进行地震观测和地震预报。
那时候,村里最“引人注目”的,就算我这两间小屋了。土坯垒墙,秫秸盖的顶,白纸糊窗,木板钉门。一根根各种用途的电线引进室内,说不尽的高深莫测,道不完的乡村韵味。
村里还住着一位高人,这个人就住在李师傅介绍的另一农户家。当时,他和我一样都是租房户,他是现在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导师张祥龙博士。张祥龙租的房子是一间过去用来当厨房的小耳房,比我租的房子要小。那时候张祥龙和我同在一个铸工车间,他是磨砂轮工,从事的工作又脏又累。张祥龙是个极有头脑,白净脸,留着小胡子,一看就是很有性格的人。他喜欢打篮球,是我们车间篮球队的主力中锋。他是六八届中专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学生分成两大派组织四三派和四四派,他是《四三战报》的总编辑,曾经与他哥哥一起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新思潮》,其中有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是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去除特权阶层,让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转变为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等等。于是被上海《文汇报》批判,被扣上“现形反革命”帽子接受学校批判,两次被专案组关押,自然被划成“问题学生”一类,参加工作和分配工种受到影响,就这么进了铸造车间,当上磨砂轮工。张祥龙为人清高,在工厂很少讲话。张祥龙住在农村,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学习,他在攻读和研究西方哲学。他的父亲是中国某部委的高级总工程师和我的母亲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他的父母都是解放以前的大学毕业生,属于那种世代书香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和张祥龙很快成了常来常往一起谈天说地的好朋友。交谈中张祥龙一改过去沉默寡言的习惯,谈论起自己的观点,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那时张祥龙虽然是个工人,他对哲学的理解,对哲学观点的领悟,已经到达一定深度。我也从与他交往谈话中,学到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全新知识,尤其认识事物,思维方法更加富于哲理,受益匪浅。

粉碎“四人帮”以后,沉闷的国家呼吸到了久违的新鲜空气,人们压抑很久的各种思想开始萌动,人们开始重新思索,讲起话来也不像以前那样谨小慎微。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既然哲学是自然科学认识的真理,那么哲学家就可以站在一个高度上,对未知的科学难题进行指导,从思维方式,精神心态,物质变化几个基本侧面进行分析。在一次我和张祥龙谈话时,张祥龙从哲学的角度,对我搞地震观测进行了概括。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要全国人民学点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中国知道的人不会占少数吧,即使不喜欢学习的人恐怕也是略知一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等于善恶,而且无所谓善恶,它们只是哲学上的两种学派。从近代以来,唯心主义在西方世界思维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什么是唯心主义?精神第一,物质第二。这里我们不必争论谁是第一才正确,比如:“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总是对的吧!精神作用于物质,精神第一。再举例子,你使用无线电观测地震的方法,提出地震电磁波的设想,然后进行研究探讨,这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也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在许多科学发明和科学发现中,科学家们都要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设想问题,研究未知领域科学家常说一句话“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所以形而上学观点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哲学家曾经这样形象比喻:
形而上学是树根,
物理学是树干,
其他自然科学是树叶。
目前,地震预报没有理论,人们正在探讨和寻求这门知识,当你偶然间,发现地震能量场对无线电传播有影响时,第一时间你就提出地震电磁波干扰概念,并顺着这个思路每天去观察和分析,这样你很快熟知了北京地区上空无线电传播正常变化情况和规律,也掌握各种电磁波干扰的基本特征,就有可能从干扰信号叠加的异常电磁波中,分辨出地震电磁波。
地震预报有意识的去认识,实在是不容易,依靠一点一滴地积累地震电磁波异常信号的解释,依靠日复一日分析对比和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使对地震的认识逐渐螺旋上升。地震预报,是世界上的难题。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目前向地下打钻最深才达到12公里,所有地震观测不能直接观测震源,而是间接通过某一种介质反映震源的变化,在观测过程中干扰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哺育着各种可能性的可能。探索地震预报的道路不仅仅需要战胜地震的信心,更需要挑战世界难题的务实监测手段,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历史责任。
什么是世界难题?因为它确实存在,它离人们思维方式很遥远,很陌生,很古怪。世界难题的研究当前是否到了转换观念的关头?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分析型、证实型的科学思维,只有打破常规才有新思路产生。场与场之间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不是线性规律变化,而是几何规律变化,就像“正方形的对角线不能用边来测量”一样。思维进行的样式,行为选择的方式等,在一定意义上规定着明天和将来。
每一个行业中的师傅都有真才实学,他们的一招一式既有基本理论,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操作,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你在观测地震中,你也会很有经验,监听方法得到三维空间数据,对各种干扰进行层层分析,从整体上,变动中,从多层次,多侧面去把握它们。但是,你和别人交流起来一定显得困难,比如:你想形容一种声音像什么一样。每一个人对一种声音像什么样子,是根据自己过去记忆对这种声音产生形象,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形象。我建议采用录音方法代替监听方法,录音磁带作为资料,想办法把资料送进地震研究所,做磁信号转换电信号进行分析对比,辨别出什么波形来自什么干扰。现代科技水平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想的结果,对各种信号准确分离目前可能无法做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这些问题总是能够解决。总之,地震预报谁知道监测什么有用呢?可以多途径探索,任何实际监测方法,哪怕只是反映地震的某一个侧面,也是接近地震预报理论一步。
在科学实验中,对于光的波(波动)粒(粒子)二性,微观粒子测量的不确定性、粒子能量的量化等,用牛顿力学的机械论是无能为力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玻尔用“互补性原理”加以说明,这一思想得益于阴阳互补,所以玻尔要求以“太极图”来象征自己的发现。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研究了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的文献,认为“道”和“气”与现代物理学的“场”概念一致。老子在道教中说:“道守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哲学思想对新的未来科学将与古老的“道”观念相融合。我们更渴求创新思维赋予的力量,这份力量带来不仅仅是冲出桎梏的途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黑暗中看到曙光。
听了这一番有指导意义的讲话,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是那么雄辩有力,那么深刻,好象给人们某种灵悟。
我在农村的土坯平房生活了两年,两年的沧桑岁月,身体不适应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土坯房没有水泥地面,土质的地面阴暗潮湿,其实冷风、阴气和潮湿都是变幻无常的恶魔,像无形杀手威胁着健康。第一年,由于自己身体素质好,没得什么病挺过去了。第二年,我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手指关节出现肿大,病得不轻,患上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很长一段时间中药治疗才慢慢好。由于长期监听无线电电磁波杂音,又得了突发性神经性耳聋,耳朵听力严重下降。马上到北京同仁医院住院治疗,幸亏及时输液、打针、吃药才恢复听力,痊愈出院没有落下残疾。这样,我不得不告别农村小屋,恋恋不舍的搬回市区家中去住。
平坦舒适的人生就像一条平淡直线,生命在于体验。人的一生如果只是去观看别人的精彩,自己就感受不到人生的真谛。在农村两年的时光,也长也短,人生的许多往事已随着时光流逝渐渐地遗忘。但是我心灵深处对这个小村庄的印象却怎么也挥之不去,让我总也不能忘记。
后来,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们俩先后都考上大学,张祥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上大学的,如愿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