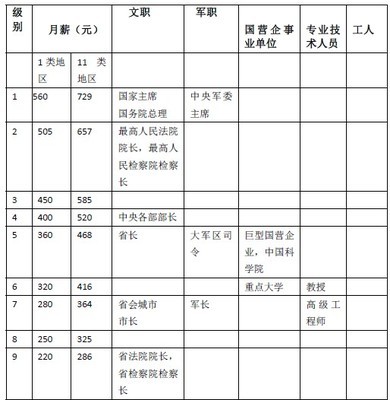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关键词:关系网络 社会运动 维权导 言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研究方法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的故事:一个持续十年的社区环保运动绿街:一个跨阶层居住街区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反对房产开发商的集体抗争网络稀缺和失败的初始集体行动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运动领导权的转移和抗争形式的变化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文革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文革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文革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街区关系网络发育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对地方政府的集体抗争绿地属于谁:地方行政权力话语和居民权益话语之争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再次冲击工地与警察上门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法轮功”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绿化卫士”:高层政府伸出援手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地方当局的“摆平”手法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维权积极分子的反击策略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作为维权市民抗争武器的关系网络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两个小区在运动中的差异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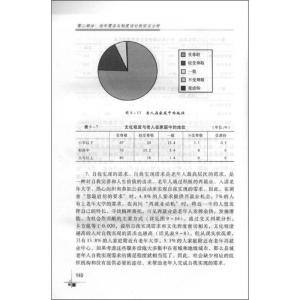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关系网络在市民建构集体抗争中的作用动员运动领导人和普通参与者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获取高层权威支持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收集对手的信息和违法证据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结 论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