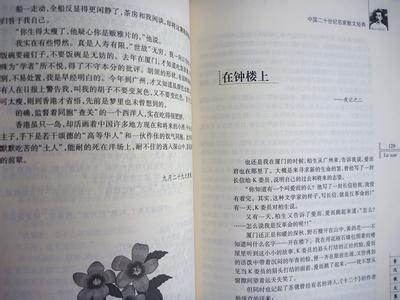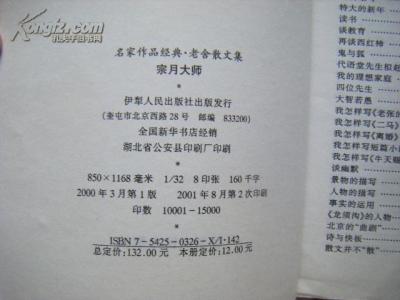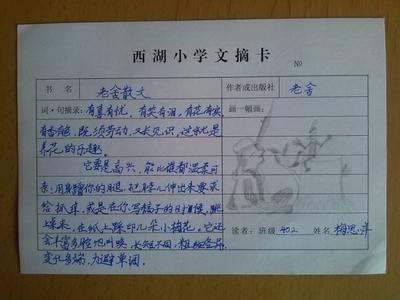书香亭外的柳树拖着长长的枝叶,微风吹来,柳树的枝叶翩翩起舞,优美极了!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弯腰老柳树散文,供大家欣赏。
弯腰老柳树散文(一)
元宵节的礼花在空中绚烂地绽放,春天轻轻地移动着脚步,在柳树梢头悄悄地缀满着早春的信息,前来凑着上元节的热闹。我和春天一样,也爱在清静中追逐着节日的欢闹,便在正月十五这天,和老公一起,沐浴着温和的春阳,漫步在小城郊外的一处灵秀之地---颍河湾,追寻着早春的痕迹。颍河湾不愧是一处灵秀之地,这里岸曲水缓,旷野无垠,春柳吐信,鸟鸣枝间,农家屋舍井然有序,本市的很多文人经常到这里寻找创作的灵感,我不是文人大家,也不免因这里的灵气而心有所动。我随手扯下一根泛着淡青色、萌动着点点春芽的纤纤柳枝,柔柔地舞在手中,于是,思绪便像南归的燕子一样,追随着在头顶掠过的飞鸟的痕迹,穿越了地域,穿越了时空,飞回了我的家乡,飞回了我的童年,栖息在我家老宅门前那棵弯腰老柳树苍劲的枝桠上。
弯腰老柳树散文(二)
弯腰老柳树是棵不能成材的老树。说它老,具体老到什么程度我说不清楚,模糊的记忆里记不清爷爷说过的话,老柳树可能是爷爷的爸爸也可能是爷爷的爷爷年青时栽下的。说它不成材,则是因为它的躯干粗矮弯曲,像是一位驼背的老人时常佝偻着腰,而且在树干弯腰处的下方有个硕大树洞,黑漆漆的,像是老树敏锐的眼睛,洞察着纷呈世界的万般变化。记得小时候,我常和爷爷手牵手地合抱才能把粗粗的树身围住,调皮的哥哥用力一窜,就能用双手拉住老柳树的枝桠,身子一缩,两脚使劲往上一跷,迅速用双脚攀着老枝桠,然后再敏捷地一转身,便会像猴子一样骑在树杈上。
我的家乡是豫东平原的一个小镇,柳树是家乡最平常最普通的树种,荒滩地头水塘边都有柳树的踪影。记得小时候,家乡人有在春天吃嫩柳絮的习惯。但是,有的柳树结出的柳絮苦涩难以下咽,人们称之为“苦柳”,而我家的弯腰老柳树结出的柳絮虽有一种淡淡的清苦,但是苦味中更有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清香,吃在口中简直就是一个“爽”,人们亲昵的称之为“甜柳”。因此,每年的春天一到,老柳树刚刚发出新芽,嫩绿的柳絮刚刚开始在枝头上嬉笑着簇拥扮俏,左邻右舍的孩子便会瞪大贪婪的小眼睛,拿着长钩,像猴子一样蹭蹭地窜到树上,于是老树上空便会传出树枝“咔嚓、咔嚓”被折断的声音。一向温和的爷爷这时会像暴怒的狮子,从地上捡起一根被折断的柳树枝,用力地挥舞着,大声地恐吓着、责骂着调皮的孩子。爷爷这时虽然暴躁,像守护神一样守护着老树,但是他也会派哥哥找来三叔,让三叔上树捋柳絮分给邻居们。

三叔是个干练敏捷的人,只见他拉住弯腰老柳树的粗壮的老枝桠,一纵身便跃上了老树,然后又三下五除二地攀上老柳树一根粗壮高大的枝桠的分叉口。三叔调整好最佳最稳的站姿后,放下一根长长的绳子,树下的爷爷把一个竹篮系在绳子上,三叔就把竹篮拉上,挂在一个树杈上。三叔常常一手拿长长的木构使劲把柔顺的柳枝拉弯,一手顺势捋柳絮,等竹篮满了,三叔就把竹篮用绳子放下,爷爷把它倒空,三叔再把竹篮拉起,挂在树杈上,继续捋柳絮。
那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家烹调柳絮的方法,但是我们家是把鲜嫩柳絮洗干净,在滚烫的开水汆一下捞出,再放到凉水里冷一会,再捞出,挤干水分,放进小盆里,撒上食盐,浇上酱醋蒜汁,淋上小磨香油,用筷子拌匀,吃到口中,淡苦中有一种和着蒜味的清香,让人觉得这真是人间最美的佳肴。每逢奶奶把凉拌好的柳絮放到桌上,兄弟姐妹们便会一哄而上地疯抢,我天生愚钝,没有能力抢过他们,其实是我不敢和他们争抢,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使劲的翕动着鼻翼。爷爷这时总会及时出现,扒拉开他们,用筷子给我扒出大半碗柳絮。我接过碗筷,来不及细细品味,便风卷残云般吃完,然后还余味无穷地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当我恋恋不舍地把小脸从大碗口中掏出,看到的是爷爷笑眯眯的眼神和咂巴着的嘴:“贪吃的丫头,你想馋死爷爷呀!”我猛然意识到,忙乎半天的爷爷竟然还没尝到蒜拌柳絮的味道。
小时候,爷爷是方圆几里有名的蒸馒头大师傅,老人家蒸馒头的技术是一流的水平,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请爷爷帮忙,但是,在我的眼中,爷爷的“巧”并不在饭菜做得咋样,而是爷爷的柳帽编得漂亮,柳笛拧的是超水平的绝。那不,就在叔叔在树上忙着捋柳絮时,爷爷则悠闲地捡起地上被孩子们折断的树枝,编起了柳帽,拧起了柳笛。爷爷编的柳帽毛茸茸的,不但有很多柳叶和柳絮,而且还偶尔会掺杂几根野草、几朵野花,哥哥戴在头上像是威武的解放军侦察兵,我戴在头上就像是美丽的小村姑。爷爷拧的柳笛有粗有细、有长有短,小拇指粗细的柳笛,吹起来像号角发出“嘟嘟”的声音,浑厚粗狂,像是沧桑的老柳树在为自己漫长的生命历程引吭高歌,如纳鞋底的绳线粗细般的柳笛,吹起来“滴滴”地响,美妙悠扬,像是沧桑的老柳树摇着摇篮,哄睡着自己的婴孩,哼吟着悦耳的摇篮曲。
爷爷虽很大方地把柳絮分给左邻右舍,但是却吝啬地不肯把柳帽和柳笛送给邻家眼热的孩子们。爷爷怜爱地把柳帽戴在我们兄弟姐妹头上,把柳笛分给我们,哥哥姐姐妹妹们戴着柳帽吹着柳笛神气地在街头巷尾疯跑,屁股后面跟满了羡慕的孩子。我则在很多时候留在爷爷身边,养着痴痴的小脸问爷爷:“爷爷,你的手咋恁巧?”爷爷总是笑呵呵的拍拍我的头:“不是我手巧,是老柳树的柳枝柔韧性好,是我孙女聪明,不用学就能把柳笛吹得像弹琴一样好听。”“你说我聪明?别人都说我傻,我傻吗?”“谁说你傻?你才不傻呢,俺孙女心里是透精透精的。”
爷爷中肯的夸奖让我自信倍增,我戴着柳帽,骑在老柳树的弯背上,吹起了柳笛。蓝天上的白云仿佛被我的笛声拉住似的,时而团团簇簇,时而散云朵朵,悠闲地飘飘悠悠,总不肯随风而去。不远处清涟荡漾的池塘里的小鱼,也好像听到了我的笛声,吐着小水泡,探头探脑地寻找着春天的信息。老柳树枝头上的小鸟和着我的笛声,叽叽喳喳地唱着春曲,为春天增添着美妙的旋律。爷爷悠闲地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着老柳树粗粗的树干,眯着眼睛,享受着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最动听的音律,偶尔间,老人家还会扯着嗓子唱几句跑调的地方戏:磨屋里走出我王汉希,我一脚高一脚低,我透骨寒冷穿湿衣,一身湿还有两脚泥,要借粮见人见不的......”。爷爷唱的是我们这里著名的“太康道情”《王金豆借粮》里的经典唱段。
弯腰老柳树散文(三)
小的时候,我很傻,具体为什么说我傻,我在混沌的记忆里找不出答案。四岁的时候,母亲的撒手人寰,让我对母亲的音容相貌无从记起。我只知道,从那时起,一抔黄土、一座荒冢从此让我们兄妹几人与母亲阴阳两隔。本来呆痴的我更加木讷,像是老柳树秋天随时要飘落的树叶无所靠依。有时候我会衣衫褴褛,有时候我会蓬头垢面,有时候我说话会支支吾吾,语言表达不清,有时候我会像流浪者一样愿意在外游荡而不愿意回家,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家有个傻妮,小朋友们不愿意和我结伴玩耍,兄弟姐妹们出去不愿意承认我是他们的姐妹。
弯腰老柳树树下常有孩子们在玩捉迷藏、跳绳、踢毽子、砸沙包,过家家等游戏,我也常常一人痴痴呆呆地吸吮着手指头地远远地看着,有时候,会趁人不注意,偷偷地爬上老柳树,坐在老柳树的树杈上静静地看着小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玩,静静地聆听着他们欢快地笑。有时候,我特别想和姐姐妹妹一块愉快玩耍,便很多次傻乎乎地跟在她们后面。伶俐的妹妹总是噘着的小嘴,满脸委屈地嘟囔着着我:傻子,二百五。聪明的姐姐也总是不分黑白地袒护着任性的妹妹,连推带搡地把我一次次赶出她们玩耍的圈子。我最后的选择总是眼里噙满泪水,无声地爬上老柳树,独自在自己的世界里想入非非。老柳树是我儿时心灵的栖息地,是我儿时的乐园。
说来奇怪,缺乏安全感的我,心中总有一种惶惑和恐惧,整天战战兢兢,我不敢回家,回家怕家人因为我的傻讨厌我,我不敢出门,出门怕因为我的呆邻居歧视我、小朋友欺负我。但是,每当我爬上老柳树,背靠着老柳树粗壮的枝桠,好像躲进了爷爷温暖的怀抱,好像漂泊的船儿驶进了温暖的港湾,内心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安静,思绪就开始信马由缰地奔跑,什么惶惑、什么害怕、什么悲愤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特别是在夏日的晚上,我在兄弟姐妹还有其他小朋友们的喧闹中悄悄地爬上弯腰老柳树,坐在老柳树稍高的枝杈上,让柳树浓密的枝叶遮住我小小的身子。我悄悄地晃动着树枝,会有小鸟惊叫着扑棱着翅膀,也会有夏蝉尖叫着嘶鸣。在有月的晚上,月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斑斑驳驳地撒在我的身上,月光下的柳枝像调皮的精灵在我身旁舞动,月光下柳叶的影子影影绰绰地跳跃在我的身上,我好像走进一处神秘的童话王国,想伸手抓住它们,又怕我的唐突惊跑了调皮的小精灵,再一次留下孤寂的我,只好作罢;在无月的晚上,我仰头看着缀满繁星的天空,用心地寻觅着爷爷故事里常讲的牛郎织女星。有时候,会在偶然间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小小的脑袋里开始琢磨着:是不是又有人将要想我的母亲一样无声地离去?顿时,心中开始充满了伤感。
夜在我的幻想中悄悄地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玩累的孩子们早已散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在星星在月亮的陪伴下,搂住树枝朦胧地进入了梦乡。“美美,美美,美美......”我似乎听到了爷爷高一声低一声急促地呼喊,睁开朦胧的睡眼循声望去,只见夜幕中的爷爷站在老柳树下焦急地东张西望,我“哎”了一声,朦胧的夜色里,爷爷急忙抬起头,下意识的伸开双臂,好像要接住要从树上摔下的我。我调皮的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下,钻进了爷爷的怀抱,爷爷佯怒地把手高高地举起,又轻轻地落下。于是,爷爷拉起我的小手,我们一同回家,爷俩的身影便迅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