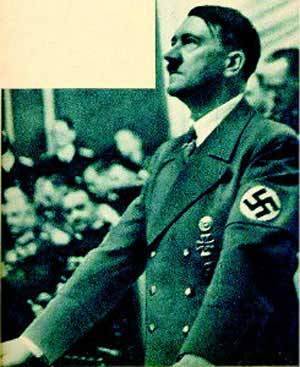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以南北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就此结束。如果说历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话,这却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诸多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促成统一的因素却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其言语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移民的往来打破了这种隔阂,因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总是要交流的,他们就会寻找出新的交流约定来。西晋后洛阳的正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及东晋长江下游扬州“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而且“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与此相关的是,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族的本族语言也渐渐地在生活中消失。语言文字的统一成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前奏。
其次是生活习俗的混一,主要在于游牧习俗与农耕生活的相适应。本时期的民族问题,不是在边境上的攻战,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处。其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步:第一是交往;第二是杂居;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为准则的认同。对少数族的上层,农业化和汉化是一致的。为了统治,他们要与汉族打交道,就会率先学习汉语言文字,如稽胡“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这种结果是惊人的,“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后期竟需“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接下来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风气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药数动发”。其中一个动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或威权。但往往这两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层。一旦下层族众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难以逆转了。

再次是水陆道路的打通。路是人走出来的,军队的征讨,民众的迁徙,商人的贩卖,行僧的云游,都会把路走得更多更广。士兵、移民、商贩、僧人是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人们,他们的往来带动了道路的发展,也带出了统一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适应南征北战的需要,自曹魏起在水利上开始做两件事。一是配合大规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统,如当时“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即使前燕这样的政权,也因屯田而“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二是开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所以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这些水道的开凿或疏通,无疑为隋代的大运河开通打下了基础,并使以后隋唐的大统一少了几分地理上的障碍。由此尽管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交往却很寻常,证据之一就是诸朝的商业税越来越成为官方的重要收入。不仅“河桥孟津,解券输钱”,就是沿途旅舍,也对“交易贸迁”者“依客舍收钱”,追求末利。东晋南朝更是如此。证据之二是南北之间还常设“互市”。早期如前秦苻健“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后来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地方上如魏崔宽为陕城镇将,以“恒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又如北魏占领淮河流域后,“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问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但也有人一下子购得鳆鱼三十枚者,可见交易量还是不小的。即使在打仗时也未停止,如高季式“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而这种商业上的利益,致使北魏缘边州郡的官员“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另一边如梁时“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凡此,可见南北边境交易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魏分东、西后,“士人仍缘姻旧,私相贸易”,虽有禁令,但“犯者非一”,后来不得不放松。又如北齐“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苏琼为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后,听两淮通籴粮食,“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这种情况当然是促进统一的因素之一。
最后落实在一统观念的强化。当时南北分裂,但交往频繁,南、北朝间国书往来,本来的套话是“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为“欲示无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抛,并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至于深层观念上的趋同更是无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后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约公元500—550年),南北双方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文化交流频繁,装饰艺术风格,特别是装饰题材、造型及纹饰渐趋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与北魏巩县石窟内顶装饰图案题材的一致、神王异兽等题材在北朝后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审美上的一致也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有了长期的和平稳定,关中和中原不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传统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于是在物质与心理的支撑下,谁占有中原,一统天下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名正言顺的尊王攘夷之举总会使人跃跃欲试。魏孝文帝当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其臣下呼应:“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埘。这种豪情壮志苻坚有过,拓跋焘有过,但客观形势都未成熟。宇文邕灭北齐后统一的条件是具备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杨坚建隋后的灭陈之策是这种意愿的自然延续。这些都说明无论北方的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少数族人,要求统一的主观愿望总是强烈的,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场景呢?在南边,自刘裕建立宋朝起,“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在与北方的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刘裕是一个出色的统帅,但为了确保夺取东晋政权,他匆匆从前线返回建康,致使先机尽失,关中沦陷,元气大伤。宋明帝时,青、齐诸州又为北魏所有,大体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线。“南北朝对峙,其国势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齐之地一役”。齐、梁两朝无大变动,缘淮为界而互有攻防,对峙下还能基本保持平衡,不过由于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两淮残破,无法成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势。梁末由于侯景之乱,使继之而起的陈朝境土局限于长江之南,“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江左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残破不堪,如《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条云:“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这样南朝就失去了与北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基础。
此外,对南方政权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顺流而下之势;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仅建康暴露,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策中,就以“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一旦决定伐陈,蜀、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南军不重兵抵御,必乘势而进,如聚船与之决战,则江防空虚,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顾此失彼。因此到了陈朝,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
但从长远来看,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东晋南朝的门阀,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但毕竟来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轻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气不振。而北方少数族历来尚武,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齐时又得到重振。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北朝所铸钱币的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上,北方也优于南方。再者,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这也是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因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两淮至为重要,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备集足够的车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圳,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奔袭,但南方是难以弄到这么多的马匹的,直至魏晋之间,农耕区域的主要养马区“实在冀北”,这个地区当然也归属北朝。何况当时北方骑兵已装备了马镫甲具,冲锋作战时更是势不可挡。北魏“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后来北齐曾“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虽然其目的在于榨取当地土豪钱财,但南北骑兵基础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见,因此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
然则基础于上述这种种的分析与比较,等到隋朝建立后,由北方完成统一,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尽管儒家推崇王道与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统,就得用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见不到有和平统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临城下的时候。就象晋灭吴的形势一样,隋朝结束南北朝的时候,又重复了南下统一的场面。
客观上是条件成熟,大势所趋,主观上是要建立功勋来巩固轻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于开皇八年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十二月,南下诸军临江出发。虽然从力量对比上看,由周军转化而成的隋军在灭北齐后士气正旺,而南军主力在吴明徼北伐后已丧失殆尽,隋伐陈是以石击卵,当无悬念,但隋还是十分慎重。首先在当年三月,一边遣使至陈试探虚实,一边颁诏罗列陈后主劣迹,以造舆论。此前,更是采用高的计策,因北方收割早于南方,屡屡在北边农事毕而江南正农收时顿兵临江,陈朝征兵防御,几年下来,废农困弊,又被麻痹;陈又不自量力地挑衅:“时后主与隋虽结和好,遣兵度江,掩袭城镇,将士劳敝,府藏空竭”,更给了隋军动手的口实。其次隋动用兵力很大,“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舰只,其中大者有楼五层,容战士八百人,南方已经没有水军优势。再次是多点渡江进攻,“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这样不仅是气势压人,而且使陈朝军队首尾难顾,其策略和西晋统一时差不多。加上陈后主初无准备,隋军势如破竹,合围建康,并迅速破城。隋开皇九年正月,陈后主被俘,陈亡。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役有关并影响以后历史发展的是,这次伐陈,是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总统诸军。为什么不用太子杨勇率军呢?其实对当时隋朝而言,更危险的敌人是北边的突厥。当时突厥强盛,时常犯边,数越长城,关中震动,所以开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开皇六年秋,杨勇又移镇洛阳。杨勇的任务虽然重要,防范好突厥是保证灭陈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却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杨广灭陈后,杀陈之佞臣施文庆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后来杨广能夺得太子之位,虽然有其他的原因,与此却也不无关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