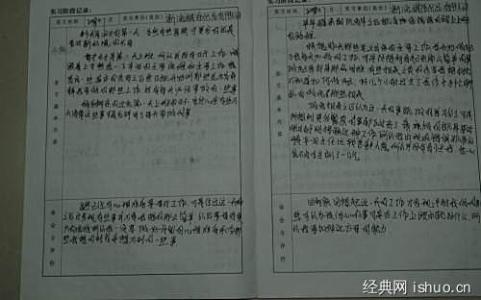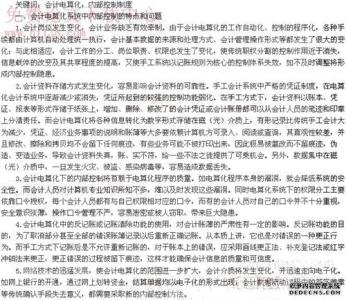在现代国家,宪法集中反映了特定社会各主体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志,司法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对其改革不应当也不可能会超越宪政的实然状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宪法学士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浅谈宪法学士论文范文篇一
《 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 》【摘要】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而言,宪法解释是主要的和根本的方法。而解释的目的在于,让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能够互相通融、协调一致。作为这两种解释方法的链接点,公共利益的含义和规范意义是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公共利益的核心含义是公共目的。虽然通过法律可以了解公共利益的大致含义,但只有透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或者“宪法原则或精神”来解释确定一个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才能根据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而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在于,基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征收和征用应符合比例原则,以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含义;意义;公共利益;宪法解释;公私利益平衡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利益”是我国宪法上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首次出现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0条(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增修条文第22条(宪法第13条第3款)。[1]这两个条款通常被看作“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的宪法规范依据,即宪法上的“征收和征用条款”(以下简称“征收(用)条款”)。随着征地拆迁和补偿问题的日益突出,“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要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首先应当通过文义解释来确定其精确含义。[2]不过,虽然可以透过公共利益的本质要素——公共目的——来了解其核心含义,但由于公共利益的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已然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1}作为一项理由,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意味着应透过法律尤其是判例法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客观含义。然而,按照一般的公法原理,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的法治诉求与依法行政的原理是一致的。这一原理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正如权力分立那样,是自由主义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思想。因为,通过法律来防止对公民财产的行政侵害,并不能为公民财产权提供真正的保护,因为这样的规定没有设置对法律内容本身的防波堤。{2}(p.44)而且,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含义复杂且时效性很强的概念,在没有判例法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单纯通过成文法的“描述性定义”[3]根本无法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
既然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那又应当如何解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引发的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之现实问题呢?张千帆教授的观点非常中肯且较具代表性:“要保证政府的征收行为符合‘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在征收的程序控制上多下功夫。如果中国的全国和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能够对土地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那么目前困扰中国社会的征收问题将有望得到根本的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将得到根本的缓解。”[4]也就是说,“完善程序控制”特别是那种正当法律程序的控制,是确保公共利益的界定达成“社会共识”的主要手段。但是,完全求助于法律程序的控制,就会抛弃“合宪性判断”的路径,甚至有“抛弃”宪法之嫌疑。况且,“完善征收程序的控制”涉及到宪法解释问题,在权力链接程序严重欠缺和司法程序控制无法发挥效能的情形下,如何对行政征收的法律程序进行宪法上的“控制”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承认宪法具有最高效力的话,那么不管是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确认”还是“法律程序的控制”,都涉及到一个“合宪性控制”问题。
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会产生两种结果,即违宪性判断与合宪性判断。一般而言,为维护一国宪政秩序,在解释法律时应尽可能以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做合宪性判断,以确保解释是“符合宪法的解释”即合宪性解释。[5]不过,毕竟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具有高于一般法律的效力,[6]合宪性判断也只能以宪法而非法律为前提。如果不能明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如何进行合宪性判断?可见,要解释“公共利益”,宪法解释是主要的、根本的方法。而解释的目的在于,让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能够互相通融、协调一致。而问题是,如何对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才能够让这两种解释方法互相通融、协调一致呢?
二、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
要保持这两种解释方法互相通融与协调一致,需要找到它们共同的链接点。就公共利益的解释而言,由于宪法解释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属于不同的解释方法,前者是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后者是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做合宪性解释,所以两者的链接点首先体现在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是否相同的问题上。因为,如果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就应当保持一致。[7]但问题是,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呢?如果宪法或法律中的公共利益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可能就会不同。所以,必须对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进行分析,以便在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解释时能够明晰其确切的含义。
此外,要保持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即便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得到合理解释,也需要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因为,如果无法探求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依据”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把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混乱”以及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宪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公共利益——的头上,这跟明希豪森拽着自己的头发将身子从沼泽地里拽出来不是一样的吗?
一般而言,一个概念的意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该概念的核心内涵(即内容),与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蕴;二是指该概念的价值或作用。本文中使用的“意义”、“规范意义”或“意义范畴”,指涉的就是一个概念所涉规范的价值或作用。由此,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体现为一种“规范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规范意义上存在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含义”或“事实描述”。比如,宪法中的“行政征收”是一个法律概念,有其核心的含义,但宪法如果没有对其意义范畴进行规定的话,那么它的含义就是模糊不清的。我国宪法透过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为“行政征收(用)”的概念划定了一个规范意义,或者说,宪法为“行政征收(用)”设定了一个边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和“补偿”。当我们谈到“行政征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说,行政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做出,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经过“合理补偿”,就是无效的。所以,法律概念如果不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就不会发生规范效力,其价值和作用就体现不出来。由此,一个法律概念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够为法律事实提供一个解释的空间。
对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而言,只有当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依据时,其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如果只是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看作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在解释“公共利益”时必须在“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内进行。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只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一个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如果仅仅把“公共利益”看作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那么在解释其规范意义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或意义)是为征收(用)设定不得逾越的界限,而不是为“公共利益”设定一个意义范畴。[8]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虽然重视“公共利益”的含义解释,但忽视了该概念背后的“规范精灵”。这一方面源自于上述宪法条款的模糊性,而另一方面则与学者们试图开启宪法解释的历史命题有关。如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规定‘公共利益’时应当依据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规定,不得与宪法上的规定相抵触,这是宪法的最高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上有关‘公共利益’规定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它是宪法监督机构审查判断普通法律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的依据和标准。可以说,这是宪法必须规定‘公共利益’的根本意义所在。当然,目前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我国这一监督审查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9]2但是,如果没有抓住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而只是求助于这样一个宪法上“无法实证”的概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监督审查?司法机关又如何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呢?可见,造成目前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1)试图用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涵盖其可能存在的不同含义;进而(2),忽视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以至于(3),没有按照宪法的原则与精神来解释确定一个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
因此,在宪法解释学上,不仅要探求公共利益的含义,而且要抓住它的“规范意义”,才能真正解决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难题。具体说来,应当透过宪法并依托法律来找寻公共利益的大致含义(由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所决定的),并通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或者“宪法原则或精神”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然后,根据这个宪法具体化下来的规范意义来进行合宪性控制,以确保法律不脱离宪法所设定的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解释方法上保持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的协调一致。由此,含义与意义就成为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
三、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虽然透过“公共目的”可以了解公共利益的核心含义,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运行领域和规范目的,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这些不同的含义在以往阐释公共利益的文献里面,要么被混为一谈,要么被忽视,而这恰是造成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基于本文写作目的之考虑,在这里并不对宪法和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精确的含义解释(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指出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表述、运用领域、规范目的,并做符合本文写作目的之解释。
(一)法律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既有助于关照公共利益的社会现实性,也有助于明晰公共利益的含义。这是由于,宪法体现的是过去人民的意志,而今天人民的意志更多地体现为法律。而且,就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制度运行的缺失,我们认识宪法概念,可能更多地就要借助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以及社会的一般认知了。……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之下,毕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最具有权威性,也最有可能与宪法解释相匹配。”{3}{4}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出现,无论是在公法还是私法中,都可以见到“公共利益”的字眼。从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和规范目的来看,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含义表述。
第一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私法领域,被视为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如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物权法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这个层面所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是一种对私权利行使的法律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凸显了在社会层面发挥公共利益的限制性功能,以保持社会自身的团结与协作、稳固社会发展的道德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第7条采用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较之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这种表述明显扩大了对私权利的限制范围。而且,该规定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条款结构和表述方式上来看,物权法第7条中的“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相对应,物权法第7条中的“他人合法权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相对应。如果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判断的话就会发现,物权法的上述规定虽然没有超越宪法第51条的意义范畴,但将物权进行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非“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的限制,是否有违宪之嫌疑,颇值得认真斟酌对待。
第二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公法领域,被视为公权力行使的向度和准据。如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和单位、个人的不动产”;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行政许可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法典范,物权法将征收条款写入其中,使之具备了某种混合法的性质。这种做法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几乎完全照搬宪法条文的做法并不利于物权的保护。尤其是,该法第7条和第42条第1款的规范目的并不相同,前者限制私权利的行使,而后者限制公权力的运用。虽然这两个条款采用几乎相同的“公共利益”表述方式,有助于在同一部法律中的保持表述方式的一致性,但在进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目的解释时就会遇到困难。
这个层面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主要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而言,其目的在于防止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公权力滥用的威胁。在表述方式上,通常采用“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与前述运用于私法领域的含义表述不同,并不特别强调其社会性。然而,上述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虽然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 基本保持了一致性,但这种表述方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明显处于一种包含关系。问题是,这种公共利益除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以外,还包括哪些含义?如果说国家利益中的部分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即国家利益被排除在社会利益之外,并在制度规范层面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第三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公私法混合领域,与维护社会的公共福祉以及社会济贫、救援、健康、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密切相关,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4条规定:“国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注册会计师法第1条规定:“为了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鉴证和服务作用,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招标投标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 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制定本法”;信托法第60条规定:“为了下列公共利益目的之一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一)救济贫困;(二)救助灾民;(三)扶助残疾人;(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六)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
这个层面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既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也限制私权利。在表述上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偶尔会采用“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就含义范畴而言,“公共利益”的含义较“社会公共利益”更为广泛。立法目的之不同乃是导致上述表述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4条的规定为例,该规定是针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的——政府征收行为的限制性规定,按理说应当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表述方式保持一致,但是,由于该法之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所以对这种征收行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征收:一方面,将征收限定在特殊情况,即原则上不能征收;另一方面,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缩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前述的解释,排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征收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规定在解释上尤其是在合宪性解释上便会遇到困难,尤其是该规定是否会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相冲突,值得认真斟酌对待。而且,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上述表述方式(意味着公共利益的含义差别)的不统一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合宪性解释。
综上可见,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征收(用)条款中“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就含有“公共利益”用语的法律规定来看,除第二种运用于公法领域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表述以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为依据外,其他两个层面的“公共利益”都无法从1982年宪法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述。而且就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言,如何解释第一种和第三种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值得认真对待。尤其是,由于第三种公共利益的法律表述即传统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之解释涉及公权力的限制,能否单纯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给予解释,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以法律来解释宪法,这种由下而上的解释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宪法自身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洽的系统,否则就无法判断法律等具体化宪法实践的合宪性问题了”[4]。所以,要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还需要从宪法规范中去找寻它的真实含义。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1982年宪法全面修订时并不存在,虽然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增修条文第20条)和第13条第3款(增修条文第22条)出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但这不过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结果。在此之前,个人(财产)权益在各种权益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为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了个人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在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入宪法以后,虽然“依照法律规定”和“合法的”的限制性规定使该修正案逊色不少,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已然获得了宪法上的明确保护,应无疑义。
自“征收(用)条款”入宪以来,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干预私人财产权的一个限制手段,在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烈,并进而导致拆迁补偿利益冲突问题的大量出现。虽然法律的不完善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但从法制层面来看,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典型的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虽然一些学者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但很显然,既然宪法第51条并未直接使用“公共利益”而是使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那么就可以初步认定,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应不同于第51条中出现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首先,从含义的核心范畴来看,社会的利益未必符合国家的利益,而集体的利益未必符合社会的利益。或者说,有些集体的利益,并不属于社会的利益范畴,而社会的利益也未必属于国家的利益范畴。尤其是,公共利益的界定通常以公共目的作为判别的依据,比如医院和学校等属于公益事业单位,通常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载体。而一个村集体的利益可能既不属于村集体范围的公共利益,也不属于一定区域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一定区域的社会的利益,可能并不属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国家的利益也未必属于公共利益。[10]所以,宪法第51条出现的3种利益,可能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也可能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中,只有符合公共目的的部分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11]
其次,从立法目的角度来看,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是作为征收或征用的前提条件,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而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是作为公民权利行使的限制条件,目的在于限制私权利,两者之间在法律意义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最后,宪法上的第51条是私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宪法依据,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第55条、合同法第52条、物权法第7条。而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则主要是公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宪法依据,如土地管理法第2条、行政许可法第1条。至于招标投标法、注册会计师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经济法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条款,是否应完全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进行解释,以及是否应结合宪法第51条进行解释,颇值得认真探讨。
综上分析可知,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如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来得清晰。这是由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才“补充进来的”。而且,如前所述,含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对应的宪法条款并不一定使用“公共利益”的表述,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物权法第7条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但宪法第51条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且明显将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置于比个人利益更高的地位。因此,不能说宪法上只存在单一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也不能随意地将公共利益等同于“国家的、社会和集体的利益”。此外,宪法中还有不少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与公共利益发生勾连,这些条款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而是使用诸如“社会秩序”、“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国家秘密”、“公共财产”等概念。这些不确定性宪法概念的存在,也是导致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模糊及其解释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而如何理清它们与“公共利益”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有权机关做出合理之解释。
四、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及其解释
(一)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
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之含义区分,如上所述,除找到两者间一一对应的含义、明晰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运行领域和规范目的以外,还应当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以为法律的合宪性控制提供依据。如此一来,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就较“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有“特别的意义”。[12]那么,这个“特别的意义”是什么?是否如学者们所言,仅仅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立法依据”呢? [13]
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公共利益”的立法依据确实不假,但这只意味着,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应当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性(在理想状态下,对应的含义相同)。既然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 的(对应)含义相同,从宪法规范不易变动的角度来看,由宪法来界定公共利益似乎并不妥帖,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显然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的范畴。因为,公共利益毕竟是一个含义复杂且现实性很强的概念。或者说,这一概念完全仰赖社会生活现实并从中获得其社会的意义。
然而,即便法律照搬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也未必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具随意性。[14]也就是说,即便是法律界定了一个“公共利益”,那又能怎样呢?那就能解决“公共利益”界定的随意性吗?那种试图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获得一个含义依据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是将其归结为一种“特殊的意义”,也无异于解决问题。不过,如果说宪法作为法律的立法依据,指的是宪法规范对法律规范的意义,那也就意味着“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已经浸润了“规范性的精灵”,它不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宪法规范中的概念。如此一来,这种规范性的意义就成为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合宪性判断的依据,以防止它脱离宪法而自在自为。
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虽属法律(制定法,尤其是判例法)的任务,但它不能违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所谓的“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的说法并不妥当,将其表述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似乎更为恰当。由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什么?而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可否看作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呢?
从规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宪法规范条款都有一个规范意旨。这个规范意旨主要是设定某种或某几种行为的准据。与法律规范条款相较,宪法上的规范条款虽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在表述上也有特殊的方式,但任何一个规范条款都包括了“假定”和“处理”的基本结构。按照这一规范结构的要求,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似乎是无法导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的。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求助于对“公共利益”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宪法概念的解释了。然而,既不能先确定一个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再据此确定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也不能通过现实中的公共利益事件概括出一个公共利益的宪法概念来。因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只有在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表征,而且,要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那就无法对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进行解释。
问题的实质在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所涉的“规范性精灵”在哪里呢?这还得从“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所在的宪法规范条款中来寻找。回过头来看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重要的宪法规范条款中的关联性概念,甚至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宪法概念。既然如此,“公共利益”的宪法规范意义应当如何进行解读呢?
要探求“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首先应当求助于文义解释。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都包含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前提条件。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这个条件并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关联规定来看,“公共利益的需要”显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的话,那它属于描述性的还是属于陈述性的?如果“公共利益的需要”属于描述性的或者把它看作是法律应当对哪些属于“公共利益”进行规定的宪法规范性要求的话,那么在判断“公共利益的需要”方面,就只能求助于立法机关而不是宪法规范了,或者说,这样的解释无异于将上述条款看作是对法律的一种授权性条款。但是,这样的解释抛弃了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控制”,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也就成为一个纯粹授权性的条款了。但很显然,单纯将这一条款解释为一种宪法对法律的授权条款,并不适当。而且,宪法条文的简洁性和严肃性并不允许任何多余的、无意义的重复。“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做上述解释的话,就会与“公共利益”具有相同的含义。那么,立宪者就完全没有必要多写“的需要”这几个字了。显然,从合宪性控制和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角度来看,不能将“公共利益”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宪法上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
此外,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词——“可以”。这个词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为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为,如果“可以”表达的是一种宪法上的授权即行政机关可以根据社会情事来确定是否征收或征用的话,那么“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也可以解释为行政机关“可以不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征收或征用。但果真如此的话,这种解释就会与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性质相背离。所以,不能将“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解释为“行政机关可以不依据法律规定”来进行征收或征用。在笔者看来,可能的正确解释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表述方式隐含了征收和征用应以“必要性”为限度,也就是说,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收或征用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的要求。
适用必要性原则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公私利益平衡作为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已经确立下来。如果没有在宪法上确立一个“公私利益平衡原则”,那么上述解释就难以获得实证法上的依据。不过,如果能够解释认定我国1982年宪法已经确立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话,那么上述解释也就属于正当且合理的了。也就是在这里,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并成为宪法上的行政征收(用)条款的一个重要解释依据。
(二)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公私利益平衡原则被不少国家的宪法判例予以确立,并被用来解释在涉及私人利益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在美国,如同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一样,国家获取个人私有财产的强大权力是先于现代宪法而存在的,被视为“政治需求的必然产物”[15]。在早期,通常运用“公共所有权”的概念。[16]2其后,自2005年著名的“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案以后,继“公共所有权”和“公共使用”的定义方式,“公共目的”的定义方式成为一种更加宽泛的定义方式。[17]3从美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解释中发现,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使两者达到共存的状态,乃是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
在欧洲各国,对“公共利益”普遍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广义解释,以寻找公私利益之间的平衡点。[18]4比例原则的含义是:要确定某一项举措是不是为达到立法目的所必须的;如果是,那么这项举措是否很好地平衡了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19]5一般来说,如果征收当局能够证明以下几点,那么征收就是符合比例原则的:对财产权进行干预的目的足以使对私权的限制具有正当性;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这一目的在理性上是相关联的;干预财产权的方法不能超越为达成目的所必须的范围;干预财产权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不能是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20]6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年)第14条第3款规定: “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赔偿范围如有争执,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从该条款可以看出,财产征收行为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且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居于高于私人利益的宪法地位,而该规定可视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基本法原则的确立。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没有真正确立判例法制度(判例法作为成文法之重要补充,乃是当今大陆法系各国的普遍做法,由此导致普通法系与成文法系逐渐融合之趋势),公共利益只能透过法律的界定(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明确了“依据法律规定”)来完成,所以合宪性判断对于我国1982年宪法的实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要真正使合宪性判断发挥效力,除司法机关(宪法实施机关之一)作为合宪性判断机关的作用能够真正发挥效能以外,作为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必须确立为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此情形下,作为落实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比例原则才能在行政司法实践中有进一步解释和适用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在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征收或征用的政府行为时,往往忽视了该原则与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关系。事实上,行政征收(用)行为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必须以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为依据或前提,如果欠缺这个依据的话,比例原则在实证法上的适用就未必是正当的了。
然而,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之前,我国1982年宪法并未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确立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原则。从1982年宪法第12条和第51条的规定来看,公共财产、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并赋予国家特别的保护义务。但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列)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宪法以后,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否应当看作确立了宪法上的一项原则,颇值得学术界认真对待。
从历次修宪的背景来看,因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决断(该政治决断虽然最先以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但它最终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通过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并逐步强化了私人财产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为公私利益平衡原则成为我国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历次修宪情况来看,1982年宪法至今共通过了4次宪法修正案,这4次宪法修正案逐步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1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第15条,1993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5条第1款,1999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第13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2条)以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第11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1条)写入宪法,从而使合法的私人财产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取得了重要的宪法地位。从历次修宪的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逐步加强,使之不再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从体系解释的视角来看,1982年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从这两个条款前后相继的关联性可以看出,虽然在公共财产保护和私有财产保护的用语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现行宪法力图在公共财产保护与私有财产保护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原则还是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权的入宪和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规定,标志着我国现行宪法已将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确立下来。而且,从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来看,行政征收(用)的补偿(普遍解释为合理补偿或公正补偿)限制,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原则在1982年宪法中的确立。不过,该原则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阐释,但基于本文写作目的之考虑,留待以后另文探讨。
【注释】
[1]增修条文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增修条文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拉伦茨认为,“文字的解释都始于字义”。[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25页。
[3]在法解释论上,以描述性的定义,特别是以“外延定义”对某些法律概念进行阐释时,常常会具有广义的取向。但从排除价值化取向的面向上来看,该解释或定义方式最能符合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参见李惠宗:《案例式法学方法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10页。
[4]张千帆:“‘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的宪法解释”,载《南方周末》2005年8月11日。张千帆教授所说的“完善对征收决定的程序(而非实体)控制”指的应该是“完善征收的法律程序”。这种观点与前述“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因为,“由法律确认”虽然指向的是一种实体价值,但表达更多的是,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方式来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5]德国学者Hesse认为,合乎“宪法”的解释不仅要探寻正要审查的法律的内容,而且也要探寻依据来审查该法律的“宪法”的内容,在合乎“宪法”的解释过程中,不仅需要进行法律的解释,而且需要进行宪法的解释。因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不仅基于实体而且基于功能的整体规范的考虑均指向于该法律的维持(尽可能不判定法律抵触宪法),所以在合乎宪法的解释中,尽可能以立法者将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来解释正要解释的宪法。因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对宪法解释产生回馈的影响,要求对宪法作符合法律的解释。参见黄茂:《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注[26]。
[6]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一段精彩论述:“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意志为准。”[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3页。
[7]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概念相同,含义也应相同。”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如此理解的话,那种试图通过1982年宪法的“基本权利限制条款”(宪法第51条)来解释公共利益的做法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该条款是为基本权利而非公共利益设定意义范畴的。
[9]参见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0]参见胡锦光、王锴:“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域外通常并不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区分,因为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本性出发,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内涵上应当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私人利益相关的领域并不存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但却与公共利益的概念发生关联。
浅谈宪法学士论文范文篇二
《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关键词】宪法文化;宗法秩序;近代中国;宪法;宪政
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肇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一役,随着北洋水师在海面上的沉没,既标志着“洋务运动”以洋枪洋炮守护封建专制体制的破产,也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的宪政制度。以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有议会、宪法。于是他们认为,中国要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自强图存,就必须仿行西方的宪法。自此,中国人开始走上了研习宪法和追求宪政的漫漫之路。
1905年的俄日战争则更是推进了这一仿行西方宪政的历史进程。俄日战争中日本虽为“蕞尔小国”,但却挫败了欧洲列强之一的俄国。这一事件震惊了满清朝野。满清以为,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仿行西方宪政的国家,而俄国却仍然奉行封建专制。日本战胜俄国,实为宪政制度战胜了封建专制。此时满清官方开始意识到宪政体制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满清政府派出了以载沣等人为代表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中国也开始了由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剧烈社会转型。
然而,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宪政运动,其结果却是“有宪法,无宪政”,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得知,失败的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缺乏宪政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的文化其根本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性。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现代宪政运动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一、传统宗法文化对西方宪法的重构
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1]这种文化我们常称之为宪政文化。西方的宪政文化催生了宪法。以宪法为根本法调整的社会秩序则被称之为宪法秩序。[2]而传统中国则与之相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质为“礼”制文化,或宗法文化,因为在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宗法关系。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秩序,即宗法秩序。[3]“由于宗法伦理的作用在于确定宗法等级制度,使得家族内部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这种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被放大为国家机构内部的君主与部属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宗法制度下,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相混淆,世俗的政治权力主宰了一切。”[4]所以,“古代中国的封建时期缺乏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由于等级制度和分配权力基本上是一回事,因此,一个人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大致决定了他与权力的亲疏远近。由于统治集团就是社会的最高等级,因此,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作为国家权威置身于等级制度之外。”[5]
由此可知,传统中国在宗法伦理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宗法秩序在权力分配上不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宪政体制下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而只能是一元化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开始,中国即实行“权统于一尊”的权力分配方式。自王开始,权力由上而下传递,每一级奴隶主根据与王的亲疏关系,而被受赐一定的等级特权。这种从一个权力中心发源,由上而下的权力传递,形成权力分配的中国模式。由于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所有权力归之一元的结构,在中国的权力制度模式中,缺乏对君主恣意妄行的限制。[6]
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原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存在领域,然而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满清政府封闭的国门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危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实用性思维的指引下,为救亡图存,近代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宪法。
自晚清以降,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中国宪法领域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宪法传入中国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重构。[7]这一重构使得西方宪法在传入中国后,其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结构设计被破坏,并异化成国家公权力的一元化模式。这就导致在近百年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在西方立宪过程中不可能具有的“独特”现象,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沿袭的权力一元化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近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与本应是民主产物的宪法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宪法不仅丧失了其制约国家公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神圣功能,反而成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块“新”招牌。
对此,近代中国的立宪史提供了大量而详实的证据。从1908年满清皇室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为“袁记约法”),直至国民党1946年抛出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中国虽然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的约法,却都通过宪法文本或实际的政治运行将国家的权力结构设置为一元化的模式。这种一元化的模式使得国家的最高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权力的传递路径不是采取宪政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传递方式,而仍然遵从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传递模式下,国家的权力来源不是人民的选举授予,而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人民并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而抹杀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宪法精神。
例如,满清的预备立宪中,考察各国宪政归来的载沣等人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竟称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载沣认为,立宪的最大好处就是不仅有利于继续维护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还有利于减轻甚至消除西方列强这一“外患”和革命党这一“内忧”,而“外患”和“内乱”的消弭又更加有利于实现“皇位永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08年满清皇室所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所规定的君主权力与传统封建皇帝的专断权力并无二致。《钦定宪法大纲》的第1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2条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由此可知,《钦定宪法大纲》虽有宪法之名,却奉行“立法、行政、司法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之实。“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8]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在“附录”中也曾规定了部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却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这就意味着,满清可以借助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被政府随意通过普通法律的形式来予以限制和停止的基本精神。《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在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下仍然奉行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分割,完全没有人的平等权利、人的尊严,自由、法治、民主等当时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内容,相反却填充了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内容。
在近百年的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中华民国南京临时约法》在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后,便将原先设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种因人而设法的做法,其意在于将权力集中于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和内阁,从而虚化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同样,取得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在其“袁记约法”中,则通过杂采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各国宪法中偏重行政权的条文,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牵制,以实行袁世凯的“一人政治”主义;国民党的《训政时期约法》则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等,不胜枚举。
总之,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之所以会走向失败,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以及从宗法文化的温床上所生成的宗法秩序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这致使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时,宪法文化强调权力制衡、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被宗法文化所消弭。宪法强调权力制衡的结构设计无法得以真正的实现,宪法秩序始终无法得以建立。尽管近代中国也颁布了数量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的约法,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仍然是追求国家权力一元化的传统宗法秩序。
二、近代中国立宪中自由精神的缺失
近代中国宗法秩序架构下的立宪催生出了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设置,从而导致国家的最高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限制,反而日益膨胀。民国时期的“大总统”袁世凯通过制定“袁记约法”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却仍然不满足,还要复辟做“洪宪皇帝”就是十分有力的例证。依据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国家权力与公民的自由形成一对矛盾关系。国家权力的膨胀必将导致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和挤压。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可以符合逻辑地推导出,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然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必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无论是在对宪法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宪法文本上,亦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大量而充分的印证。
首先,在理论认识方面,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曾明确地反对将宪法的核心和首要功能定位为捍卫公民个体的自由。在西方宪政文化中,个体是本位,或者说个体是社会的原点。宪法的首要使命就是保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然而,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比如梁启超、孙中山、严复等,却都曾深切地表述过对自由权利学说的担忧。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对西方宪法精神研究得比较深入的学者之一。然而,“当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认识随着与西方著作接触的增多而不断深化的时候,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导致他感觉到自由权利学说的危险性,并最终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退却下来。”[9]梁启超之所以放弃自由主义的学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宗法文化的思想、文化底蕴。其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梁启超认为,自由主义不仅难以达到此一目的,相反却可能致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破坏国家统治秩序。因此,梁启超主张加强国家权力,削减个人自由。对此,梁启超说:“自由云者,团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也。”“文明时代,团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10]所谓“团结之自由”,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就是主张加强国家的权力。梁启超认为,国家权力的加强有利于中国形成一个核心力量来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资源,以增强国家实力实现中国尽快走向富强。
一味以追求国家的强盛为目的,而忽视其他国家价值,是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并反映在中国的宪政文化中。它是中国思想者们取舍自由价值和功用的标准尺寸。这个尺寸甚至对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种种混乱、纷争和倒退,特别是民众的麻木、散漫以及革命队伍的涣散和分裂,导致孙中山对西方宪法的自由价值产生了怀疑。[11]孙中山曾说:“我们以往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12]“孙中山如此看待自由,是因为自由对他的民族主义事业已经构成威胁,因此,孙中山认为,争取国家强大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一个像堡垒似的团体。其实,在一个原本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对自由的功利性理解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13]
其次,在宪法文本上,近代中国的立宪也体现了对自由精神的排斥。从《钦定宪法大纲》,到“袁记约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近代中国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虽然一方面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财产、人身等方面的些许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和权利却可以被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随时进行剥夺。例如,《钦定宪法大纲》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仅以“附录”的形式来进行规定,这就充分表明《钦定宪法大纲》的立法宗旨在于保障“君上之大权”,而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194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和“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但是,该部宪法第23条却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权利和自由,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系社会秩序,或增进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其意在于,宪法所列举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可以以维护社会秩序等原因为理由,用法律限制之。而正是基于该条规定,宪法实施后,国民党就先后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一系列政令文件,对人民的游行、请愿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或禁止,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14]
最后,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在近代中国公民也不可能具有权利和自由。例如,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而实际情况却全然不是如此。据1947年1月4日《大公报》的报道:“报纸、刊物登记困难,登记了发行困难,种种束缚,样样挑剔,再加上各地乱列禁书,毫无章则。自由主义及主张民主的出版物,封的封,倒的倒,机关被捣毁,人员被殴打,弄得文化衰落,作家贫病,社会混蚀,人心郁结,而请议不闻。”《中华民国宪法》第8条规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审问、处罚,得拒绝之。”然而,据1947年2月9日《大公报》登的一篇题为《为人民权利自由而呼吁》的文章,文章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机关常常非法逮捕拘禁人民,一禁十天数月,甚至一次也不讯问”。[15]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国宪法》所列的权利和自由具有明显的虚伪性。对人民来说所谓自由权利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所谓自由权利不过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文字游戏。
三、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与宪政建设反思
近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是传统文化的阻却,这已为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和法律革命失败的历史所证实。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习了西方的制度设置,辛亥革命还试图运用西方最民主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来引导中国的法治进程,但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其终极原因就是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目标不仅得不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支持,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最大障碍。[16]那么,在中国进行宪政建设该如何面对我们的传统宗法文化?一方面,近代立宪史中所呈现出的权力重构现象表明传统文化实际上在对宪政建设起着阻碍作用,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当仁不让地是当代宪政建设的文化基础。我们不可能在全盘抛弃传统的基础上推行宪政体制改革。因此,传统文化给我们所出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难题。
(一)既然传统文化的阻滞影响了近代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文化的转型一般有两种范式,即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和外在的批判性重建。所谓“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其基本内涵是:立足于中国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从中“创造性”地转化出民主与自由、法治的宪政文化要素。从文化学的基本理论来看,采取这种文化转型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需要转型的“母体”文化中必须含有可以培育成新型文化的“文化胚芽”,也就是必须具有新型文化的核心要素。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发育出宪政文化,是因为从古代开始,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中就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文化胚芽”。
持“创造性转型”理论的主要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其代表人物在近现代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在当代则有庞朴、杜维明等人。例如,庞朴认为:“传统是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并经过选择的。我们如果想彻底砸烂它,否定它,我想是不可能的。……因此,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来转化传统,但是不可能纯粹依靠外力来转化传统,而是必须依靠内部力量,即传统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斗争来解决传统的转化问题。”[17]新儒家们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主、自由的宪政文化,也承认传统的宗法文化中缺乏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不缺乏产生民主和自由的宪政文化的“文化胚芽”。例如,唐君毅认为,西方宪政精义中作为现代民主核心的自由权利观念,其实质就是一种人文关爱精神。这种人文关爱精神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唐君毅不仅认为传统儒学中内含有“自由”的文化因子,同时还认为传统儒学还具有平等精神。他指出,基于儒家的“性善论”,视人性为纯善而无恶,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从这一点来说,儒家实际上还是具有平等精神的。他们以传统儒学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传统儒学中转化出宪政文化。
尽管新儒家们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包含着诸多启人心扉的重要启迪,例如,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开辟出宪政、民主来,从而形成将传统文化与宪政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新思路,但是,就他们对儒家文化和宪政文化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判断而言,确实是十分令人感到遗憾的一大失误。因为“仁”的人文关怀精神,支持的不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而是封建专制体制。近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反复证明,作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产物的儒家文化在整体上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同质,其现实导向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关联的个人主动精神和公民权利、法治意识的培育和生长。因此,儒家文化体系是无法转化成宪政文化体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十分矛盾的民本思想却始终未能促成“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18]
既然从内在的传统文化中无法转化出民主、宪政来,那么就只能采取外在的批判性重建的途径。日本是采取这一形式并成功地实现近代化转型的典型。日本在实现近代化以前,其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属于儒教文化传统。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改造本国的传统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和法律学说,从而完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因此,日本通过采取批判性重建的方式并建立宪政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借鉴。根据日本传统文化近代化成功转型的经验,在不具有西方国家那种民主与法治精神的东方国家,要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一是必须通过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即要通过接受民主与法治思想来实现本国政治法律文化主体的改变;二是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制度创新是文化转型的关键。只有在实际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严格推行法治制度才能最终实现转变公民的传统法律观念。[19]
(二)宪法文化在中国的批判性重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宪政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培育构成了阻碍作用,但这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价值,必须全盘抛弃。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曾泽被过众多异邦民族,中华文明还被美国文化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是世界文化圈中的重要一极。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才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但这也并不能表明中华文明因此就只能彻底抛弃并应当全盘西化。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庞朴先生说:“如果想否定传统,可能就等于否定这个民族;要让这个民族消亡,至少让这个民族的文化消亡。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实的。好多古老民族的文化化为乌有,慢慢地那个民族也就没有了。我们不想让中华民族没有了,就不能提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20]
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近百年的近现代中国立宪史一再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西方宪法文化的舶人会产生抵制,甚至存在权力重构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宪政建设又无法在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否则,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会导致对中华民族的否定。那么,在培育宪政文化时又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怎样的策略?对此,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法律制度设计的层面,应该奉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悬置”起来;实施“以法治为主体,在法治的基本框架下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可以;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而被整合到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中去。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文化的整合的实现,只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整合到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精神之中,而不能是相反,把工业文明的某些文化因素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总体之中。否则,我们又会落入到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旧模式之中。[21]如果不改变宗法文化的主体结构,并确认以法治为主体的社会秩序,那么,宗法文化不仅无法支撑起民主与宪政制度,中国的宪政也将仍旧徒有其外在形式而无宪政的精神,有民主的外观而无民主的实质。[22]
如果我们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们的宪政也许可以提前百年。
【注释】
[1]参见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2]参见陈晓枫、易顶强:《宪法秩序的文化内涵》,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5期。
[3]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4]朱福惠:《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5][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6]参见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7]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8]《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卷四,转引自前注[6],陈晓枫书,第244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 -45页。
浅谈宪法学士论文范文篇三
《 宪法学上的“安全”与“安心” 》【摘要】 “想安心地过一个安全的生活”的人类愿望因层出不穷的危险、不安和威胁而变得绝望。近代宪法均将个人的安全作为权利加以列举,但在文本中同时使用了safety和security两种表述。近代的课题是将人们“免于具体危险的安全(safety)”作为“人的权利”,并在将来也予以保障,那种消除人们的不安进而带来安心的体制就是security。安全权利的主体是个人,国家安全的建构只有回归到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的原点上,才能形成合理的安全与安心的体制。
【关键词】作为权利的安全;作为制度化任务的安全;安心;国家安全;人的安全
一、“安全与安心”的各种形态
“想安心地过一个安全的生活”,这是亘古以来颇为人性化的愿望。但让这一愿望变成绝望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却在现实中层出不穷。要凭想象来描摹危险、不安和威胁,其所涉及的形态则是广泛而复杂的。[1]
在国际社会,进入本世纪之后,以9·11事件为契机,主权国家宣传着“恐怖主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高举“反恐怖主义”大旗,但以主权国家的“自卫权”为根据,开展了与其不相称的单方的美军、盟军、志愿联盟的军事行动,以这种军事行动为契机,又有所谓报复性攻击,两者之间无止境的连环杀戮,至此,苦心经营起来的抑制国际武力纷争的机制渐趋崩溃。[2]各国正在采取“恐怖主义”应对之策,也匆匆着手检验近现代宪法原理、刑事法原理的协调性,深入开展新的法律整顿。[3]同时,警察与军事的近现代法律界限不再分明,军事的警察化和警察的军事化,警察与军事的融合变得十分明显。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为了保护2008年召开的日本洞爷湖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安全,自卫队参与警备,警察性质的警备因自卫队而变成了真正的军事应对,警察被编入其体系中。[4]
与此形成连锁反应,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军事承诺现状也开始发生质的转换。日美安保体制是由日美两军进行“日本的防卫”、由驻日美军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这种条约上的“规制”由于“国际安全保障”的政府间协议一下子缓和下来、并全球化了。驻日美军的改造(transformation,媒体将此译为“重组”,但仅从语义上说并不是“重组(Reformation)”,外务省确切地将其译为“变革”,应该说就是“彻底的变质”)造成了日本财政的沉重负担,自卫队也随之迅速“变质”。以这一事态为背景之一,对于“全球规模上的差距与不平等”的不安也在急速扩大,可以说隐隐形成了对抗轴心,但还无法明确描绘消解这种不安的确切进程。
换一个视角来看,同样在国际社会,1960年世界人口已超过30亿人,仅在40年后的上个世纪末时就成倍增长,突破了60亿人(准确地说是1999年7月)。照此发展,到2050年时预计将超过90亿人。若按照可供给的粮食、水、能源等的测算标准,这种人口爆炸是理所当然的,暴露出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威胁。在日益狭小的地球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加上快速发展的“差距扩大”这种新的世界性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约占世界人口20%的13亿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状态,更有6千万人口是处于饥饿状态。
转过来再看看自然界。虽然大地震、火山爆发、暴风雨、洪水、干旱、龙卷风等因自然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灾害威胁常常与人类历史相伴随,但最近的问题是人口爆炸与能源消费的急速上升等带来了臭氧层空洞、沙漠化、森林破坏、冰川和永久冻土的消失等,进而造成人为的全球变暖(在英语中也称作global warming,“温暖”化有种温和的语感,难以传递“灼热”化的真相)。这又导致了反常的气象,对环境破坏的威胁也是空前的吧。而且,在交通、通信、信息、运输等社会基础设施高级化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因环境破坏而带来的空前的自然灾害威胁在大幅度增长。这种人为因素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不可逆转的自然秩序破坏。有人不安地说,未来地球生物、因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人类可能会灭绝(所谓“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要缓和、消解这种世界规模的危险、不安和威胁,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确切地说,能认识各种危险及其原因的是科学,即使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能有所预见并采取一定的对策、减轻不安和威胁的也是科学之力。换言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迅捷和简易的生活,同时,医疗技术、药品开发的迅速发展也挽救了人的生命,让他们免于绝症和死亡的威胁。
然而,这些“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便利等,同时也产生出让生活关系变得脆弱的事态。例如,“IT革命”带来了信息化社会,一旦其信息系统受到下载的病毒侵袭,就会立即引起金融、交通、通讯、产业等社会基础部门的连锁性功能瘫痪。既有容易遭致恐慌的脆弱社会,也有防御弱、畏惧所谓网络恐怖主义的社会。或者说这些“发展”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克隆人、转基因食品等新的不安。为了消除感染症的威胁原因,开发出了抗生素,然而新产生的抗药菌实际上又反过来袭击人类,形成了恶性循环。本来利用核能的危险性和军事技术飞跃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 RMA)带来的威胁也没有减少。美军以伊拉克涉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其发动武力攻击,使用了甚至包括贫铀弹这种核武器在内的高技术水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科学技术的发展本应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幸福和便利,但反过来也造成了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这就是一个悖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生活带来了高级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事态,[5]借用U·贝克的话来说就是,正在形成“包含工业体系的第二自然(die in das Industriesystem hereingeholte Zweitnatur)”。[6]
转过头来看日本社会。日本经济持续受到全球化、通货膨胀、资源能源短缺的直接打击,在主要发达国家很难看到的所谓“差距扩大”、名为“差距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正在显现。由于名为“新自由主义”的、脱离规制和节度的“自由”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狂奔,在本国“传统的”长时间劳动、加班服务、过劳死等之外,失业、就业难、就业无保障的增大都在急速展开。“景气”即使在数据上有所恢复,但就业无保障却代之以扩大的“无雇用恢复(jobless recovery)”,愈加深刻。一些异常状态在继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劳动者(所谓工作的穷人)超过了1千万人,有名无实的管理职、网吧难民、*无家可归者、离群索居的宅男宅女等作为社会现象常态化。另外,社会朝着低生育、老龄化在发展,而社会保障体系却在明显恶化,生活保护、生活扶助、退休金、医疗保险制度在明显倒退——管理运营这些制度的行政部门中完全人为地瓦解制度这样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也逐渐显现。在“饱食”的日本,因未获得生活保护而饿死的人每年有50人,日本一方面自诩为平均寿命高,另一方面每年却有超过3万人的自杀者。以这种状态为常态的国家,不能称之为“成熟社会”。
这些事情仅以“安全网的重新修补”是无法应对的,可以说这是劳动力商品化极为怪诞的显现,虽努力寻求根本性、结构性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与之相对应的却很贫乏。简言之,其矛盾在于,一方是连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的存续也陷入危机的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另一边却是(归根结底是以破坏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为目的)军费开支的国家财政神圣化突进。对此确有根本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为何媒体和言论界在这种问题上变得如此迟钝呢?
再转过来看看我们的身边。连日常的饮食,除了BSE(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家畜传染病的威胁之外,违法添加剂和虚假标识的蔓延(从“白色恋人”到“赤福”一流食品企业的“红白”伪装交战)、因残留农药、残留抗菌剂、因收获后处理等造成的食品、食材、食器、什物污染等层出不穷,即便在“安心地享用安全的饮食”这种人类生存的基本之处,也充满了不安。
连日常生活都悄然来临的不安、前景的暗淡、人们心理的不安和社会的颓废现象等表面化,“安全的日本社会”此刻也已成为一个神话。这不仅反映于吸引眼球的新型凶恶犯罪的增多,[7]也可以看到家庭暴力、家庭犯罪、虐待儿童、老人和流浪者等社会弱者、人格障碍者的违法行为、犯罪游乐、*袭击型犯罪、发作型犯罪、尾随跟踪者、性骚扰、利用职权骚扰等等可谓无国界型犯罪的社会明显化,从而能窥见到病态的现代社会面貌。这种危险、不安和威胁感觉在扩大,对此一方面包括“死刑”的刑事法上的“严刑重罚化”,另一方面强化标榜“生活安全”警察行政、促进“居民参与”其中,但以名为“防范”摄像机的监视摄像机和所谓街景(Street View)摄像机、窃听法、住基网等来构筑“安心”体系,在其内部又酿成了监视、管理社会的不安。
仅凭想象而描摹至此也能看到,“从各种普通犯罪到恐怖主义对策的‘安全’” 的确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以此作为“正义事业”,“国家的过剩——干预过多”十分明显。[8]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层出不穷,为了实现与此相对的“安全和安心”,却又召唤出更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
但是,国家要实现国民的安全,这是自近代国家以来的当然职责。既然前所未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国家或公权力怠于以“公”的名义履行消除危险的任务,也理应予以谴责。着眼于此间的复杂现象,1980年代以降,以前文引述的社会学者贝克的讨论为嚆矢,呼吁人们关注所谓“风险(risk, Risiko)”论。这种风险论原本与像天灾那样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Gefahr)不同,虽然以人类行为带来的、能追究责任的危险(Risiko)为对象,但像以“第二自然”命名现代文明那样,正如自然灾害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管理也有困难那样,给人们造成危险、不安和威胁的现代文明将向何处去,也是考察的目标。只是不仅如此,现代特有的、在以前的分析框架中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不安和威胁也容易普遍包含于“开放”概念之中。[9]如此,我们继续保持着对“安心的法西斯主义”[10]的警戒, “风险学”的构筑也正在成为重要的现代学术课题。[11]
上述种种危险、不安和威胁,虽然包含着别有用心而有意增加的意识形态,但也的确存在具有实质性现实根据的情形。这些叠加起来填满了人们的心理,以此为推动,建立随机应变的“概括性”“危机管理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可以设想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像列举的那样多种多样,其应对之策也只能是多种多样的,能“概括性”应对的危机管理体制真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吗?对此,我极为怀疑。灾害应对基本法制体系是以自然灾害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以这一体系为基础构建应对“武装攻击灾害”之“事态”的法制,即“有事法制”,将政治、外交政策这种人为原因引起的“武装攻击事态”,与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等自然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控制的事态同质化,其基调就必须予以批判。关键在于,虽说是发生危机时的管理体制,为了不发生危机,就应周到地构想何为必要的吧。
二、近代国家、宪法与“安全和安心”
“想安心地过一个安全的生活”的愿望并非从今天才有的,毋宁说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人性化的愿望。只是这一愿望正式登上人类社会的公共舞台、并被标榜为统治妥当、正当目的,却是近代以降的事情。原因在于,“近代”是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主权归属于被统治者为原则的,近代的统治将作为被统治者的国家成员所希望的“安全与安心”列为其统治的基本目的。这在几部宣布近代开始的古典文献中也能见到。
美国在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无疑是描绘近代图像的最早的古典文献之一。该宣言在开头处写着这一名句,“人人(all men)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后写道,“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among Men)建立政府,而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反这一目的时,人民便有权利(the Right of the People)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就描绘出了约翰·洛克所设计的统治原理。因而,这种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必须以让人民的安全和幸福(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最大化为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和组织权力的方式”。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人民的安全(safety)”等同于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各种权利,并将建立新政府的目的作为统治的目的。
然而,这一文献为了讲述美国独立的经过,还特别继续论证了新政府建立(=独立于英国)的正当性。它在开头一般正当性的文脉上写道,“长期的暴虐和强取豪夺……表明(政府)企图让人民服从于绝对专制时”,“人民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废弃这样的政府,并为人民将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组织”。这里,“将来的安全”被表述为future security。
顺便说一句,《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比《独立宣言》早二十多天颁布,“与独立宣言及其内容紧密关联,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关系”。[12]该法案第1款规定了近似于《独立宣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权利被界定为“通过取得并拥有财产、追求并获得幸福和安全的手段,享受生命和自由(the enjoyment of life and liberty, with the means of acquiring and possessing property, and pursuing and obtaining happiness and safety)”。同时,第3款规定,“政府是或者应该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护和安全而设立的(That government is, or ought to be, institute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nation or community)”。这表明了设置政府的一般设计。前面用的是safety,后面用的是security。
译为日语“安全”的多是safety和security——因而也有译者将“安全”分别译为“保安”“安宁”等。[13]从以上的脉络来看,两者之间包含着微妙的细微差异。如果非要加以区分识别的话,可以将safety推认为“与客观的现实危险相对的具体安全”,将security推认为有组织地提供安全“以备将来不安的安心体系”。引用权利论的话来说,暂且可以将两者作这样的类型化,即将safety视为作为人的具体权利的“安全”,将security视为作为政府的制度化任务的“安全”。
另一个著名的近代宣言性文献是1789年8月26日的法国《人与市民的权利宣言》,它 “提供了近代宪法的各种基础性观念和公式”,[14]屡有引证。其众所周知的第2条规定,“一切政治结合(association politique)的目的在于保全人的不因时效而消灭的自然的各种权利”。这些“各种权利”除“自由”、“财产(propriété)”、“反抗压迫”之外,还列举了“安全”。这里的“安全”是s?reté,也就是区别于sécurité(security)的safety。因此,可以看出,这里更为直接地将“安全”(s?reté,safety)作为“人的权利”,保障它成为统治和政府的目的。
在法国的权利宣言中,作为权利的“安全(s?reté)”,即便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部宪法经历众所周知的激烈变革时,也一贯得以规定。1791年宪法在序言中采用了1789年的宣言;即便在1793年吉伦特宪法草案中,仅仅采纳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的自然的、市民的、政治的权利(les droits naturels, civils et politiques)”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propriété)、社会保障(garantie sociale)和反抗压迫”。同年的雅各宾派宪法中人权宣言第2条“人的不因时效而消灭的自然的各种权利(les droits naturels et imprescriptibles)”列举的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尤其是1795年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宣言”第1条“社会中人的权利(les droits de l'homme en société)”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 [15]这种种宪法性文件之间的异同和背景中,虽有著名的论点和讨论,但不变的是均将“安全”作为“人的权利”。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一时代的宪法性文件登场的“安全”,成为身体自由(人身自由)的总则性规定。1789年宣言接受了这一“安全”规定,同时将刑罚平等原则、刑事法定程序、罪刑法定主义、刑罚法规不溯及既往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广泛地吸纳于其中。[16]同样的规定在之后的种种宪法中也都能见到。另外,1793年吉伦特派宪法草案的人权宣言第10条中,将这一“安全”定义为“社会为了保全(conservation)各市民的人身(personne)、财产(bien)及其他权利而给予其保护(protection)”。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的人权宣言第8条给出了大致相同的定义(只是与“为了保存人身、权利及财产(propriété)”有微妙差别)。然而,1795年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宣言”第4条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安全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通过所有人的合作而产生的(La s?reté résulte du concours de tous pour assurer les droits de chacun)”。这其中反映了这一宪法的“反革命的性质”,[17]仿佛可窥见今天为了“安全”而动员社会的“合作(concour)”概念,意味深长。
另外,近代宪法的权利构想区别“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对此,青年马克思认为,所谓“人的权利”是指“利己的私人所有的权利”,所谓“区别于市民权利的人的权利”是指“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亦即利己的人、人与共同体相分离的人的权利”。因而,将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解释为“安全是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的社会性概念(Die Sicherheit ist der h?chste soziale Begriff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整体上的社会(ganze Gesellschaft)是为保障其每一个成员的人身(Person)、各种权利及保存(Eigentum)其财产(Erhaltung)而存在的,是一个警察(Polizei)的概念。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判认为,“市民社会并没有通过安全的概念超越其利己主义。安全毋宁是利己主义的保证(Versicherung)”。[18]
在上述近代宪法的理念中,包含着作为权利的安全(safety)与保障它并让每个人安心的安全(security),但两者在词义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这与两个词的拉丁语词源含义也是相吻合的。safety 来源于sollus(完全),是指排除具体危险而获得的客观的“安全”,而security来源于securitas,是se(=without)+cura(=care)的意思,不担心、没有不安,也就是意味着完全主观的“安心”。顺便说一句,这其中的不同也可从两个词的日常用法中看到。例如,安全带(safety belt)是具体地为了发生事故时的确保“安全”的装置,而安适毯(security blanket)*则是一种在婴儿睡觉时带来“安心”的毛毯,但毛毯本身并不一定有这样具体的效用。
如此看来,与安全(safety)相对的是危险(danger, risk),与安心(security)相对的是不安(insecurity, insecure)或者威胁(threat)。这种类型化也许也是可能的。近代的课题看来是将人们“免于具体危险的安全”作为“人的权利”,并在将来也保障该权利,消除人们的不安进而带来安心的体制就是security,将此设定为政治和统治的任务(但在德语圈中,既表达为不危险的Gefahrlosigkeit,也表达为并非不安的Sorgenlosigkeit,同时还表达为Sicherheit。在现代德国的讨论中,前文引用的贝克的论述就是如此,他将重点置于识别安全(Sicherheit)的对象是人为的风险(Risiko)还是自然的危险(Gefahr)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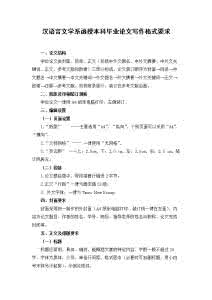
Security是统治和政府原则性任务之一,若回归上述理念的原点,它就是要构筑以具体的人的“安全”为基础的“安心”体系。本来,生活世界(Lebenswelt)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场所,构想其保障的应然状态,是符合这一理念的。背离这一原点,而以缺乏根据的(有时政治性地有意酿成)“不安”为理由,寻求过剩的“安心”,就变成了不合理地追求(对其他的政治目的而言是有效的)安全(security)体系。
不过,“安全”的客观性与“安心”的主观性并不是高度契合的,也可能会碰上矛盾的关系。这不禁让人想起“耶和华见证人拒绝输血事件”。[19]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到,输血在客观上无疑是为了该患者身体“安全”的医疗行为,但因特定的宗教信念而与“安心”相背离,故而遭到拒绝。在这一事例中,该患者选择的不是客观的“安全”而是主观的“安心”,未能消除该疾病的“危险”,却满足了其主观的安全感。
三、国家安全的光与影
如此产生的“近代”,就能展开以国民为主权者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其原则是国家忖度身为国家成员之国民的意向,以“国民的安全与安心”为名,构筑种种安全(security)体系。译为日语“治安”或“公安”并造成另类印象的public security,在社会体制的含义上,不外乎是为了各种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交易的安全”而建立的体系,但原则上是指在国民国家内部,通过公共力量、警察保障其成员平安无事地生活而获致的“公共安全”。日语中被称为“社会保障”的social security,在社会体制的含义上,一方面是指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稳定的体系,另一方面也是指将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结构性地产生的社会弱者的权利要求回收到这一体系中,但原则上是指以社会自身的友爱性连带能力来纠正支撑国民国家的社会内部差别(=阶级对立)而获致的“社会安全”。粗略说来,历史的轨迹是这样的。在近代,当时的原则是,国家将这种public security 标榜为自己全部的任务,社会内部的事务则委诸“市民”的自由、自律的活动来处理。但社会内部迸发出的结构性矛盾,到了难以通过社会自律来纠正、解决的时候,为了标榜保障社会的安全和安心、维持国民国家秩序,便推出了作为社会保障的social security。无论如何,security让人想起在安宁中确保该秩序安全的“安全保障”色彩。
这样,近代一方面在国民国家内部,由public security 到social security 的多层次地展开,另一方面在对外关系上,构成国民国家的抽象整体——国民或民族(nation),为了实现其安全(security)而出现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体系。以国家为单位来说的“安全保障”极大地成长起来。同样,若连security也变成了以nation为单位,作为通过构成军事力量的“力”实现“国家安全保障”而出现,“保障”“国家”的“安全”直接被当作“保障”“国民”或“民族”的“安全”,这逐渐引起激烈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也就是各nation之间的)纷争、抗争。
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以nation为单位构想安全和安心,这种构想在近现代史上渐渐为人所熟知。于是就把“国家”的安全和安心视为“国民”或“民族”的安全和安心。
众所周知,nation无须回溯其拉丁语词源natio(出生、诞生),就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与“出生”相关的历史纽带而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统一体。它不断有意识地识别、分割、排除并非该nation成员的“他者”,而与作为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人的纽带之间处于尖锐的紧张关系。不过,Nation在表面上是一体的,只要限定在该nation的内部便充满了同胞的友爱,因而也可以打开了与“他者”的友爱(fraternité),作为美好的人类共同体而镌刻在历史上。然而,即使从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和安心”的理念原点来看,特别是过去的(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就是“短短的”)20世纪,也是“国民国家”的(以及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国民经济、国际关系的)光与影鲜明化的时代。
以国民国家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与经营国民经济的近代担负着人类和文明的发展,但其中的security被设想成完全抽象的整体的国民(民族)、亦即国家的安全保障。然而根据这一安全体系,国民国家成员以外的、例如殖民地等的人,尽管同样是人,却被作为“他者”而被置之度外。而且,nation虽然原本包含着多样性,但强制为“一体性”,即便nation内部因结构性矛盾而削弱了一体性,甚至崩溃,追求一体性的关键词却依然被频频使用,出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乖离。于是,也就产生了不能断言“国家”的“安全”就是“作为人的国民国家成员”的“安全”的情况。若其与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高级化和军事构想的全面战争结合起来的话,即使该“国家”战胜作为他者的“国家”,其成员的“国民”仅有的将是超越胜败的悲惨损害,借用败者悲叹的“国破山河在”(杜甫)来说,也会产生“国胜亦惨祸”的事态。如果这就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实态,从“人的权利”的角度来看,那就必须给国家安全也打上问号了。
随着这种以国家为单位思考安全的局限性的产生,返回原点,最终会发现有必要修改安全与安心的人类设计,提倡取代nation的security、或超越它的安全体系的范式转换。以帕姆委员会提倡的common security[20]为嚆矢,特别是“人”的安全与安心、即human security的概念呼之欲出。
四、“人的安全”的解读
对于这一概念的登场及其意义已有很多论述,[21]这里仅从本文关心的问题出发简述几个观点。
human security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4年的《人类开发报告》[22](以下称“UNDP报告”)倡导的。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外乎是具有特定背景和内容的国际政治上的专有名词。它是从这样一种想法中产生的,即所谓“冷战”结束之后带有浓厚的某种乐观气氛,人们认为,以常规性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能够消除直面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至少让其退居相对的地位。在这一脉络上,从以贫困为首的南北问题的因素中已经见到今后纷争的苗头,也可以“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为核心来把握人的安全。因而,在这一想法的前提中应该说暗藏着“和平与开发的整合”的构想,具有对“因开发不足而引起的不安定”进行预防性处理的政治含义。
众所周知,上述乐观气氛不久就被破坏了。伴随着从新的地区纷争、民族纷争的显现到9·11事件后“不安、危险和威胁”的高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明显地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稳定,而联合国也因此而让“人的安全”这一概念退为背景。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例如,加拿大主要是以所谓PKO、即维和行动的新版本来把握这一构想,将某种军事力量置于已承诺的国际、外交政策的主轴。[23]而日本政府,则将其作为已穷途末路的ODA政策*的新版本,内置于外交政策的色彩浓厚。[24]该专有名词大抵带着政治性、多样性而扩散到各国。
另外,更为根本的是,将这一构想置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来看,这里所追求的“安全和安心”,在其标榜的普遍性的背后,也忽隐忽现着“安全和安心”不可或缺的新秩序与安定化的契机。的确,UNDP报告将人的安全分为“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个人、社区、政治”七个领域来论述,常规性的安全保障限于个人、社区、政治的领域,其倒退是明显的。作为对人的安全的“六大威胁”,分别列举了“人口爆炸、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国际间过度的人口流动、环境恶化、毒品的生产和交易”,同时也不忘未作概念界定的“国际恐怖主义”。[25]“国际恐怖主义”的概念,的确并非主权国家传统“安全保障”的对象,但在被接纳为常规性的安全保障对象上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如此看来,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志愿)联盟的传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无法抑制国际秩序的混乱因素,却可能在全球规模下得到控制、驾驭并有序化。仅此而言,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体系在近代国家史登场,人的安全这一概念潜在地贯穿于这一体系。
毋庸置疑,世界上常规性“安全保障”以外还有很多的问题产生,特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无法涵盖的问题在急速扩大。为了涵盖这诸多问题,UNDP所提出的各个问题肯定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这些问题已由常规性安全保障体系加以取代,这样的理解也未必正确吧,各国政府也不是这样去理解的。[26]UNDP报告说,“从保全领土的安全(security)到重视人的安全”、“从军备保障的安全到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用两种基本方法切换security的相关思考”,这一点的确得到善意的接纳。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的时代认识是,“现在应是从国家安全这种狭义概念向人的安全这种概括性概念发展的时期”,并不是说单纯的“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的范式转换,而是提倡“包含国家安全的概括性的人的安全”的转轨。如此看来,人的安全构想并不是要排除传统的国家安全。
Safety与security的不同业已提及,在人的安全概念的用法中,security概念被扩大化,轻而易举地就同时包含safety和security。对于居住于日益全球化的巨大社会的“人”来说,不管何种危及安全的危险、不安和威胁都被最广义地总括起来,可以说它们成为一个普通名词,而淡化了专有名词的性质。
在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主权国家的门槛逐渐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若意识到它可能是该主权国家自觉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作为政策的全球化”,也未必就会带来“主权国家的黄昏”。[27]但寻求安全(security)的舞台超越了主权国家内的公共(public)舞台、社会(social)舞台乃至国家(national)舞台,或者说事实上在这些基础上,全球(global)舞台的比重也日渐加重。要求人的安全的事态也佐证了并不是以划界的共同体为单位而构想安全体系,而或许要超越它,独立的个人作为“人”而要在全球的层面上直面安全。
正因为如此,security本来应是以safety权利为起点而体系化的,现在有必要返回到这一原点。这时,在原点孕育的安全“权利”的保障,成为政府的目的,由国家垄断性地予以制度化。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28]有必要重新捡起。正如某学者所准确指出的那样,近代国民国家的“安全保障(security)”体系“在属性上是‘依存于国家’的构造”,往往变得“国民对安全保障漠不关心”,于是“国民放手让国家去消除威胁,实现确保自身安全的目的”,这一安心便是“疏忽大意”。[29]或者像著名的法国现代思想家回归到1789年宣言所道破的那样,其第2条“不是安全保障(sécurité)而是安全(s?reté)”,这并不是次要的语法差异问题,而是从“安全”属于市民“接近国家的权利”的瞬间,“安全成为国家的一种功能,市民在缄默中寻求国家的保证。在这一方面,可以使用安全保障(sécurité)的用语。所说的安全保障,是在市民通过自己设立的国家来获取安全(s?reté)时,安全就发生了变化”。[30]如此说来,与这位思想家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安全这种]基本权利(所谓自然权利)不是从‘主’和‘守护神’那里获得的,因为它没有授予的可能性。市民自己行使,首先通过起义,然后日常地行使——它在结果上是民主主义的,进而成为市民自身获得的权利”。[31]但“安全”作为“人的权利”,必需片刻不得放松。它很难在单个的个人水平上自我完结地加以实现和保障。另外,“民主主义”的施行是否会损害“人的权利”,(特别是在日本)是片刻也不能马虎的注意事项。如此,与构筑“公共领域”的道理一样,能在逻辑上、结构上断然拒绝“通过法律化、制度化而易于接受的‘殖民地化’,探析自由的动态的、日益更新的‘自发自律的结社(Assoziation)’的‘逻辑’与‘结构’”,[32]仍是横亘于我们面前的课题。特别是“近代”,在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结语
总之,人的安全这一概念的登场,作为普通名词,从主权国家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观来看,也隐藏着向实现人们“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的体系与安全保障观范式转轨的转换可能性。“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的说法,最初在众所周知的1941年《大西洋宪章》登场,免于法西斯主义“恐怖”的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正义的战争”目的,成为国联(United Nations)的标语。但其普遍的含义,不仅支撑着沿袭《大西洋宪章》理念而组成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精神,连战败后的日本在回归国际社会的宣言中、在日本国宪法的序言中也予以讴歌。但日本国宪法宣称的是世界上所有人(all peoples of the world)个体地拥有、在“免于恐怖与匮乏”的和平中生存、生活的“权利”(the right to live in peace)。若这一点能看出日本国宪法在承认“正义的战争”的《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上飞翔,并返回到“安全”的“权利”性这一原点、让其在现代复苏,将会重新受到注目吧。[33]
【注释】
[1]以下的“各种形态”,笔者参照了被选任为日本学术会议第18期、第19期会员的各种活动所获得的知识,笔者在各种报告中执笔的部分也为本文打下了基础。作为学术会议活动的一环,笔者在“人与安全”特别委员会及“学术与社会”常设委员会担任委员长、在“日本的计划”特别委员会担任了干事。日本学术会议对外报告:《安全で安心なヒューマンライフへの道》(2003年3月17日)、同《科学におけるミスコンダクトの現状と対策》(2005年7月21日)、日本学术会议:《日本の計画 Japan Perspective》(2002年12月)、同《科学のミスコンダクト》日本学术协力财团(2006年)。另参见日本学术会议:《多発する事故から何を学ぶか―安全神話からリスク思想へ》日本学术协力财团(2001年)。
[2]关于这一点的文献很多,但最近的考察可参见松井芳郎:《国際法における武力規制の構造》,载《ジュリスト》第1343号(2007年)。
[3]关于这一点的文献很多,目前的可参见大沢秀介・小山剛编:《市民生活の自由と安全》,成文堂2006年版。
[4]参见2008年7月2日《读卖新闻晚刊》;水島朝穂:《今週の直言》2008年7月7日,(http://www.asaho.com/jpn/index.html)、并参见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20080625-3057808/news/20080705-OYT1T00449.htm、《特集・サミットと“テロ対策”》,载《法と民主主義》第429号(2008年)。另参见拙文:《 “戦う安全国家”と人間の尊厳》,载《ジュリスト》第1356号(2008年)。
* 这是2006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纪录片的名字,记录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近几年跑遍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城市,讲授温室效应对地球威胁的经历。整部影片反映了一个事实:人类正在遭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困扰。——译者注
[5]参见村上陽一郎:《安全学》,青土社1998年版,第45页以下。另参见村上《安全と安心の科学》,集英社新书2005年版;《特集・“安全”とは何か》,载《現代思想》第27卷第11号(1999年)。
[6]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 M. 1986, S. 9 f.日文翻译,ウルリヒ・ベック:《危険社会》,东廉等译,法政大学出版局1998年版,第5页(另外本文引用的外语文献不一定是日文译本)。Auch vgl. ders., Politik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Frankfurut a. M. 1991.
* 网吧难民(日语为ネットカフェ難民,简称ネカフェ難民,即net-coffee)是一个新造的复合词,他是无家可归者的一种,无固定居所、利用网吧作为住宿场所的人。和一般由于年纪大而求职困难、或无意求职的露宿者不同,很多网吧难民都是有心寻找工作,但只是做一些日薪工作的临时工。自2007年起,日本的传媒使用这个名词去取代露宿者。——译者注
[7]对此间事情的正确研究,目前可参见河合干雄:《安全神話崩壊のパラドックス》,岩波书店2004年版。
* 日文原文是“愉快犯”,是指通过某种行为引起人或社会恐慌,然后暗地里观察或想象其丑态和慌张的样子,并乐在其中。该行为是否违法、违反什么法,因行为而定。——译者注
[8]樋口陽一:《撤退してゆく国家と、押し出してくる“国家”》,载《憲法問題》第14号(2003年),第187页。
[9]对此,从U・贝克在9・11事件之后进行的讲演,即使是事件之后他在俄罗斯国会的讲演缩略版,也可见一斑。他以风险的框架论及该事件。Vgl., Ulrich Beck, Das Schweigen der Worter, Frankfurt a. M. 2001,日文翻译收录于ウルリヒ・ベック:《世界リスク社会論》,島村賢一译,平凡社2003年版。
[10]参见斎藤貴男《安心のファシズム》,岩波新书2004年版。
有关浅谈宪法学士论文范文推荐:
1.有关宪法论文范文
2.宪法论文的开题报告
3.宪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4.有关宪法论文开题报告
5.从宪法角度谈教育公平的论文
6.浅谈法律案例论文范文
7.浅谈法律系毕业论文
8.本科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参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