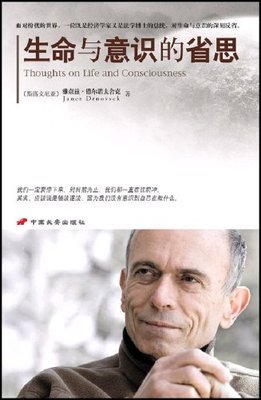彭国翔:拒绝“死亡之吻”——儒学的功用和复兴的省思
大国之兴,必有强大的文化为后盾。
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在文化的根基处与过去“决裂”为特征。批儒学、反传统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真空、信仰失落以及认同危机。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器物甚至制度层面“一体化”的同时,中国开始日益突显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寻找自我的过程,呈现出儒学的复兴之势。
让贻误的问题重回我们的视野,让模糊的事物变得清晰。
复兴缘由
儒家传统在中国至少有2500余年的历史,并且,汉代以降,儒学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主流的观念和价值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许多学者将古代中国称为“Confucian China”(儒教中国)。但是,综观整个20世纪,儒家传统的命运却发生了急遽且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我们将1919年迄今界定为“当代中国”的话,那么,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和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 1960年代“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再到1980年代末的“河殇”,批判和否定儒家传统的线索一以贯之且登峰造极。儒学遭遇到了全面解体的命运,至少在中国大陆最终沦为“游魂”。中国人也相应几乎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要彻底抛弃自己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
第二阶段自1990年代迄今,首先是学术界开始反思激进与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的偏颇,官方态度亦逐渐扭转。在广大国人开始日益认识到传统不可弃的情况下,社会上渐有复兴儒学之说。尤其2000年以来,复兴儒学的呼声日高,从官方到民间,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活动,颇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就儒家传统自身来看,如果说前一个漫长的阶段简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后一阶段虽为时尚短,却也不能不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如果我们意识到对儒家传统的批判晚清已经开始,到1980年代,反传统的思潮实已有百余年。百余年来,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反传统的传统” (tradition of anti-tradition)。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到2006年为止,认为至少在社会声势的层面上儒学复兴之说日益深入人心,也许并不为过。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缘由。
首先,儒学的基本价值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非但广大知识阶层多以儒学的核心价值为"安身立命"的所在,普通凡夫俗子由于长期受儒学的教化,亦将儒学的一些核心价值如“忠”、“孝”、“仁”、“义”等奉为为人处世的“常道”,并在日常生活中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来体现这些价值。可是,如前所述,20世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所导致的只是原有价值系统的崩溃,并没有给我们从“西天”取来“真经”,使之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系统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于是,在批儒学、反传统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真空、精神失落以及信仰危机。然而,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系统和意义世界,否则即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一点,在各种西方理论涌入中国、轮番占据知识人心灵而“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后,终于逐渐为人所自觉。如何摆脱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心态,深入发掘传统中的精神资源,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综合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终于成为中国广大有识之士共同的问题意识。
其次,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从反传统的传统中走出,开始重新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问题亦是一个重要的缘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器物甚至制度层面带来“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突显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越是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我是谁”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只有植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有一席之地。这一点,迫使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体不仅不能乞灵于任何纯然外部的文化来建立“自我”,反而必须深入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认识你自己”。海外的华人之所以对文化和价值认同问题有格外的体会,决非偶然。当然,任何文化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其更新和发展需要不断吸收外部的资源。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不过,任何文化吸收新的成分从而转化和发展自身,其成功的前提必须是立足于已有的传统,否则即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从政治、经济上看,中国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文化上看,中国能给全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西方有源自希腊的理性文明和源自希伯莱传统的宗教文明;伊斯兰世界有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有支撑它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体认我们是谁。不单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单元,更作为一个文化实体。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因此,全球化一方面使我们日益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我们越来越了解其它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儒家传统。显然,如果弃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儒家传统于不顾,我们还能给世界提供别的什么呢?
此外,还有一个缘由不能忽略,那就是:一批真深入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文化优秀成分的儒家知识人对于守护和重建儒家传统不遗余力的毕生奉献。尽管整个20世纪是反传统思潮当令,但自始即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学者能够认识到儒学的基本价值不但不与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相悖,反而彼此相通相济。从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再到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等,都为在整个反传统的浪潮中保存儒家传统尽心尽力。1949年以后到80年代以前,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主要在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得以不绝如缕。80年代之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由批判的对象受到重新评价,以上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广义的新儒学终于重新回到了大陆,并日益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唐君毅先生曾用" 花果飘零"来形容中国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而这些一生为中国文化、儒家传统"招魂"的学者,对于如今儒学能在中国大陆呈现复兴之势,实在是功不可没。
契机与危机之间
上世纪90年代也曾一度有所谓“国学热”的说法,但当时尚不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如今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再来看中国文化、儒家传统,笔者认为的确已经真正显示了“一阳来复”之机。对于传统价值的需求已不再只是部分知识人的呼吁,而真正表现为社会大众的心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复兴“形势一片大好”。事实上,目前存在的问题甚至相当严重。对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警觉和克服,儒学复兴的“契机”未尝不会转变为更大的“危机”。
首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本身未必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民族主义都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却会产生很多弊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与原教旨主义互为表里,而目前世界和平的大敌恐怖主义,其渊薮正是原教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中国崛起向世界上传达的文化信息如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儒家传统的复兴如果被认为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抬头,那么,从中华文明之外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恐怕就是人之常情了。如此反过来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够于儒家传统深造自得者,一定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儒家知识人都是“以天下自任”而能超越一己与小群体之私的。综观近现代的整个中国历史,最具开放心灵而能吸收其它文化之优秀成分者,几乎无一不是当时最优秀的儒家知识人。不但中国如此,整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等都是同样。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假儒家之名号,甚至有时亦自以为是以儒学的价值为自我认同,但既不能于儒家传统深造自得,终不能得儒家之实,只能给儒家带来灾难。因此,要想在当今新的时代重建儒家传统,首先要加以警惕的就是不要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弘扬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而“别有用心”之辨,识者不可轻忽。
其次,是目前无所不在的商业化对复兴儒学的侵蚀。社会上总有些人是“风派”,其实并无自己的原则。凡是能带来好处的,皆趋之若鹜;反之,则避之惟恐不及。如今,儒学已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成为一种正面的文化象征和资源。于是,不少机构和人物纷纷奔赴儒学的旗下。问题是,如果这仅仅是因为儒家能够带来名利,而不是从事和提倡者出于自己对儒家的体认,出于对传统文化深厚的了解,势必会给儒学的真正复兴带来很大的麻烦。目前,广大社会民众确有了解和实践儒学价值的良好愿望。但是,相对于这种需求,在百余年反传统的传统下,真正有资格代表儒家传统发言的人并不多见。即便是基本儒家知识的介绍,也需要受过专业训练而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来从事,更不必论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了。如果面对公众讲儒学者自己并无有关儒家传统的深厚学养,既误人子弟,于自己也未必是福。因为长远来看,良莠朱紫终有水落石出之日。对于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社会大众慎思明辩,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广大知识人自我反省、自觉自律。
拒绝“死亡之吻”
历史进入 21世纪以来,的确是重建儒学传统的一个很好时机。社会上有这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在全球的范围来真正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资源。但是,如果这个时机不能好好把握,上述问题不能够好好解决,那么,儒学是否能够真正复兴是很可怀疑的。各种表面上推波助澜的力量弄不好会成为儒学的“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它表示对你亲近,可带来的结果是死亡;它所做的一切看起来是要提倡你、推动你,结果却让你早点毁灭。所谓“契机”变成“危机”,正在于此。
至于如何避免上述问题?笔者以为,当务之急莫过于树立对于儒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前已指出,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之中。目前谈儒学的复兴,必须对这一历史背景有充分的自觉。可以试想,“五四”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无不生活在这样一个反传统的传统里面。 90年代时哪怕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出生之日已身处反传统、批儒学的氛围之中,因而对儒家传统、中国文化究竟能有多少认识,是很值得思考的。长者尚且如此, 1949年以后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者,就更不必论了。佛教有“正见”与“正行”的说法。“见”是思想、观念、意识,“行”是实践。先要有“正见”,然后才能有“正行”。借用这个讲法,我们可以说,只有对儒学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之后,才可以去讲儒学、实践儒学的相关价值。如果只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去讲儒学,则“起脚便差了”。如果让一些皮相或似是而非的对儒学的理解左右人们的认识,则重建儒学传统,从儒家传统中汲取身心受用的资源,将是无从实现的。因此,要发挥儒家传统的价值,从中汲取有益的资源而有所“受用”,首先在于确立“正见”。讲儒学的学者对儒家传统一定要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之后,才可以采用各种形式把真正儒家的信息传达到社会上去。有了“正见”,无论采用怎样的形式来讲儒学都无妨。但如果并无“正见”甚或根本是别有所图,则 “死亡之吻”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中国文化、儒家传统已经隔膜甚深的情况下,要获得“正见”,除了激情之外,更需要清明和深沉的理性。没有孟子“掘井及泉”和荀子“真积力久则入”的工夫,很难真正接上儒家传统的慧命。
儒学的“功用”
最后,对于儒学在当代中国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笔者愿意从一种前瞻的观点来谈谈个人看法。
儒家传统有很多层面,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的特点也各有不同。不过,儒学将来的主要价值,首先在于作为一个精神性的传统,能够为人们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提供资源。中国古代有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说法。“四民”即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四民异业而同道”就是说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所谓“道”,儒学可以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体现,不论其职业如何。知识人固然能够且应当体现儒学的价值,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可以“当仁不让”。如今的社会分工早已不只“四业”,并且会越来越多。但是,只要是人,不论其职业如何,都会碰到人生的意义问题。而儒家传统恰恰具有可以解决人生意义问题的丰富资源,历久弥新,超越时空,可以为不同时期各行各业的人所受用。
除了人生意义的智能之外,儒学的整体有机和谐观更是人类将来发展的宝贵资源。我们如今正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其实,和谐不只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在全球范围内,从个体的身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如今都面临着和谐的问题。人格分裂、生态恶化以及文明冲突,都是缺乏"和谐"的恶果。而儒家传统的 “万物一体”观以及“和而不同”、“理一分殊”的原则,都具有一种人类—宇宙的整体和有机的视野,恰恰可以为如何保持身心平衡,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其它文化传统相较,儒家传统的这一特点,业已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广大有识之士的一致认可。如何将其中的普遍原则与当今世界的各种具体境域相结合,从而使之不断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正有待于我们致力其中。
当然,儒家传统并不只是一种精神性的传统。笔者历来认为,儒学本身是一个包括政治、社会、伦理等等多向度的(multiple-dimensions)传统,除了精神性的资源之外,经过一定的转化,儒学还应当而且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其它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的资源。即便在制度建设的层面,儒家传统同样不是“俱往矣”的博物馆陈列品,其中仍然蕴涵许多丰富的可以“古为今用”的内容。譬如科举制,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很强的理性的精神。过去俗话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论什么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进入社会的管理阶层,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为老百姓办事。这个例子说明,哪怕在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儒家传统仍然有许多理念可以为今天所取用。只不过,即便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恰如对儒家传统的精神价值已经隔膜甚深一样,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深入其中,深明其得失呢?其实,无论哪一个层面,哲学性的、精神性的、政治制度的、社会伦理的,如果不能“入乎其内”而后“出乎其外”,任何关注和提倡就和以往那些“雾里看花”的批判一样,都无法免于口号式的肤泛。那样的话,儒家传统的真正诠释和重建,将是无从谈起的。因此,只有大家分工合作,沉潜深入地发掘儒家传统各个层面的内在资源,然后创造性的转化和综合创新才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朱子(1130-1200)所谓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是始终值得我们再三玩味的。http://www.aIhUaU.com/
作者简介:彭国翔,1969年生,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2001)。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2004)。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