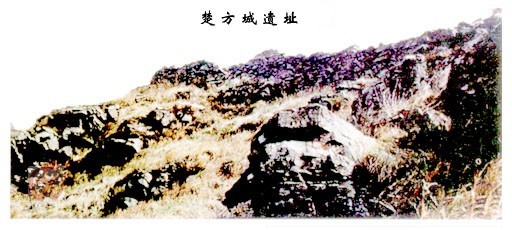我是这条路上的常客。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每两周就要在这条路上往返一次。每次都是千里之行。我常常躺在车的后座上,捱过疲惫而漫长的几个小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以睡觉来打发时间的。更多的时候,我默默地将视线投向窗外,这样,无一例外地,每次我能看到的,都是沿路之上那些树梢的风景。
我看到最多的,是那些枝叶茂密的树梢。它们一排排的,整整齐齐地飞快奔向后方,像那些疾驰而过的岁月,让我们来不及定睛就已远去。也像蒙太奇的电影镜头,跳跃着,如梦似幻,飞越而过。虽然它们无数次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每一次,我都有一种惊异的感觉。我感觉到那些厚密的的树梢,就像是在专门列队等候我们。我常常弄不清,是我在看窗外的它们,还是它们在看窗内的我。是我在经验它们的岁月,还是它们在巡视我的生命。它们虽然是无声地移动,但我常常听得到那哗哗哗的巨响,那不是风的声音,那是一条河的声音。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是树下面的叶子先长出来还是树梢上的叶子先长出来?我问过身边好多的人,他们都不能确定。这更加加重了我的好奇。我因此更加留心窗外的那些树。
在那些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看到树梢上零零星星的叶子钻出来了,像一些惊惊咋咋的小鸟,扑腾起鹅黄色的羽翼,想要试着飞离枝头。每一棵树上都只有很少的那么一些,可是它们确乎站得很高,让我总是担心它们会掉落下来。不过,我又安慰自己,掉落下来也没有什么,它们带着翅膀呢。
在深秋大面积撤离的日子里,我又看到树梢上站立着零零星星的叶子,它们披着寒霜镀给的金色或者赭红的颜色,骄傲地四顾着旷远而清寒的原野。它们在风中抖动着、跳跃着。我知道在距离他们很高的树下,已经厚厚地躺着一层又一层的落叶。那是它们的必然的归宿。可是它们视而不见,依旧喧闹而安详,坚守着冬天里最后的一线生机。
我问母亲,树从根部吸取营养,为什么树顶的叶子先长出来,又最后落下去?母亲笑了,说,大概是因为它们离太阳近吧。我问研究生物的朋友,他们说,树根部的营养,通过主管道,先输送到树顶,然后再往下面的枝条上一级一级输送。

我恍然大悟。树梢上的叶子遭受风吹日晒雨打的机会要多得多,可是它们的生存能力最强,生命最长久,那是因为它们优先享受了更多的资源啊。反过来说,它们优先占有了很多的资源,所以它们有责任承担起最长久的坚持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