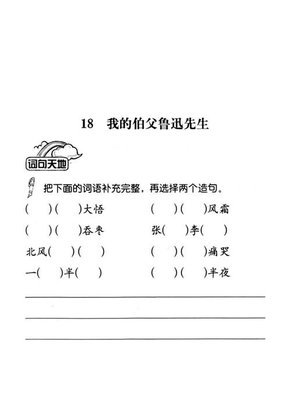《我的反间谍生涯》
作者:【荷兰】奥莱斯特·平托上校
连载5
第三 章

审讯方法
对嫌疑分子的审讯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阐述自己用过的成功和失败的方法之前,我想首先筒略地谈谈英国和其他国家使用的方法。在纳粹德国,广泛使用刑讯,其方式因审讯者的性格而异。如在无麻醉的情况下把削尖的针状物插入指心、拔掉指甲、用金属圈把骨头或头颅箍碎、有对还用牙钻钻磨牙神经。用这些刑罚可以取得一些口供。很难对苏联使用的方法做出精确的估计,因为幸存下来的政治犯为数甚少,而这些为数甚少的人也难以逃出铁幕的网眼。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俄国内务部怎样在无休止的,消耗性的,有时甚至连续三十六小时不间断的审讯中,广泛使用饥饿和药物来摧垮犯人的抵抗力。这样,犯人一回到牢房,便疲惫不堪地沉沉入睡。一小时后,又重新被叫去审讯。这种反复中断睡眠的方法可以摧垮最健壮和最顽强的人的抵抗力。
美国使用的方法——主要指审讯——是用强光源照射被审者的眼睛。审讯人不断轮换。另外,还使用科学的手段,如所谓万无一失的“诚实剂”和“测谎器”等。我之所以说“所谓”,因为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些发明的“万无一失”性。据使用这套方法的人讲。一针学名叫致幻剂的诚实注射液,能使嫌疑犯的意识进入一种假睡眠状态,但不影响其下意识的活动。这样,嫌疑犯便会不由自主地供出知道的一切。而据我个人的经验,长期的专门训练,完全能使人控制自己的下意识,把握住自己的语言。测谎器是一种精巧的仪器,其理论根据是:一个人的代谢机能随着人的情绪而变化。这种现象在科学上是被证实了的。这一方法的发明者据此推断,认为由此可以测出一个人是否在说真话由我承认,从理论上来讲是有据可循的,但是,我怀疑它是百分之百的有效。我曾在实践中遇到过一些头脑冷静的人,他们完全可以欺骗测谎器。当然,这种人是不多的,但这为数不多的人也就够了。为使证据准确无误,必须无一例外,普遍可靠。
纳粹德国,苏俄和美国所用的属于“第三类方法”。他们相信通过疲劳肉体可阻取得想要得到的情报。毫无疑问,体刑可以把任何人的抵抗力降到最低限度,不管这个人在体质上和精神上是多么坚强。曾有个具有非凡勇气的人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指甲全部被拔掉,一肢折断。尽管遭此折磨,此人始终没说一句行刑者感兴趣的话。鉴于种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盖世太保的刽子手只得罢手。如果继续用刑,他或许能说出点什么;因为不堪忍受重刑,他会宁肯求得速死,以免继续受折磨。
任何人都不堪长期忍受水刑。行刑时,每隔几秒钟,把一滴水滴在倒霉者的头上。我完全相信这一古代刑罚能在几分钟内把一个人的抵抗力摧垮。若持续一小时,遮种折磨足以使人发狂。
好在英国法律不承认通过刑讯所得口供的真实性。体刑除了令人深恶痛绝外,还有着很大的弊病。由于剧痛,一个人可以捏造出最耸人听闻的罪名来,以便减轻痛苦。由于不堪忍受折磨,往往随便编造个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以免继续吃苦。刑讯可阻使任何人招供,但决不能保证所得口供的真实性。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执行任务的间谍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或那样的药片。第一种是迷药,可以使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失去意志,另一种叫安非他明,能使疲倦的人重新振奋精神;第三种是用于自杀的,其成份是氰化物或其他烈性药物,可使间谍立即毙命。每一种药片都有其特殊用途,最后一种是用于那些落网后怕受刑不过而招供的人。能把化作一小小药片的死神随身携带,这无疑是些宁死不招供的勇士。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逼供用的刑讯方法。这些方法一般都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不可谓不残酷和令人深恶痛绝,特别是对那些自诩为文明之邦的民族来说。当然,其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间接地表明审讯者由于无能而不得不靠这些方法来打开被审者的口。
第二厅——法国的一个机构,相当于英国特工组织MI-5——使用一种别出心裁,一般说来效果不错的方法。嫌疑犯面对两个审讯者:一个是彪形大汉,说话气势汹汹,指手画脚,咄咄逼人,不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另一个却心平气和,默不做声,和蔼可亲,似乎对犯人满怀同情,并千方百计地制止发火的同事。审讯进入高潮,粗暴的审讯者盛怒之下,高声叫骂,语言不堪入耳,发出可怕的恫吓。突然,彪形大汉被叫走,这场戏便嘎然而止。笑容可掬的人继续进行审讯,但方式是温和的,亲切的。递上一支烟,安慰对方被另一审讯者搞得极度紧张的神经。气氛的突然转变往往产生理想的效果。神经缓和,心情平静下来的嫌疑犯终于供出知道的一切。
伦敦警察厅使用的就是这种怀柔方式。英国的特工人员很善于制造这种亲切的气氛。他们认为人总是人,而人是容易受骗的。英国的特工人员样子是和蔼的,宽容的,通情达理的,所以总能得到需要的口供。作为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荷兰人,无须象中层的英国人那样过谦,我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对嫌疑犯的怀柔方式有力地证明了英国人的两大特点:对一切人的宽容精神和向走投无路的人提供出路的善意。在英国的法庭上,采用一种不同于任何别的国家的法律程序,即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被告有权随时收回自己的口供。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从逮捕到出庭的其他环节。
有的读者可能还记得第二次大战时发生在威尔士菜城的军官事件。一个纳粹飞行员在对小城进行扫射时被击落,俘虏被带到司令部。他神情傲慢,盛气凌人。将军被他的无理态度所激怒。又加之认为他刚刚扫射过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于是就打了他一手杖。在儿周后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将军由于这一不克制的举动披开除军籍。这一惩罚是太过分了,因为将军是出于义愤才揍了激怒他的人。然而,细想起来,就能看出这正是在执行上述的重要原则。
一九四一年,我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只是影响要小得多。找审讯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人,在审讯中,称他为撒谎者一一他是个地道的撒谎者,我使用的这一词被人听到了。于是,我受到上司的申斥,不得不到内政部去上一堂冗长的职业道德课。过去,审讯工作在内政部进行,那里有一条不公开的内部规定,即禁止称嫌疑犯为撒谎者。审讯人员必须转弯抹角地对嫌疑犯这样说:“我觉得你对我刚才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完全符合事实。”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表示这一意思。严禁粗暴地对可怜虫直截了当地加上这一罪名,伤害他的感情。当时,我虽为此事怏怏不乐,但后来却感到欣慰,因为这个所谓的受害者是个讨厌遥项、顽固不化的撒谎大王。细想之下.我认为这一硬性规定也有它的道理。然而,也得承认,有时我是多么想砸烂它,或者情况迫使我很难完全照它办。
荷兰解放后,我为荷兰反间谍局训练荷兰青年从事间谍工作,当时我用的名字是弗兰克·杰克逊。在本章末尾,我将引用一些我的讲演记录,这些记录主要是谈我的审讯方法,这里无须赘述。但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我的审讯方法主要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使嫌疑犯情绪激动,而且激动得越快越好。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审讯的最后阶段,是一场智慧与冷静的较量,彼此都想推倒对方。对于审讯者来说,除了怕一无所获外,别无顾虑。即使审讯失败,对他也不是性命攸关的事。因此,他可以随意驾驭,任意决定中断或继续审讯。然而,若不能在一开始就压倒对手,审讯人将失去原有的有利条件。如果能使对手失去克制力,成功就近在咫尺了。这时,实用心理学便用得上了。审讯者只要善于利用受审人的情绪变化,就能立即巧妙地抓住他的破绽。尽管刑讯受到谴责,反间谍局的人员仍可采用造成嫌疑犯身体上某种不适的方法以达到获取口供的目的。比如说,给他一把硬座椅,或让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站立。如果我设有记错的话,军队的特工人员对被捕的敌方军官常玩这样的把戏,先是摆出一副十分热情的样子,递上一支烟,端上一大杯咖啡或茶,然后审讯就按上述方法开始进行,一直到可怜虫感到生理上受尽折磨,甘心情愿将重要情报和盘托出,以便尽快得到解脱。我本人认为,这是一种很缺德的方法。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体刑,但也近乎体刑的边缘了,仅差一步就越过界线了。说起来有些荒唐,我总是把自己摆在与嫌疑犯平等的位置上,他若需要一把舒适的椅子或摆出一个舒适的姿式,我从不拒绝。审讯的时间不可过长,一般儿早九时至晚六时,中间有一小时吃午饭时间。另外,我尽量亲自审讯,决不自己去休息,让旁人代劳。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我在审讯过程中从不作记录。从一开始,就要打破那种一本正经的局面,让嫌疑犯有很随便的感觉,除非此人更喜欢军队中的刻板。我总是设法使他情绪激动,以便掌握主动权。有时,一切方法都不能奏效,,而且又肯定嫌疑犯是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我就让他从头到尾反复重述自己的交代,一些细节也不能遗漏,不管他把自己的经历编造得多么煞有介事。有时,这种整日整日的重复会延续几个星期,这需要双方都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很好的记忆力。如果他的交代不是真的,迟早会在某一重要情节上出现漏洞,从而把事实的大门敞开一条缝。大门一开,成功便易如反掌了。
二次大战开始时,工作条件要比第一次大战差得多。一九一四年八月,老天作美,加之细致的调查,在战争爆发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所有在英国的间谍便被一网打尽了。卡尔·洛迪是战争开始后第一个到达英国的德国间谍。在他到达前,早已布下罗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逮捕了。此案流传甚广,除非偶尔需要引证一下,我就无须重复了。一九一一年,德国政府代表团访英。代表团中一位高级官员总爱到加里东路的一家理发店理发。这是一家很不起眼的理发店,完全不是普鲁士的高级军官应光顾的那一类。这就立即引起了反间谍局的怀疑。理发师受到监视,所有来往信件被检查,一下子便查明了理发店原来是德国间谍组织在英国的“邮局”。英国当局不动声色,对该店继续监视,并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口这样,战争一开始,情报局便一举把德国间谍苦心经营了三年的组织全部摧毁了。这对德国间谍机构着实是一场灾难,在以后的交战过程中,再也没能重接上这被打断的链条口这一失败完全是由一个德国高级军官选择了一家不够上流社会标准的理发店理发所造成的。
二次大战爆发时,英国反问谍机构的处境就困难得多了。通常,伦敦的外国人总是很多,这些人同敌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九三〇年前后,伦敦的外国人由于德国和意大利难民的涌入而大大增加了。难民中的大多数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的,是一群叛逆者。纳粹和法西斯的间谍分子也就借此机会潜入英国。另外,纳粹分子在英国还有一批政治上的同情者,而一批希望和平的人则主张迁就希特勒,避免杀戮。
根据18-B国家安全法,战争一开始,重大嫌疑犯便被逮捕了。然而,网再大也不能将鱼打尽。人们反抗侵略的烈火刚刚燃起,便由于人身自由的被剥夺而被首先扑灭了。这不能不算是整个战争中最具有讽刺性的悲剧。许多忠诚的爱国志士反对执行18-B法令。无疑,有些判决是不公正的,使不少男男女女蒙受了不白之冤。例如,第一次大战时著名的“黑色入侵者”冯·林特伦,十分憎恶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后来虽证实他是无罪的,但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他却一直被关在切尔西。那时,我同他很熟,他始终不明白他想为之效劳的国家不利用他所掌握的对付德国间谍的丰富经验,反而如此不公正地抛弃了他。这就
应了那句“有所得,必有所失”的谚语了。不打破一些常规,便不能进行战争——这便是战争最大的灾难之一。
一九三九年一宣战,对来自许多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德国难民需要立即进行审查,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又有十五万难民蜂拥而至,他们大都来自丹麦、荷兰、挪威.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主要是由英国远征军的撤退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入侵所引起的口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德国空军一轰炸,这一本来就很棘手的问题就更麻烦了。英国必须捍卫自身的安全,而难民也需要加以照顾。
安置难民的临时措施是这样的;在伦敦设置五个收容点,一个在富勒姆,一个在巴勒姆,一个在布希公园,一个在水晶官,另一个在诺伍德。收容点是由伦敦郡议会设置的,每个点的负责人——瞧有多么幼稚!——由难民局的人担任。我在诺伍德呆过,对那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些。那里原是所医院,全是二层楼房,没有地下室,也没有阁楼,防空掩蔽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房屋四周草草围上了一道铁丝网,由士兵把守。
每天早上都有大量难民到达。从一九四一年六月起,难民到达的时间总和空袭碰在一起。有时,从伦敦来的车队一次运来的难民竟达七百人之多。男男女女的难民,个个精神沮丧,饥饿,离乱,亲人下落不明,都使他们极度失望。夜间,当突如其来的德国飞机用无情的轰炸对他们表示“欢迎”时,这些刚刚到达的饥寒交迫的难民便乱作一团,有时简直成了一群惊恐万状,大喊大叫的疯子。
在黑暗中把一群外国人的秩序整顿好实在不易。但又必须尽最大努力使他们安静下来,以便一个一个验明身份。然后,每人领取一份食物和一杯热饮料,下面的问题就是给他们找被子和安排过夜的地方。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维持好的秩序会立即被德国空军的轰炸重新打乱,惊恐又在可怜的人群中掀起轩然大波。德国空军的飞行路线总是经过诺伍德和水晶官。每天夜里,这两处总是要挨炸的。
天亮时,彻夜未眠的各点的头目已是精疲力竭了,但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去。难民洗完了操,换上消过毒的衣服,然后由大夫逐个进行体格检查。凡是有传染病症的人,麻疹也好,疥疮也好,一律隔离。经过长途跋涉,许多人需要进行治疗。
这时,反间谍局便开始工作了。七百人左右的行李都要进行严格检查。每张纸,每页书,每件衣服,包括衣裙和表缝,箱子和旅行包都要进行检查。这项工作不属于海关人员,必须做得一丝不苟。有的难民为了给予收容他们的国家一些帮助,随身带来了地图,照片,图片,提供德占区的详细情况。这些东西都要经过详细检查。
这些工作结束后,开始口头问话。可疑的人另行拘留,待进一步审查。
这一过程大约需要一周。在此期间,难民是被隔离的,不能接收信件,不能同外界接触,并随时准备接受反间谍局的审问。以后,他们便被送进难民局,由该局发给他们在英国“落脚”的证明。所有的嫌疑分子——其中也有无辜者——另行看守。有一份详细记载着难民情况的中央档案簿,通过这份材料,可以了解到每个难民的全部生活。即使一个对难民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只要翻开一看,他甚至可以为一个嫌疑犯进行辩护。
审查难民的这些临时措施一直使用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份,那时我和一个同事被派往克拉彭去组织一个特殊机构,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由于积累了前面所讲述的,在同难民日日夜夜的接触中得到的经验,我和同事们终于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用此方法审查难民,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麻烦,而对我们又是完全保险的。这时,难民潮业已过去,而审查人员的数目又在继续地增加着;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对付他们。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我被调到荷兰反间谍组织为止,我一直作为反间谍人员的负责人在该组织工作。在此期间,审查人员的数目从五人增加到了三十二人。
可以肯定地说,在那关键的六个月里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的一段时间,有几个间谍滑过了我们过分松弛的网眼。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很难确定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否是间谍。另外,审查人员少得可怜,没受过专门训练,难民又蜂拥而至,简直没时间对他们进行详细审查。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我在伦敦审查难民的工作仍没结束。由于法国的沦陷,除葡萄牙一小段外,整个欧洲海岸线都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通往大不列颠的唯一港口是里斯本,从里斯本来的船只仍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停泊。来自里斯本的水上飞机每周有两个班机蓟达伯恿默恩附近的昔尔,其他飞机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惠特彻奇降落。除了在伦敦的工作外,我还要带领一组审查人员去上述四个地方,对刚刚到达的人,英国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也好,进行审查。每去一地都需要几个小时的旅行。我想,我可能是反间谍组织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直到我完全调到克拉彭的维多利亚皇家爱国学校为止。那时,不管是乘飞机还是乘轮船来的人,都一律送往该柱进行审查。
这就是下面我所讲的故事的背景。
反间谍局在一九四O年遇到的问题要比一九一四年复杂得多。一九四〇年五月,情报局为接待潮水般的难民所做的准备并不比陆军部队为应付德国装甲部队的进攻所做的准备好。军队需要集结,要学会如何击退德国人,反间谍组织需要苦心经营自己的队伍。稍有不慎,后果就不堪设想。最近五年,我一直在等待着德国会出版某一德国人著的《我在英国从事间谍的岁月》一书,该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在英国愉快地度过了极其有益的五个年头的人,然而,此书至今尚未问世。如果有朝一日我在书店看到它,我丝毫也不惊奇。当然,如果这位设想中的作者仍在从事情报工作,或者根本不存在此人,那也就无从谈该书的出版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