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前面总有站头,只要她想回家,随时可以下车往回走。芝加哥就在前面,眼下她乘坐的火车每天往返,把芝加哥和她家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她家乡哥伦比亚城离得不算远。她甚至还去过一趟芝加哥。真的,几小时的火车,几百里路,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她看着上面有她姐姐地址的小纸片,心里问着自己。她把目光转向窗外,看着绿色的田野飞快地向后退去。随后她c@!!!l瘃?。
一个18岁的女孩离家出走,结局不外两种。也许她会遇到好人相助,变得更好;也许她会很快接受大都市的道德标准,而变坏了--二者必具其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好不坏,保持中不溜的状态,是根本做不到的。大城市具有自身种种诱人的花招,并不亚于那些教人学坏的男男女女,当然人比社会微小得多,也更富于人情味。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像最老于世故的人才可能想到的甜言蜜语一样乱人情怀。都市的万点灯火比起情人脉脉含情的迷人眼神来,那魅力是不差分毫的呢。可以说,有一半涉世未深的纯洁心灵是被非人为的影响力带坏的。城市里喧闹的人声和热闹的生活,加上鳞次栉比的楼房建筑,在令人惊愕的同时,又令人怦然心动,教给人们模棱两可的生活意义。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人在她们身边轻声告诫和解说,又有什么谎言和谬误不会灌入这些不加提防的耳朵里去呢?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看不清生活中的那些虚假外表,而为它们的美所倾倒,就像音乐一样,它们先令人陶醉松弛,继而令人意志薄弱,最后诱人走上岐路。
嘉洛林在家时,家里人带着几分疼她,已具有初步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她有利己心,不过不很强烈,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她充满着年轻人的热烈幻想。虽然漂亮,她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阶段的美人胎子。不过从她的身段已经可以看出将来发育成熟时的美妙体态了。她的眼睛里透着天生的聪明。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她们家已是移民的第三代了。她对书本不感兴趣,书本知识和她无缘。她还不太懂如何举手投足,显示本能的优雅举止。她扬起头的姿态还不够优美。她的手也几乎没有用。她的脚虽然长得小巧,却只会频频地放在地上。然而她对于自己的魅力已极感兴趣,对生活的更强烈的乐趣感知很快,并渴望获得种种物质的享受。她还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小骑士,正冒险出发去侦察神秘的大城市,梦想着某个遥远的将来她将征服这新世界,让那大城市俯首称臣,诚惶诚恐,跪倒在她的脚下。
“瞧”,有人在她耳边说,“那就是威斯康辛州最美的度假胜地之一。”“是吗?“她惴惴不安地回答。
火车才开出华克夏。不过她已有好一会儿感到背后有个男人。她感觉得到那人在打量她的浓密的头发。他一直在那里坐立不安,因此凭着女性的直觉,她感到背后那人对她越来越感兴趣。少女的矜持和在此种情况下传统的礼仪都告诉她不能答腔,不能允许男人这样随便接近她。不过那个男人是个情场老手,他的大胆和磁性般的魅力占了上风,所以她竟然答了腔。他往前倾着身子,把他的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开始讨人喜欢地聊了起来。
“真的,那是芝加哥人最喜欢的度假地。那里的旅馆可棒了。这地方你不熟悉吧?”“哎,不对,这一带我很熟的。”嘉莉回答。“你知道,我就住在哥伦比亚城。不过这里我倒从来没有来过。”“这么说,你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去了。”他猜测说。
他们这么交谈着时,她从眼角隐隐瞧见了一些那人的相貌:红润生动的脸,淡淡的一抹小胡子,一顶灰色的软呢帽。现在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脑子里自卫的意识和女性调情的本能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
“我没有这么说,”她回答。
“噢,我以为你是这个意思呢,”他讨人喜欢地装着认错说。
这人是为生产厂家推销产品的旅行推销员,当时刚刚流行把这类人称作“皮包客。”不过他还可以用一个1880年开始在美国流行的新词来形容:“小白脸。“这种人从穿着打扮到一举一动都旨在博取年轻心软的姑娘好感。这人穿着一套条纹格子的棕色毛料西装,这种西装当时很新潮,不过现在已经成了人们熟悉的商人服装。西装背心的低领里露出浆得笔挺的白底粉红条纹衬衫的前胸。外套的袖口露出同一布料的衬衫袖口,上面的扣子是一粒大大的镀金扣,嵌着称为“猫儿眼”的普通黄色玛瑙。他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其中有一枚是沉甸甸的图章戒指,这枚戒指是始终不离身的。从他的西装背心上垂下一条精致的金表链,表链那一头垂挂着兄弟会的秘密徽章。整套服装裁剪合度,再配上一双擦得发光的厚跟皮鞋和灰色软呢帽,他的装束就齐备了。就他所代表的那类人而言,他很有吸引力。嘉莉第一眼看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优点都看在眼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要记下一些这类人成功的举止和方法中最显著的特点,以防他们永久消失了。当然,服饰漂亮是第一要素,要是没有了服饰这类东西,他就算不得什么人物了。第二要素是身强力壮,性欲旺盛。他天性无忧无虑,既不费心去考虑任何问题,也不去管世间的种种势力或影响,支配他的生活动力不是对财富的贪婪,而是对声色之乐的贪得无厌。他的方法一贯很简单,主要是胆大,当然是出于对异性的渴望和仰慕。年轻姑娘只要让他见上一面,他就会用一种温和熟识的态度去套热乎,语其中带有几分恳求,结果那些姑娘往往宽容接纳了他。如果那女子露出点卖弄风情的品性,他就会上前去帮她理理领带。
如果她‘吃’他那一套献殷勤的手段,他马上开始用小名称呼她了。他上百货大楼时,总喜欢靠在柜台上和女店员像老熟人一样聊聊,问些套近乎的问题。如果是在人少的场合,譬如在火车上或者候车室,他追人的速度要放慢一些。如果他发现一个看来可以下手的对象,他就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打招呼问好,带路去客厅车厢,帮助拎手提箱。如果拎不成箱子,那就在她旁边找个位子坐下来,满心希望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可以向她献献殷勤:拿枕头啦,送书啦,摆脚凳啦,放遮帘啦。他能做的主要就是这一些。如果她到了目的地,他却没有下车帮她照看行李,那是因为照他估计他的追求显然失败了。
女人有一天该写出一本完整的衣服经。不管多年轻,这种事她是完全懂的。男人服饰中有那么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界线,她凭这条界线可以区别哪些男人值得看一眼,哪些男人不值得一顾。一个男人一旦属于这条界线之下,他别指望获得女人的青睐。男人衣服中还有一条界线,会令女人转而注意起自己的服装来。现在嘉莉从身旁这个男人身上就看到了这条界线,于是不禁感到相形见绌。她感到自己身上穿的那套镶黑边的朴素蓝衣裙太寒酸了,脚上的鞋子也太旧了。
“你知道,”他在继续往下说,“你们城里我认识不少人呢。”
有服装店老板摩根洛,还有绸缎庄老板吉勃生。”“喔,真的?”想到那些曾令她留连忘返的橱窗,她不禁感兴趣地插了一句。
这一下终于让他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于是他熟练地继续谈这个话题。几分钟后,他已经过来,坐在她的身边。他谈衣服的销售,谈他的旅行,谈芝加哥和芝加哥的各种娱乐。
“你到了那里,会玩得很痛快的。你在那里有亲戚吗?”“我是去看我姐姐,“她解释说。
“你一定要逛逛林肯公园,”他说。“还要去密歇根大道看看。他们正在那里兴建高楼大厦。这是又一个纽约,真了不起。”
有那么多可以看的东西--戏院,人流,漂亮的房子--真的,你会喜欢这一切的。她想象着他所描绘的一切,心里不禁有些刺痛。都市是如此壮观伟大,而她却如此渺小,这不能不使她产生出感慨。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会是由一连串的欢乐构成的。不过从他描绘的物质世界里,她还是看到了希望之光。有这么一个衣着体面的人向她献殷勤,总是令人惬意的。他说她长得像某个女明星,她听了不禁嫣然一笑。她并不蠢,但这一类的吹捧总有点作用的。
“你会在芝加哥住一段日子吧。”在轻松随便地聊了一阵以后,他转了话题问道。
“我不知道,”嘉莉没有把握地回答,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万一找不到工作的念头。
“不管怎样,总要住几周吧。”他这么说时,目光久久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单纯地用语言交流感情了。他在她身上看到了那些构成美丽和魅力的难以描绘的气质。而她看出这男人对自己感兴趣,这种兴趣使一个女子又喜又怕。她很单纯,还没学会女人用以掩饰情感的那些小小的装腔作势。在有些事情上,她确实显得大胆了点。她需要有一个聪明的同伴提醒她,女人是不可以这么久久地注视男人的眼睛的。
“你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她问道。
“你知道,我将在芝加哥逗留几星期。我要去我们商号看看货色,弄些新样品。也许我可以带你到处看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我得住在我姐姐家,而且”“嗯,如果她不许的话,我们可以想些办法对付的。”他掏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好像一切都已说定了。“你的地址是哪里?”她摸索着装有地址的钱包。
他伸手到后面的裤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皮夹,里面装着些单据,旅行里程记录本和一卷钞票。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前向她献殷勤的男人中没有一个掏得出这么一个皮夹。
真的,她还从来没有和一个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见多识广性格活跃的人打过交道。他的皮夹子,发光的皮鞋,漂亮的新西装,和他行事那种气派,这一切为她隐隐约约地描绘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花花世界。她不由得对他想做的一切抱着好感。
他拿出一张精美的名片,上面印着“巴莱·卡留公司”,左下角印着“查利·赫·杜洛埃。”他把名片放在她手上,然后指着上面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这字要念成杜--埃。我们家从我父亲那面说是法国人。”他把皮夹收起来时,她的目光还盯着手上的名片。然后他从外套口袋掏出一札信,从中抽出一封来。“这是那家我为他们推销货物的商号,”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信封上的图片。“在斯台特街和湖滨大道的转弯处。”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自豪。他感到跟这样一个地方有联系是很了不起的,他让她也有了这种感觉。
“你的地址呢?”他又问道,手里拿着笔准备记下来。
她瞧着他的手。
“嘉莉·米贝,”她一字一字地说道,“西凡布仑街三百五十四号,S·C·汉生转。”他仔细记下来,然后又掏出了皮夹。“如果我星期一晚上来看你,你会在家吗?”他问道。
“我想会的。”她回答。
话语只是我们内心情感的一个影子,这话真是不假。它们只是一些可以为人听见的小小链子,把大量听不见的情感和意图串联起来。眼前这两个人就是如此。他们只是短短地交谈了几句,掏了一下皮夹,看了一下名片。双方都没意识到他们的真实感情是多么难以表达,双方都不够聪明,瞧不透对方的心思。他吃不准他的调情成功了没有。而她一直没意识到自己在让人牵着鼻子走。一直到他从她口里掏出了她的地址,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输了一着,而他却赢了一局。他们已经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了某种联系。他现在在谈话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轻松地随便聊着,她的拘束也消失了。
他们快到芝加哥了。前面就是芝加哥的迹象到处可见。这些迹象在窗外一掠而过。火车驶过开阔平坦的大草原,他们看见一排排的电线杆穿过田野通向芝加哥。隔了老远就可以看到芝加哥城郊那些高耸入云的大烟囱。
开阔的田野中间不时耸立起两层楼的木造房屋,孤零零的,既没篱笆也没树木遮蔽,好像是即将到来的房屋大军派出的前哨。
对于孩子,对于想象力丰富的人,或者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近一个大城市真是奇妙的经历。特别是在傍晚,光明与夜色交替的神秘时刻,生活正从一种境界或状态向另一种境界过渡。啊,那即将来临的夜色,给予劳累一天的人们多少希望和允诺!一切旧的希望总是日复一日在这个时刻复苏。那些辛劳一天的人们在对自己说:“总算可以歇口气了。我可以好好地乐一乐了。街道和灯火,大放光明的饭堂和摆放弃整的晚餐,这一切都在等着我。还有戏院,舞厅,聚会,各种休息场所和娱乐手段,在夜里统统属于我了。"虽然身子还被关在车间和店铺,一种激动的气氛早已冲到外面,弥漫在空气中。即使那些最迟钝的人也会有所感觉,尽管他们不善表达或描述。这是一种重担终于卸肩时的感觉视着窗外,她的同伴感染到了她的惊奇。一切事物都具有传染力,所以他不禁对这城市重新发生了兴趣,向嘉莉指点着芝加哥的种种名胜和景观。
“这是芝加哥西北区,”杜洛埃说道。“那是芝加哥河。”他指着一条浑浊的小河,河里充塞着来自远方的帆船。这些船桅杆耸立,船头碰擦着竖有黑色木杆的河岸。火车喷发出一股浓烟,切嚓切嚓,铁轨发出一声撞击声,那小河就被抛在后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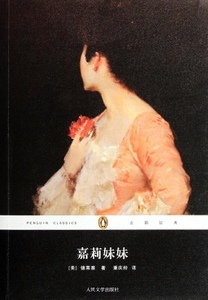
“芝加哥会是个大都市,”他继续说着。“真是个奇迹。你会发现有许多东西值得一看。”她并没有专心听他说话。她的心里有一种担心在困扰着她。想到自己孤身一人,远离家乡,闯进这一片生活和奋斗的海洋,情绪不能不受影响。她不禁感到气透不过来。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她的心跳得太快了。她半闭上眼睛,竭力告诉自己这算不得什么,老家哥伦比亚城离这里并不远。
“芝加哥到了!”司闸喊道,呼一声打开了车门。火车正驶入一个拥挤的车场,站台上响彻着生活的嘈杂和热闹。她开始收拾自己可怜的小提箱,手里紧紧捏着钱包。杜洛埃站起身来,踢了踢腿,弄直裤子,然后抓起了他的干净的黄提箱。
“你家里有人会来接你吧,”他说,“让我帮你拎箱子。”
“别,”她回答,“我不想让你提。我和姐姐见面时不想让她看见你和我在一起。”“好吧,”他和和气气地说,“不过我会在附近的。万一她不来接你,我可以护送你安全回家的。”“你真好,”嘉莉说道。身处目前这种陌生的场合,她倍感这种关心的可贵。
“芝加哥!”司闸拖长声音喊道。他们现在到了一个巨大的车棚底下,昏暗的车棚里已点起灯火。到处都是客车。火车像蜗牛一般缓缓移动。车厢里的人都站了起来,拥向门口。
“嘿,我们到了。”杜洛埃说着领先向门口走去。“再见,星期一见。”“再见,“她答道,握住了他伸出的手。
“记住,我会在旁边看着,一直到你找到你姐姐。”她对他的目光报以微笑。
他们鱼贯而下,他假装不注意她。站台上一个脸颊瘦削,模样普通的妇女认出嘉莉,急忙迎上前来。
“她喊道。”随后是例行的拥抱,表示欢迎。
嘉莉立刻感觉到气氛的变化。眼前虽然仍是一片纷乱喧闹和新奇的世界,她感觉到冰冷的现实抓住了她的手。她的世界里并没有光明和欢乐,没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娱乐和消遣。她姐姐身上还带着艰辛操劳的痕迹。
“家里人还好吗?”她姐姐开始问道,“爸妈怎么样?”嘉莉一一作了回答,目光却在看别处。在过道那头,杜洛埃正站在通向候车室和大街的门边,回头朝嘉莉那边看。当他看到她看见了他,看到她已平安地和姐姐团聚,他朝她留下一个笑影,便转身离去。只有嘉莉看到了他的微笑。他走了,嘉莉感到怅然若失。等他完全消失不见了,她充分感到了他的离去给她带来的孤独。和她姐姐在一起,她感到自己就像无情的汹涌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孤苦无依。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