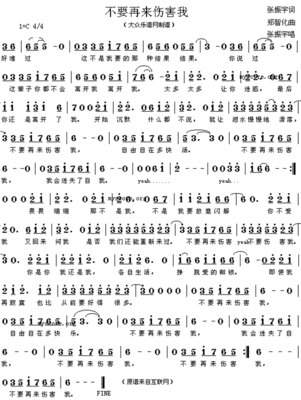十二月一日是我重生之日。三年前的这天,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家庭,把他们至爱亲人的肝脏捐赠给了我,使患了绝症的我得到重生。
故事要回溯到2004年。那一年初,我的小叔诊断出患了肝癌,他是由乙形肝炎导致的,四个月之后便离世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因为我也是病毒携带者。趁回国探视他的那段时间我做了超音波及核磁共振等的检查,赫然发现肝脏里有一个1.8公分的阴影,说可能是血管瘤,但多种检查均不能确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追踪监测着它,每三个月验一次血,每半年做一次或是超音波、或是断层扫描、或是核磁共振一类的检查。2007年四月,我照例又做了抽血检查。一周后去看报告时发现AFP值为五十多(正常值是9以下,而医生竟然没有通知我!),当下又再验血、做断层扫描等,基本确诊那个“血管瘤”其实就是个肝癌。私人开业的华人肝科医生把我转介到位于比华利山的西达赛奈医疗中心进行治疗,那所医院有做肝脏移植。六月中,做了第一次“介入”治疗。放射科医生把一条导管从髂动脉伸进我的肝脏,把药物注射入癌瘤部位,并把营养癌瘤的血管堵塞住,毒死及饿死癌瘤。做完介入治疗后,AFP下降至接近正常,接着又回升。三个月后再做核磁共振检查,又发现两个2公分的阴影!十月份再做了一次介入,证实新长出的癌瘤其实只有一个,把它杀死之后,病情暂时稳定。
做了第一次介入治疗之后,医生们就安排我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对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把我列入肝脏移植等候名单上。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UNOS,是UnitedNetwork for OrganSharing的简写,中文可译为“器官共享联合网”,与联邦政府有合约,为联邦政府掌管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一切事务,例如,审核等候名单;安排捐赠者和受赠者的配对;安排器官的分配,确保等候移植的病人,无论他们的年龄、性别、族裔、宗教、生活方式、财务状况或社会地位为何,都能受到公平对待;还有对病人及其家属或朋友提供帮助等等。等候肝脏移植的病人按“MELD”分数,分别病情的轻重缓急,或迟或早获得捐赠器官的分配(当然有很多人等不及,在等待之中去世)。“MELD”全称是“ModelforEnd-Stage LiverDesease”,中文意思是“末期肝病模式”,分数越高的,需要做肝脏移植的情势越迫切,在名单上排得越前。捐赠完全是无偿的,捐赠家庭不能获得金钱报酬,且与受赠病人并无任何关系;受赠人除了负责应负的医疗费用,不须为受赠器官付任何金钱或礼物,如果不是病情需要,无法花钱买时间,获得快速的安排。
医院为了方便我,在完成各项相关检查之后,肝脏移植小组的协调员(这是美国医院器官移植团队内的一个特殊角色,不知国内医院的移植团队有否这样的人员?我在医院实习过,知道普通科室是没有的)安排我在同一天看了各个相关科系的医生---其实是各科的医生到肝脏科诊室来看我,我是坐着不用动的。心脏科的医生来检查我的心脏情况;胸科的医生来评估我的肺功能;还让心理医生来看我,看看我有没有因患了癌症而患上焦虑症;最后来了个社工---医院都配有专门的社工,英文是“socialworker”,社会工作者---来看看我有没有财务方面的困难需要帮助以及手术后的照顾安排(他们叫“caregiver”,在病人手术后提供照顾的人,可以是家人或朋友)。各科各项检查都显示出我身体状况良好,应能承受肝脏移植这样的大手术,最后,我的名字加进了等候名单上。这时是2007年九月。
在六月份做了第一次介入治疗后,AFP值未下降至完全正常复又升高,医生的解释是下降至正常需要时间和它会有波动,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是不信服的,但医生答应说三个月后再做核磁共振检查,我想,就算有新癌瘤长出来,也需要时间让它长至一定程度大小才容易被检测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就只能等了。结果在十月初AFP值又飙升至四百多,一个新的癌瘤在短短三个月内从无到有长至两公分(影像上说是两个,但做介入时发现只有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出入),足见病情来势凶猛。十月下旬做了第二次介入治疗。原来我对接受肝脏移植还有一定的顾虑,怕排斥,以后终身不好照顾,但在发现又有新癌瘤长出来之后,我就坚定了准备接受移植的信心,并且恨不得能尽快进行。只有进行肝脏移植,才是根治的办法。给我看病的一个高级护师(美国的护士分很多个级别,有些护士是取得硕士学位的,跟在医生身边工作,可以代替医生开一些处方,在中国,没有对等的职位)告诉我,我大概得等大半年,约在2008年的五或六月份才会“qualified”---符合资格,这时我开始有点儿焦急了。好在我遇到很多“贵人”。在做各项检查进行全面评估的那天(也是为了方便我,他们把所有检查安排在同一天进行),我遇到了王先生,他是一个五年后的肝脏受赠者,他感恩得到了生命的馈赠,为了回馈社会和医院,每个星期抽一天回医院当义工。他带我跑各个科室完成各项检查(有识途老马的指引,我方便多了),作用更大的是他介绍我参加了医院组织的病员互助网,互助网由医院的一个社工主导,大家通过连了网的电邮传达消息,社工时常给大家发电邮,通报一些有关器官移植的消息和资讯,病员们如有问题,也可通过发出电邮提出,由知道答案的病员发出电邮来解答。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另一个贵人,简.芭蕾女士和她的先生,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简.芭蕾的先生三个月前在加州最南端的大城圣地牙哥接受了肝脏移植。他是五月份参加到那边去的,七月份就得到了肝脏移植。简.芭蕾女士建议我也到那边找一家我的保险公司特约的医院挂上钩,在圣地牙哥和洛杉矶两边同时等待。我于是便这样做了。我何其幸运,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去UCSDMedicalCenter(洛杉矶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医学中心)跟我将来的两个医生---埃及裔的肝科医生哈辛尼和美国黑人外科医生马克斯.哈特进行首次会面,仅仅五天之后,十二月一日的下午,我就接到了要我马上赶过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好消息。
UNOS分配器官的原则,除了根据MELD分数,还按就近先分配的原则进行。先在捐赠者发生地附近地区配对等候名单上符合资格的病人,如果附近没有人合符条件,就扩大配对的范围至跨出县界、州界甚至进行国际性的捐赠。我就是受益于这一原则,在一个等候名单相对不那么长的地区在短得多的时间内等到了。好像冥冥中已有天意的安排,那天我刚洗了头、洗过澡(我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卧床不起不能洗头洗澡)、家里小朋友刚参加完一个考试,她老爹刚把她接进家门、我又刚吃过午饭(恐怕得有几天不能吃饭),电话就到了。出门的必要行李,如换洗的衣物、简单的锅碗瓢盆(美国有些酒店有些套间带厨房,老夫子得在那边住上一阵子了)早就预先准备好放在车子行李箱里了,当下马上起行。往圣地牙哥去的两个小时车程里,好像大家的心情并不沉重,没有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没有人担心手术会不成功。不知他们俩心里想什么,在我来说,没有比不移植更糟的情形了,所以我心境是出奇的平静。四点多到了医院,进行了各种术前再检查,七时半各种报告出来了,我被送进手术室,八时许手术开始,凌晨一时许,哈特医生来到家属等候室,告诉老夫子手术非常成功,手术过程中我失血很少,只输了少量血。经过这样的“浴血奋斗”,我得到了重生!
术后第二天我在加护病房醒过来,身上插满了管子,象一只大蜘蛛。我在重症加护病房ICU度过了头两天,第三天转到了轻一级的加护病房IBU。实习医生每天来给我拔管子,我一根一根的数,大概花了六、七天时间拔完,一共是十三根管子!
美国医院的设备和技术、人员配备都是一流的。患上肝癌后一共住过五次院(在西达赛奈两次介入治疗住院、一次因介入治疗后发生急性腹痛回去住院、在圣地牙哥医疗中心进行肝脏移植住院、出院后有过一次发生排斥回去短暂住院),都住的是单人病房。据说也有双人及四人的病房,但我没有遇到过。医院病房不分级别,没有象国内那样,有什么高干病房、华侨病区等的分别。我住的单人病房内,有电视、电话、厕所(西达赛奈医院更好,厕所内还有淋浴间)、简便沙发;每顿饭送到床边,护士包办一切,基本上随叫随到(很忙的时候会稍慢一些),所以不用陪人。又有营养师来配我的伙食,第四天能下床了,复健师就来帮助并督促我下地行走。我想国内的高干病房也不过是如此待遇吧!可能因为是公立医院,在同病区,还不时见到有警务人员在某些个病房门口守卫,里面有监狱犯人也在此住院。这在西达赛奈医院倒是没见过的。不过医生查房倒不象国内,一定在上午来,美国医生查房没有定时,有时下午才来,有时甚至一天不见人影。美国的护士是两班倒,从早上七时半上班至晚上七时半交班,每周工作三天。经历了与美国医院、医护人员长期打交道,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不是一般的好(也曾经有一、两个护士不是那么好,但这不影响我对他们的总体印象)。在2007年11月26日第一次见到我的手术医生哈特医生和肝科医生哈辛尼医生,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对老夫子说,我非常喜欢这两位医生。他们都是如此彬彬有礼、耐心、细心和周到(而在华人圈子执业的华人医生,可能因为有挣钱的压力---他们必须挣足够的钱维持诊所的运作和雇员的工资,就不能做到那么耐心细致,尤其他们喜欢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让病人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让人感到他们事事都跟钱挂钩)。住了十天医院,出院之后,又认识了肝脏移植医疗组内其他几个专门负责移植后病人的护理的协调员(就是前述那样的高级护士,医生的助手),她们也都是那样的细心、热情、负责和富有同情心。你现在可以理解,我对能来到美国生活是如何地感恩---不仅仅是能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更因为美国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获得重生。如果没有我生命里的那位大恩人---我的肝脏捐赠者捐赠给我生命之礼(美国人的话是“giftoflife”),没有哈特医生和哈辛尼医生高超的技术为我治疗,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帮我付了绝大部分费用,恐怕我今天已经不在了吧!
这里我得说一说美国的医疗制度。美国的医疗制度是最让人诟病的,在发达国家排名是敬陪末座。在美国是不怕你穷,越穷越好,穷人有政府的医疗福利,俗称“白卡”,拿着那个医疗卡看病免费。残疾人或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则有联邦提供低费医疗保险,不那么穷年纪又不够老的,如果有工作单位的,靠工作单位给买医疗保险,没有工作单位的就得自行掏腰包买保险了。我是有先生的工作单位买有包括家属的医疗保险,三十多万的手术费自付额仅是数千元,术后每月数千元的药费也仅付三百来元。如果有人真的没有保险呢?那也不用担心,突发的急诊,美国医院是先治疗后来账单的,那时候你还可以从长计议;如果是慢性大病,或急性大问题,医院的社工会自动来找你的。我们家一个朋友,十年前她来美国不久,有一天在加油站加油,错把倒车档当停车档,从车里一出来,车门往回打,打断了她的腿骨,救护车送进了医院,社工来了,一了解,属于新移民低收入户,马上给她办了一个“白卡”,半年有效。这个事故没让她花过一分钱。还是她,在我做肝脏移植的期间,她发现患了“结肠癌”,她自忖在国内有公费医疗(她是小学老师,退休了才来美国),且又怯于英语的沟通问题,便回国治疗。虽说是“公费医疗”,但很多药物及检查还是要自费,结果她花了十多万人民币。回美国后继续后续的治疗,发现转移至骨,又再进行放疗,社工又给她办了白卡,还因为她不能上班成了残障,每月国家还补贴她生活费六百多元,她先生也因为要照顾她而“不能外出工作”,也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取到六百多元的生活补助。还有专人每次来接送她去做放疗。后来美国的医生又发现她患的不是“结肠癌”而是甲状腺癌。在美国的治疗没让她花过一分钱。有美国先进的治疗,她现在还是好好的。她很后悔,说早知道,在美国治疗就好了,跑回去白折腾,还花了自己十几万。
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最怕出现的是不大不小的状况。譬如我的一个朋友,小孩子患了急性阑尾炎,住了三两天医院,这种情形可以花掉你三万五万的。这个情况下,社工又不来,没有政府给你扛,就只能自己慢慢还了(好在那个朋友有给孩子买了一个“住院险”,光保住院的开支,帮她付了大部分医药费)。不过就算不还,医院也不能把你怎么的。我的另一个朋友,她的哥哥有一天突然中风送到医院,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出院后回台湾去了,落下了五十多万医疗费,至今才付了一万多,好像算是“搞定了”。也有政府的医院,可以免费看病,阿罕布拉市最近就成立了一家。多年前我在一个私立的英语学校学英语,班上那个白人英语老师说,很多人到公立医院看病,看完病账寄单来了,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有医疗保险的问题是,病起来想到私人开业的诊所去看病,倒是得真金白银先奉上诊金,“没钱同鬼讲”在那里倒是真的。
美国的肝脏移植技术中有一点值得一提,如果病人原来患有B型肝炎,换肝后医生会马上给病人滴注高滴度的B型肝炎抗体,把病人体内的病毒中和掉,还继续滴注直到病人体内B型肝炎抗体滴度达到一千以上。我在术后连续滴注了七天,出院后第四个月开始,体内滴度又下降了,医生又给开处方给予肌注抗体,每月一次维持。除了长期服食抗排斥药物,还加上长期服食抗病毒药,确保B肝不再复发。所以,在美国因为感染了B型肝炎而导致肝癌的病人,换肝后是连B型肝炎病毒也清除掉了,能够确确实实获得了新生。曾经看过国内报导,说B型肝炎而导致肝癌的病人,换肝两年后肝炎又复发会导致病人在短时间内死亡。不知现在国内解决了这一问题不曾?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令我又怒又哀的事。这事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我的祖国。在我决定了准备等候肝脏移植而西达赛奈医院的护师告诉我得等半年以上时,我有点儿焦急,有朋友建议我不妨试试回国内寻找肝源。我就在广州市的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网页上填写了表格登记等待肝脏移植,两年多来没有回音,从来没来过任何信息说收到我的登记表格,上个月倒是来了一封电邮,我一看,又怒又哀又气,马上把它洗掉了,洗掉了才想到我应把它留着,让大家把它源源本本的看个清楚。现在只能凭记忆说个大概。那封电邮说如果我愿意交纳两万元人民币(记得好像是可以算进将来的手术费之内),他们将保证在两个月内为我找到合适的肝脏,如找不到的话,两万元可以退还给我云云。我当时立即的反应是:荒谬!一个人什么时候死你怎么能保证?继而一股怒气和悲哀的感觉涌上心头:怒是怒其不争---怎么我的祖国的风气堕落到了这个地步,从前救死扶伤的伟大医生们怎么变得全没了人味只有钱味;哀是哀其不幸---祖国的穷老百姓有需要换肝的,从此将永远等不到了,因为他们没钱!肝脏总是被那些能先交得出两万元的人先抢了去了!穷人的命运是何其的不幸!相比美国等候器官移植,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公平按病情缓急安排次序,在拯救生命方面,怎么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反而比美国更不“人民”呢?
在今天重生三周年之日,回顾重获新生的历程,心潮起伏,充满心里的是感恩,深深的感恩。千言万语只能化作简单的一句:谢谢!谢谢我生命中的大恩人,那位我不知姓名、馈赠我以生命之礼的捐赠者;谢谢令人崇敬的哈特医生和哈辛尼医生;谢谢我的贵人王先生和简.芭蕾夫妇;谢谢西达赛奈和圣地牙哥医疗中心肝脏移植小组的全体医护人员;谢谢在我获得重生过程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你们的恩情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感谢您,敬爱的马克斯.哈特医生! Thank you, DrMarquis Hart!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