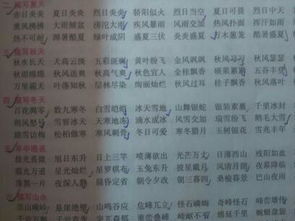2012年7月23日,慕容雪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以下是讲稿全文
如秋水长天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