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莞张氏之表彰袁督师——兼考袁督师在京故迹(转)_tmg26 袁督师
——兼考袁督师在京故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姜纬堂
出版者: 莫乃群主编
出版地: 南宁
出版日期: 1984.10
一
晚清之际,有识之士于奔走呼号拯时救世之余,多留意于明季史事之推求,“以淬厉民族气节”。[1]时尚所及,尝为“东事”干城之蓟辽督师袁崇焕,亦被重新提出,再成论题。语其肇端,则为新会梁启超之著《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2]言其后继之具影响者,除东莞陈伯陶(九龙真逸)外,则有东莞张伯桢父子之“两世一肩,承荷不衰”,[3]“以表彰袁督师为职志”。[4]
伯桢(1877—1947),字任材,号子干,又字沧海,别号篁溪。自廿一岁由原籍东莞赴广州从学于万木草堂,遂成南海康有为之忠实弟子。1904年负籍东瀛,与朱执信、邹鲁、汪兆铭、程树德等同学于东京法政专科学校。1908年毕业归国,与马叙伦、伦明等共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次年,赴京应游学生考试,授法科举人,签分法部,以七品小京官在制勘司行走。见知于该部侍郎沈家本。民国成立,改任司法部佥事。1914年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1928年政府南迁,解职。嗣后,除一度出任广东法官学堂监督外,长期息影京华,以鬻文、著述为业。后从班禅司佛典,法名罗桑彭错,又号仁海居士。自1917年于北京创建袁督师庙后,复别署袁庙祝驼。[5]生平刊有《沧海丛书》五辑,[6]所著除见于该丛书者外,尚有近代史料多种,泰半坡露于六十年代以来政协所编《文史资料》。临终前,以珍藏康有为、梁启超书牍墨迹、袁督师文物及佛教法物一千三百余件,捐赠北平历史博物馆,以著述稿本及所藏金石拓片一百余件捐赠北
平图书馆,对论称之。[7]
其长子仲锐(1909~1968年),字江裁,号次溪,晚署涵锐。1913年,从父移居北京。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及孔教大学。1929年末,入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从事北京史研究。以治梨园史,尤其是北京史有声于时。秉承家学,亦积极于表彰袁督师,尝自颜其斋曰拜袁堂。后未能恪勤操守,于1943年出任汪伪淮海省教育厅长等职,[8]非惟有负“拜袁”初衷,且成名节之大玷。解放后,入“华大”学习,痛悔前尘。后经分配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事研究辛亥革命史,为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编者之一。生平著述甚富,尤长于史料之辑集、整理与编纂,刊有《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燕都风土丛书》等多种丛书,见称于学林。[9]
伯桢尝谓:“袁督师为我邑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吾幼年读《明史》,慕其为人。每过其祠,瞻其遗像,为之呜咽流涕不忍去”。[10]乃以“我与督师同隶东莞籍”,“表彰先烈乌可辞?”[11]计其父子于表彰袁督师之所为,大抵有四。除经营督师在京故迹,容专为详述于后外,余三者为:
其一、搜罗督师遗著、遗物及有关文物。
早在东渡之前,伯桢即已“搜求文献,得督师秦疏、杂文、遗诗,汇为一卷,题曰《袁督师遗集》。复搜辑与督师有关系之文,汇成一册,名曰《附录》。乙巳(按:为1905年)携之扶桑,质诸梁任公先生。”[12]后收入其1913年刻于北京之《沧海丛书》第一辑中,凡《袁督师遗集》三卷、《附录》一卷,康有为作序,梁启超题签。1932年又行补刻。按:督师之有遗著传世,始见于余大成《剖肝录》所述“将所汇(崇)焕前后章疏十本,付(崇焕弟崇)煜藏之,盖自为督师至下狱时所言职方副本也。又见于屈大均《翁山文录·王子安先生哀辞》所记其于浙东王氏得所藏“袁大司马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讼冤诸疏”,而携之岭南。此盖嘉庆、道光间佚名辑刊《袁督师事迹》[13]中所收督师秦议等之所由来。惟其书流布不广,迨1850年伍氏粤雅堂重刊于《岭南丛书》第五集中,方显于世。虽其未标督师遗著之名目,仍题《袁督师事迹》,然实为张氏《沧海丛书》本之所据。自张氏刊本,始题为《袁督师遗集》,且经初刻与补刻迭相发行,流布之广,尤非《袁督师事迹》所能比。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14]所著录与《明清史料汇编》第八集[15]所影印者,皆为张氏本《袁督师遗集》,即可见其情形。
随研究袁督师之不断深入与本世纪前期明清史料之渐次发掘,督师遗著多有发现。1941年张次溪复就当时所得网罗者,辑为《袁督师遗稿》。[16]以较其父当年所刊者,凡增奏疏三篇(原为九篇)、函牍及文四篇(原为四篇)、诗一首(原为十一首)。虽其至晚年犹抱憾于未及觅见《三管英灵集》,致失载其中之督师遗诗,[17]然其所辑终较前此为多,故仍为后此数十年间考论督师者之所资。
督师既冤死,举家亦被罪,故督师遗物之存于天壤间者殆如晨星,其见于记载者,惟遗像与《镡津考古录》所记之大纛。张氏于此亦不惮搜求。先是伯桢尝觅得督师遗像、遗墨,具刻石及庋藏于其所经营之北京袁督师故迹中,详见后述。继有次溪之求得金梁旧藏督师手书七言联:“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真源。”又[17]复搜得督师铜雀瓦砚、未央瓦砚、紫檀笔床及砚匣等物。渠尝有记,谓:“铜雀台瓦砚……漆匣面刻‘袁誓师遗砚’五字,燮阳居士所题。按:居士即东莞陈策,字纯伯。当援辽时,有诗别亲友云:‘诸君蘸墨悬相待,不是铙歌即挽歌。’其忠勇勋业,可与督师争烈。匣则明漆工黄筱成手制,上刻袁督师识语,曰:‘建瓴建瓴,剜右赋形,未央沈碧,铜雀凝青,含其抱璞,岳峙渊停,侯封即墨,鲲起南溟,磨牙盾鼻,杀虏穹庭,势如破竹,若发新硎,凯旋钦至,式昭德铭。’下署:‘天启辛酉三月,东莞袁崇焕’。旁有赖文光识语两行,曰:‘此为明东莞袁元素督师故物。方今天军北指,上帝眷顾,天恩浩荡,犁庭扫穴,咄嗟间耳。恭献东王殿下。太平天国丁巳七月亥日,殿前检点使、木一丙三总制检军司马、平天贵赖文光百拜上。’字略欹斜,板挺秀。”“东王既殂,展转至淮阳,民国初归方地山,又三十年,余乃得之。庚子(1960年)二月十一日,章行严师八十寿辰,遂以紫檀笔床呈献留念。三月初一日,汪公岩丈九十生诞,复以未央宫瓦砚为寿。至铜雀台瓦砚及原有漆匣,失诸旅途,殊为恨事。”[18]据称罗振玉曾跋督师铜雀砚拓片云;“……吾友埭山水部精赏鉴,富收藏。公寓津沽时,与讨索金石。其介弟地山解元,世居扬州。癸丑夏甓社湖西某旧家式微,子孙不能守,舁藏物入郡求售,地山斥重资得之,如获瑰宝。”[19]张氏谓得之于方地山家,本此。按:所谓赖文光题诗,据所署年月考之,其时东王已亡,亦与“天军北指”不协,且署衔及所用历日,直书讳字等皆与太平天国制度不符,论者已辨其伪。[20]而据督师识语署籍东莞,与进士题名牌不符,且在天启元年未任边事之时,即发“杀虏穹庭”,““凯旋饮至”等语,则其真实性,亦颇值推求。其真赝固有待进一步鉴定,然亦足令景慕督师者称喜。惜已零散,倘得聚而全之,亦不失为世人追怀督师之一段佳话。
至有关督师文物之搜罗,其最著者即赵惇夫所绘《肤功雅奏图》之发现。该图为长汀江瀚旧藏,其乃得之于桂林王鹏运。虽上款剜去,然王氏“考为袁督师任蓟辽总督时,同人赠行之作,其说甚确”。[21]卷后附陈子壮、邝瑞露等十八人题诗。于考镜督师行迹,弥为珍贵。经东莞伦明借归,与容庚、张徨溪父子等,于1935年集资加以影印流布,题《袁督师督辽饯别图诗》。张氏复将图附题诗与跋语,辑入其《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二,益广其传。题诗诸家,除释氏三人外,余多明季忠义之士。展之,不惟得睹昔日江干饯别之景况,亦于督师之交游及其思想、性格之形成,多见线索。
其二、考论督师史实、遗事。
伯桢有感于“《明史·(袁崇焕)传》讹阙尚多。其最误者,则未审东江所在,而于毛文龙逆迹又不甚详,且附会之以为妄杀;其于虎墩兔、刘国祚,概不之及,而‘五年平辽’方略,一若大言自诡,而不究其成算之未得行;其狱之冤,虽知为清朝设间,又不知突出温体仁;皆失之大者也。梁(启超)先生撰《(袁崇焕)传》时,适居日本横滨,海外无私籍野史参订,亦略而不详”。[22]乃决意“搜罗野史及秘档,详细论列,以正《明史》之误,暨补梁先生之阙,”于1935年著成《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23]连同《补遗》、《附录》,近八万亩。复取“限于篇幅”所不及载之督师遗事,辑为《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闻录》,[24]凡三万言。由于广采秘书、野记、方志,尤其是大量运用档案材料,故时人誉为“掇拾之详备,……无逾此传者。”[25]是传非特为张氏研求多年之心得,亦且为当时关于袁督师研究之最新成果。即就今日观之,虽因明、清及朝鲜李朝《实录》、《满文老档》之次第流布及多种秘书复出,其所据史料显有不足,且其以英雄史观持论,致有偏颇,然其考索勾稽之功,端不可没。其于推进袁督师研究之贡献,则尤载诸论者之口。[26]嗣后,其子次溪复据屠寄《富将军战略》所述线索,鸠集文献,于1939年辑为《东莞袁督师后裔考》。[27]督师传后于瑷珲,虽在疑似之间,[28]然寻根梳理,亦足广异闻,有俾参考。又将当时所得网罗之督师史料,汇为《东莞袁督师遗事》。[29]复于1941年并二者及督师遗稿为《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六卷,包罗之富,远在其父当年所刊《遗集·附录》之上。晚清以来,研究督师之成果,“一翻阅而悉备,”[30]颇便寻检。
其三、吁请崇祀督师。
1915年,袁世凯政府开礼制馆,重议民国敬祀先哲名单。经伯桢献议,兴武将军朱瑞于增祀武庙名单中列入袁崇焕,以呈大总统,袁即发交政事堂礼制馆核仪。礼制馆以袁崇焕“原系文臣,无庸置议”具覆。张氏乃草《袁督师应配祀关、岳意见书》,以十大根据驳礼制馆之说,复请于政府。更联络当时十八省之将军、督、抚及北京各部、院长官,以至在京粤籍官员、名流、广东地方绅耆共二百人,分头吁请总统驳回礼制馆原议,崇祀督师于武庙,“以阐幽光”、[31]“壮士气而励忠贞”。[32]虽其“为此事,两年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33]然袁氏之开礼制馆本在为帝制张目,岂复有暇及此?故崇祀督师之议,最终不了了之。张氏慨于曲尽心力,奔走徒劳,乃辑共始末并其间往复函扎,编为《袁督师崇祀关岳议案》[34]七卷,冀“使后世读是书者,得知此案之真相”。[35]按:自乾隆四十八年五月诏谕以督师子孙补官、嘉庆三年九月准以督师入祀乡贤祠,清室虽于督师有所褒崇,然非国典。张氏所争者,在使督师之崇祀升格为国家级,以与所谓“武神”关羽、岳飞并列。由今日言,历史人物之地位,固不在祠祀与否。然当清社方屋、民国肇立之时,则享庙传统未衰,宜张氏之有此争。
二
张氏表彰袁督师,尤以营护督师在京故迹为驰名。计其所致力者有三:
第一、创建袁督师庙。
1916年,伯桢捐资于北京左安门内东火桥广东新义园中之高阜(其地在今北京龙潭湖公园内),兴建袁督师庙。庙计三楹,面南坐北,为木梁砖砌硬山式建筑。门额“袁督师庙”四字为康有为尺大楷书,两旁则为康有为撰书之长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庙内正中嵌督师遗像刻石,像附督师手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36]两旁则为康有为撰书之七言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所余四壁分别嵌有康有为撰书之《庙记》、王树楠撰、宋伯鲁书之《庙记》、张篁溪纂集、宋伯鲁书之《袁督师遗诗》等刻石。康、宋书法皆见重于时,康氏小楷,世不多见,所书《庙记》尤为珍品。全庙之刻石,皆出于当时北京刻石名家高学鸿之手,亦为镌刻精品。自1917午5月落成后,遂“为旅京乡人岁时荐享(督师)之所”。[37]张氏复即其事,著为《北京袁督师庙志》。[38]
第二、营护袁督师墓。
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其地旧称佘家馆,“文革”后易名东花市斜街),旧有袁督师墓,前树南海吴荣光所书“有明袁大将军之墓”碑。1868年曾经旅京粤人集资修葺,[39]1916年复集资重饰,[40]增设石供桌于墓前,并为植树。墓为园台馒头顶,砖砌灰抹。墓门前有槐树二株,墓后有马尾松一株,墓两旁植不松树两行。其中之小松树为张氏所献。侧有小墓一座,乃旧传窃督师尸归葬于此而令子孙世守之佘义士墓。为张氏捐资所立,碑铭乃其手撰,宋伯鲁所书。
第三、“修复”袁督师故居。
袁督师庙南里许有张氏捐资置地兴工,于1919年“修复”之袁督师故居(其地在今左安门内左安西里三号)。故居凡三楹。门悬督师手书“听雨”额,内祀督师神主、画像,并以康有为手书之《袁督师故居记》刻石嵌壁。张氏复筑室其旁,“插援激流,列畦莳卉”,[41]辟为张园,以为读书之所。其地“三面环水,时唱渔舟,虽僻静而不孤寂。春日潭水频积,萦绕左右。雉牒隐于后,法塔耸于前。清波漠漠,朝飞白鹭;高树隐隐,时躁昏鸦。”[42]虽处尘嚣之京华,乃独有田园兴味。以有督师故居,且小具园林之趣,故尤为“日下文士裙屐所萃”,[43]一时名流,若陈三立、杨圻、吴闿生等皆尝于此植松,缅怀督师英风。他如沈家畸、伦明、罗惇融、陈衍、夏仁虎等,尤为常客。顾颉刚、陈垣、余嘉锡、胡先绣、钱基博、瞿蜕园以及章士钊、叶恭绰、李根源、潘伯鹰、张伯驹等,皆尝先后来谒督师故居,多有题咏。齐白石尤爱赏其地,三十年代每避暑作画于此,尝颜其所居为“借山馆”,有感主人“平分风月”[44]之句传世。伯桢曾著《北京张园志》,[45]以志其盛。
经张氏之经营,北京东南城隅,遂有督师墓、庙、故居三故迹,错落其间,相去不远。其地又正毗邻督师当年星夜驰援,血战却敌之广渠门,尤令观者兴感。及张氏殁后,三逐渐衰落。1948年国民党驻车张园,园中花木横遭蹂躏,督师故居亦被破坏。
解放后,根据政府政策,旅京粤人组成以蔡廷锴为主委、叶恭绰等为常委之北京市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张次溪亦与其事,于蔡氏等推动会务多有襄助。[46]1952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为规划市政,决定将城内所有墓葬迁出城外。依规定,广东新、旧两义园中之坟墓皆在迁移之列,而袁督师庙及墓恰在其中。及获区政府建设科通知后,管委会商定一方面由张氏拟稿,以管委会名义上书彭真市长及北京市文化事业管理局,一方面由叶氏拟稿,邀集李济深、章士钊、柳亚子,联名上书毛主席,分头吁请保护并予崇饰。[47]
张氏所拟之稿,略谓:“本年五月二日,本市七区政府建设科通知我会所属广东新、旧两义园……迁移所埋坟墓。……我会为响应政府号召,已经通知各坟主进行迁移手续。惟查新、旧两义园中留有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墓、庙等遗迹,批恳政府派员调查,予以保护。倘能将此墓、庙加以修建,表扬英烈,借以激发人民爱国心情,以收同仇之效,想亦我市长所乐予倡导。兹将墓、庙所在地及督师事迹列下,以供参
考。”
各函发出,即引起党与政府之相当重视。毛主席于5月25日亲笔函复时氏:“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护。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48]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亦先于5月22日复函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已告有关方面对明代袁崇焕墓及祠庙,注意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彭市长复派专人赴叶、蔡诸氏家,面告“已交该管区
局办理。”
在此基础上,叶氏复召次溪等妥加筹议,以管委会名义拟具整修计划及图纸,由其寄呈彭市长,函谓:“各同人对市府盛意,均深感佩。兹同人拟有较具体的意见,特将图说计四纸奉上。依此计划,公家所费,当不甚多也。”
次溪等所拟计划之要点为:
袁督师庙:依原式翻建已破烂之庙顶;庙周新砌四尺高之砖围墙;庙门前土坡改建为石阶,庙内外加以粉饰。
袁督师墓:砖砌园冢;添建四尺高砖围墙;墓碑用砖砌衬边,加以保护;油饰墓堂内外。
此建议,为市府所采纳,拨款二千八百万元(按:为旧人民币,其比价相当今人民币二千八百元),委崇文区政府建设科施工。除墓碑衬边不做,围墙尺寸略为降低,墓周增植松树六十株,墓堂因尚为崇文区合作社借用,仓卒间无地迁移,暂不油饰,余依原计划进行,至十二月初竣工。12月5日,由崇文区人民政府民政科根据市民政局意见,会同施工单位崇文区人民政府建设科,将庙三间(原有匾、像、碑文及新建围墙、台子等建筑物全部)及其施工执照一件、墓两个(按:即督师墓及佘义士墓,包括小松树六十株与花围墙等建筑物全部。)、庙及墓两处所有门钥匙五份,移交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立有三方钤章之移交书在案。
至此,督师庙与墓崇饰一新,且较昔日尤为规整。并于次年清明隆重举行公祭仪式,李济深副委员长暨一时耆宿与在京两粤人士代表等百余人出席。观此次崇饰始末,足见党与政府重视保护历史文物之一贯政策,且经毛主席亲为关怀,尤堪纪念,然亦赖李济深、叶恭绰诸氏之积极呼吁,终以成之。至次溪等之襄赞,亦多与有力。故李济深撰《重修袁督师祠墓碑》(其文实叶氏代笔,见《遐庵谈艺录》)于详记崇饰始末之余,亦以次溪等筹策奔走之劳,附志于末。此碑后由叶恭绰书以刻石,嵌于袁督师墓堂。
1954年12月20日,管委会得“民政局根据教育局请求,征用广东旧义园土地,兴建中学,袁墓亦在其中”之通知。次溪当即报告叶氏,“请予指示”。经叶氏主持,决定:一方面由管委会派员与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及区人民孩府磋商;一方面由蔡廷锴代表管委会,由叶氏邀集李济深分函彭真市长,以袁“墓连同前面墓堂,占地无多,请特予保护,以资观感。”
因保护袁墓有案在先,今竟节外先枝,出此问题,故市府颇为重视,乃分工由薛子正副市长负责查处。经查,此实工作人员疏忽所造成之误会。缘市建筑事务管理局批准征用广东旧义园土地兴建中学时,早已明确“将园内袁墓划出,不得占用”。惟工作人员于绘制该通知之附图时,误将占地界线划错。具体执行人员无视《通知》正文,仅以附图为据,遂通知管委会欲占及袁墓。为此,市建管局特于1954年4月2日发出《关于广东义园用地的边界问题》之专门通知,主送市教育局,抄送薛副市长办公室、市房管局、崇文区人民政府,重申原建字10889号通知中“袁墓须予划出”之规定,且附以新图以更正该通知附图中之界线错误。复再次强调:“请你局转知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处理土地、迁移坟墓、建筑工程施工、运料期间,及往后学校建成后,均应注意切实保护袁墓及某祠堂建筑,勿使有所损坏。学校建筑用地,希尽量靠北。现有树木,希注意保护,对建筑确有妨碍的,亦希尽可能移植。”4月6日,薛副市长据以函复叶、蔡,并请转任潮(李济深)副委员长,附以建管局通知之抄件,解释与报告其中原委。函谓:“关于保护袁大将军墓园及其亭堂门楼的完整,在都市规划上向来重视此问题。”
一场误会,就此冰释。然因当年崇饰时墓堂未及施工,又值新建中学即将兴工,遂有吁请政府顺便崇饰墓堂、改建门楼之举。经次溪拟具之计划要点为:
1.迁建门楼
原广东旧义园门楼处于征用区,理应拆除,请就原料依原式迁建于袁墓前适当位置,以充袁墓门楼。
2.改建墓堂
原墓堂与袁墓不正对(按:其本为义园之建筑,原与袁墓无涉,后以居于袁墓前,遂充为袁墓之墓堂,故二者方向不协),请依原式以原料改建于正对之位置,并加油饰。
3.建成后,请指定单位接管
此计划经叶氏审定并寄薛副市长。附函略谓:“兹将该墓地前后情况,附以详图,希望先生提交主管部门酌予办理,以符政府保存先烈遗迹之意。至砖瓦木料,若就原有拆除下来已足敷用,在利用废物而不浪费条件下保存古迹,想亦市政所乐许。因乘该地正在施工时,盼以此具体方案交崇文区政府建设科,必能完成此任务也。”
经市府委崇文区政府建设科办理,至年末竣工。除调正墓堂方向外,余均依所议进行,墓门、墓堂油饰一新,门、堂皆悬叶氏书额,党廊柱悬康有书“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联,党内供奉袁督师遗像刻石,四壁嵌历次重修广东新、旧两义园碑记及李济深《重修袁督师祠墓碑》。原在袁督师故居之督师手书“听雨”及康有为《袁督师故宅记》等刻石,亦由张氏兄弟献出,嵌于壁间。至此,袁督师庙、墓之崇饰,分两次全部完成。旋移交崇文区文化局保管。1957年清明于此举行最后一次之公祭仪式。
至袁督师故居及张园(面积2.488亩,房屋14间),亦由次溪兄弟于1958年捐献于不久前成立之龙潭植物园(今龙潭湖公园之前身)。植物园表示愿尽速重建遭国民党驻军破坏之督师故居,以存胜迹。次溪亦深“幸得国家营护,长供国人游览,则有胜于私家之护惜者多矣”。[49]
次溪复就督师三故迹之始末著为《龙潭袁迹志》以志鸿雪。又以与崇饰督师祠墓有关之函牍、文件原件或复制件、抄件,汇订为《崇饰袁督师祠墓经过》,借存故实。
“文革”发生,督师墓被平毁,墓堂析为民居。庙亦被移作他用,故居更成为居民杂院。龙潭袁迹,面目全非,令人慨叹!今北京市及崇文区已将袁墓、袁庙列为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区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修复袁庙,业已奏功,重使游人得于龙潭湖公园之柳荫湖光间瞻谒故迹,缅怀督师。
三
督师生平事业之关乎北京者甚多。其自万历三十四年乡荐以迄四十七年中进士期间,尝数度赴京会试,惟居留皆暂。成进土后引见,候选期间则居留或相对为长。及天启二年,广宁失陷,朝野震惊,督师大计在京,乃条论边事,毅然请缨,遂启其戎马生涯。崇祯即位,再起督师,频诏就道,召对平台,授以节钺,夏镇东边。其在京逗留之日尤暂。崇祯二年,清军迂道肆扰,督师千里入卫,广渠门血战却敌,京师赖以为安。自身陷诏狱,以迄被磔西市,历时九月,此督师之又一次长期留居北京,且以被诬冤死而长留遗恨于世。用此,北京之督师故迹宜所多有,惜因督师被祸,遂湮而不彰。及乾隆间《明史》刊布,督师冤狱大白,则去督师之死已百余年,且经改朝换代,世移物易,其故迹益发迷离。张伯桢凭个人之力,营护督师在京故迹,“以为天下倡,”[51]其志可嘉,其功足纪。然核之史实,则其所谓督师遗迹者,又不无可疑。
先言督师故居。
督师数度居京之行迹,文献无征,址已难考。张伯桢忽发现于近三百年之后,谓“访得督师手书‘听雨’楼额”于其地,即指为督师故居,于发现经过及此额来历皆无交待,已不合事理。且据督师居京之时间及其具体情况推断,恐皆寄居全馆,不可能斥资构屋,作久居计。退而言之,即令置第,亦必不在左安门内。因其地僻远,交通不便,实非日须趋衙、谒朝之官员所宜卜居之地。
按之实际,刚张氏于左安门内甘露寺西上坡购地三亩,事在1918年,立契于该年9月9日,价大洋五百园整。原拟“营建生圹及宗祠,以为开族发祥,子孙永久占籍北京之计,”[52]及次年施工则又别筑所谓袁督师故居听雨楼。由是观之,则购地于先,旋于其地“访得”所谓故居,此无异为指定故居,宜其言之含混,无由语其原始。据张氏所言,其指为督师故居之理由,端在有督师手书“听雨”额。一似此额发现于所购之地者。然其处本耕地,则比额断无弃置地面之理。倘发现于地下,则其现场情况及埋于地下之因等又不可解。事实证明,此额确为张氏“发现”,惟其发现地不在北京,而在广东东莞。据调查,“东莞县文化馆保存着一块长三尺多、宽一尺多的楠木板匾额,中间由右而左横刻‘听雨’两个行书体大字,署袁崇焕名。据说是袁崇焕给附城温塘乡一家袁姓人建成新屋写的。”[53]此犹存于今之实物,且不论其果否出于督师亲笔,殆为张氏所称“发现”于北京张园者。盖欲故弄狡狯,致匿其来历而移置于北京。由之益见张氏所指督师故居之不实。
张次溪晚年著《莞乡烟水录》,谓:“袁督师在京故宅,道光间先渔石公璐撰《渔石纪闻》二卷,曾述及之。有云:‘袁督师元素驻师北京左安门内,有楼三楹,自题榜曰听雨’。……”按:《渔石纪闻》今无传本。估计为张氏世藏之先人手泽,今已难睹原文。既有道光间之记载,或可充左安门内袁督师故居为真之证,故需一辩。按:有记载与记载之确否,未可等同,而记载者去其事之远近,亦于该记载之价值殊有影响。此记载之出,去当时已二百年;所记数语中所谓“驻师北京左安门内”已非事实(见后),则其余之真实程度自然可疑,况所言直以“驻师左安门内”为前提,前提既伪,余则难论。故该记实不足充确据。
再言督师庙。
立庙祠奉先贤,其地在人自择。倘即先贤故迹兴建,固佳。即立于与先贤无直接关联之地,亦史所多有,本未可厚非。因之,故居容有真伪之辨,而祠庙本身则不存在类似问题。无如张次溪所为文字,类皆指其地与督师有直接关联。或谓其地为“袁崇焕曾经驻兵的地方”,[54]或谓其地“为袁督师驻在地(即今之司令部)”,[55]或谓为“督师当年点将台”,[56]因经反复申说,故颇有影响。《莞乡烟水录》谓此说乃出于《渔石纪闻》:“袁督师元素驻师北京左安门内,有楼三楹,自题榜曰‘听雨’,其北半里许东火挤,有荒台一丘,为誓师坛旧址。”
按:誓师率兵,当在其挺出严关,身为监军之后。考之行迹,自天启二年监军关外,以迄天启七年乞假归里期间,战守方殷,其不可能率军入京。及其解绥南归过京,更无率兵之理。逮再起督师,亦不可能率兵入京。排除以上可能,则督师率兵来京,惟有崇祯二年十月闻清军突入长城,而亲提一旅,兼程入卫,与清军战于北京城下之时。而此次从督师而来之关宁铁骑,实均列营于左安门外韦公寺前,[57]虽督师数请开城门容入城休整,皆不获允,即督师朝觐,亦皆缒城而入。是则曷得驻师于左安门内?况明时制度,京师驻军皆奉明旨,外镇之兵不得擅入,更不要说屯驻于京城之内。据此,则“督师驻师左安门内”之说,并由此派生之左安门内有听雨楼故居,今督师庙处为誓师坛、司令部等等,皆属传说失实,不足凭信。
继言督师墓。
督师墓之可资考证者,实以墓前吴荣光书墓碑为最早,署:道光十一年,即1831年。吴碑所据,当即原树于墓前之小碑一方,惜至民国间已剥蚀漫患不可辨识。[58]据吴碑所署年月,估计旅京粤人之公开祭奉督师亦必在此前不久。
至督师墓之所从来,惟有佚名《燕京杂记》曾载其事,谓:“明袁督师崇焕坟,在广渠门内岭南义庄,相传督师杀后,无敢收其尸者。其仆潮州人佘某藁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其右。迄今守庄者皆佘某子孙,十余代人卒无回岭南者。岭南冯渔山题义庄有云:‘丹心未必当时变,碧血应留此地坚’。”此传说即张伯桢建佘义士墓之所据,亦民国间称其地为佘家馆之所由起。按:该书著作时代无考,始由南清河王氏于光绪六年(1880年)载入《小方壶斋丛钞》,据其引冯敏昌(1747—1807年)之诗,知其最早当成于乾隆后期,或竟为嘉庆、道光间之作品。记载明确,固当无疑。然其间亦有数事,可为提出:
其一、此窃尸之佘义士,倘果如所传足以激励其后人世代为督师守墓,其后人亦恪遵祖训未之或违,何至并其祖之名亦皆迷失?此在重祖之旧时及世守祖训之后人实不可解。
其二、《燕京杂记》谓佘为潮州人,而张伯桢为之表墓又谓为“顺德马江人”,籍贯乡里不符。
其三、笔者1957年尝亲访最后一代守墓之已故佘汉青先生(时其任职于新建于墓旁之北京市第五十九中学)。[59]据其所谈督师死事及藁葬始末(渠云:乃本之上代所传),颇有不符史实者。如其谓督师乃被杀头,又谓下葬时镶以金头。倘其先世确如所传之亲为窃尸藁葬,则何贻其后世以此附会不实之说?
其四、“横扫四旧”时,他处墓仅平墓毁碑而已,袁墓则因向有“金头”之说,并遭挖掘。据目击者称,彼时“革命小将”为寻金头昼夜轮番“奋战”,至掘坑近三人深(估计约五米),非惟金头,即席头亦未见到。按:金头之说本属无稽之谈,宜其不获。然掘至如许深度,并骨殖亦皆未见,足证其地本非埋尸之所。虽当时之挖掘不同于科学发掘,然其意在寻金头,故可断其必极细微。未掘获于该处,或因积年既久,不断培土,而坟、墓偏离,其所挖之穴,早非督师葬身之墓。或则其地本无督师之墓,后世屡培之
坟,实乃象征。二者必居其一,是可称为督师遗骨之谜。
上举诸疑,虽不足否定督师墓之真实,然作为问题,亦颇可寻味,此外,李慈铭尝谓“督师墓在右安门外草桥,粤人旅葬处也,岁三月祭之”。按:当同治、光绪年间,粤人旅葬处,不在草桥。斯时旅京粤人岁祀督师于广东旧义园袁墓之前,决无可疑。而草桥乃当时都人游宴胜地,文人墨士诗咏连篇,乃独无道其事者,张次溪据以断此为误记,[60]当属确论。因附及之。
兹所论,旨在考实求信,非欲否定龙潭袁迹。曾得毛主席及李济深诸公关切,且已列为文保对象之袁庙、袁墓,理宜修复,以为纪念督师之胜迹。即袁督师故居,亦亟应恢复,犹如陕西黄帝陵、南岳舜庙、山海关孟姜女庙,虽并其人之有无亦属两可,然世代传说,足资凭吊,未尝不可为文物;八达岭长城,灌县都江堰,兴安灵渫陡门,虽非秦皇、李冰、史禄所制,然作为象征,亦堪供后世由此及彼而缅怀。准此而言,则考实求信为一事,古迹本身之存在价值又为一事,不当混淆。因为声明,免滋误会。
四
东莞张伯桢父子,自民元以来积极表彰袁督师,致力最勤,贡献殊多。究其出发点,首为宣扬督师爱国精神,以抒抱负、厉世俗。此于《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表现最为明显。当其于1935年初载于《正风半月刊》时,副标题作:《当日之满洲国比今日之满洲国何如?》、《誓收复东北之模范人物》;肩题作:《东北问题之殷鉴》。《引言》更谓:
“今欲恢复东北疆土,非取法崇焕不可。”同年末,张氏以该传刻入《沧海丛书》第四辑,卷首载《刘袁督师、张文烈二传成自题诗,谓:“寄迹都门感喟深,聊耽著述付袁吟。……辽沈故墟空想像(原注:明戮袁督师而明遂亡,满洲遂得入主中夏。今辽又成故墟矣。),增城伟业叹销沈(原注:张文烈公誓死不附清,胡殁于增城……),有功世也教吾何敢,为表先贤报国心。”1932年,张氏补刻《袁督师遗集·跋》称:“今日国情与明暗合。安得督师复生于今日,同赴国难,以复我失地耶?观辽东往事,可悚然矣。”这些发于“九·一八”后之言,恰足说明“其微意所在,尤足起衰振懦,为当世之药名”。[61]
1915年5月9日,为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之“国耻纪念日”。张氏恰于是日草成《袁崇焕应配祀关岳意见书》,乃附识曰:“意见书草成,适为日本最后通牒之纪念日。千秋万世,当不忘此日也。安得崇焕再生于今日,为中国吐气耶?特附记之,以志哀痛。”1916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为策应其一手泡制的蒙古巴布扎布匪帮妄图建立满蒙帝国的军事行动而挑起奉天(今沈阳)“郑家屯事件。”日军“威压奉军”,制造军事冲突。当时日方调军增兵,箭拔弩张,我国舆论哗然,同仇敌忾。明此背景,则袁庙门联“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何处更得先生”之所指,自不言而喻。康氏《袁督师庙记》所谓“令人爱中国、思将才”之含义,亦昭然若揭。
伯桢尝自铭其生圹曰:“嗟我身世,有如落花,纵化作泥,犹护中华。”[62]爱国之忱,情见乎辞。1937年“七·七”事变后,伯桢居于沦陷之北平,慨“表忠无计”,谓:“配祀曾挥意见书,当时众口互訾予;表扬更草三忠传,我慕程生(按:指为袁督师讼冤程本直)愧不如。”[63]从知其积极表彰袁督师,实有慨于国难方殷,“欲以扶衰立懦”,[64]迥非“发思古之幽情”。言其表彰袁督师之积极影响,此乃最主要者。
其独积极予表彰袁督师,固以督师生平事业在于“东事”,此与张氏当时之东北现实颇相关,易取为殷鉴,然亦另有原因,即以督师为其邑先贤。郡邑为国之一隅,合诸隅方有国之可言。古人于此局部与总体之关系早具认识,俗谓“爱国当自爱家乡始”,即其表现。是以乡贤传、郡邑志之编著,郡邑丛书之刊刻,蔚为传统。当“洋”风日炽,或且数典忘祖之时,张氏立志表彰乡贤,其精神亦属可称。然为“乡”字所囿,亦难免偏狭,即如督师祖居固在广东东莞,而其通籍实在广西藤县,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所载,即为明证。督师生前虽家广西藤县,然与广东东莞故里亦时有往来。言督师身后,则吁请从祀乡贤实发于广东巡抚,而求其后人,则见于广西平南。督师之为粤人、为桂人,固宜明确,然谓非此即彼,必须排它,甚则为强调属我,竟泯他地而不书,皆非公允。昔人曰:“督师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一代之英雄豪杰,岂一乡一邑之可得而私者?”[65]旨哉斯言!张氏处理督师籍贯问题,执乡贤之成见,必欲为东莞独
有,实不足为训。
论者尝谓;“甲、乙之际,有附合项城者,请以祀关岳之典祀袁崇焕。项城亦自谓源于东莞。其实崇焕无子,以从弟文炳子为嗣。乾隆四十八年录崇焕后裔于原籍,得五世孙炳,以佐杂选补,是逃居河南之说为子虚,且崇焕戮只一身、未及拏也。”[66]考所谓焕弟“逃居河南之说”,实倡于张氏。其《袁督师遗集·跋》谓:“忆尝闻诸吾邑父老曰:督师罹难后,一门殉节,嗣遂斩。其弟崇煜以避难故,逃河南,流寓于豫东。至今子孙蕃衍,为邦家光,缙绅先生类能言之,袁嗣虽斩于粤,犹绵于豫,可见英雄挺生,自有真(按:疑为‘其来有自’之讹)也。”由之复有“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67]之附会。虽其曾指出闻于东莞袁厚常,然究铺扬推阐,则张氏实不能辞其责。时人讥为“欲附合项城”,“媚袁”良非无故。按:以诗文干公卿,应帝王,本旧时之常。谓张氏借此为敲门之砖,亦未为苛论。观其以所刊《袁督师遗集》、《张文烈遗集》进呈大总统“恭候批示”,[68]亦足窥见其旨。至于伪造明板《袁氏世系》,则尤贻饥于世。[69]同时,封建时代附骥以求不朽者,所在多有。为此,不学无术之富商买办,不惜重资刊刻丛书。所谓“欲求不朽,莫若刊书”,且被奉为劝善名论。无可否认,张氏之表彰袁督师,
恐亦不无此意存在。故其既刊督师遗像于《督师遗集》之首,复刊篁溪三十八岁肖像于《督师遗集附录》之端;既立庙崇奉督师,复以其意钓、悼亡之诗咏图绘刻石嵌于庙壁。致不明真相者谓图绘张氏亡妻为督师夫人,尤属笑话。自今日观之,固不伦不类,然在昔时,乃属风雅。凡此,皆其历史局限,虽不当依今日标准,求全责备,然需指出,以符事实。
综上所论,则张氏表彰督师之出发点,虽较复杂,然其第一位者,究为发扬爱国精神,此业由其社会效果所证实。至其它种种,究属瑕不掩瑜,不当以之否定其第一位之动机,及由此而发挥之积极作用。
张氏于表彰袁督师过程中,既于袁督师史料、文物之辑集、整理、编纂建树颇著、亦于督师史实之考索,多有发明,其在袁督师研究史上之地位,彰彰在人耳目。此固不容抹杀,然其间亦存在明显之缺陷,尤宜指出。
首先,其用以指导研究者乃唯心史观,故所论多有偏颇。举其要者如论督师之历史地位,犹沿《明史》所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及梁启超推督师为“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降替者”之论,谓“崇焕有关一代之兴亡”,“明戮袁督师而明遂亡,满洲遂得入主中夏”。脱离社会经济与阶级状况之实际,独以英雄人物决定一切,宜其难获正确之结论。就当时论,袁宏焕个人实不足挽救濒临火亡之明帝国,即袁健在,明亦必亡。审时度势,则其所谓“五年复辽”决难兑现。作为杰出之英雄人物,断难脱离历史条件发挥作用。囿于“英雄决定历史”,故于督师难免神化,必谓“五年复辽”为可得实现之成算,必谓在当时条件下惟有杀毛文龙为正确,亦即不允许督师有不足、有失误,必令其一贯正确,自然有悖历史实际。
其次,出于功利之考虑,故弄狡狯,以致谬误流传,徒滋纷乱。如前举所谓焕弟逃居河南,北京左安门内有听雨楼,以及实为翻刻粤雅堂本独讳而不宣,皆其明例。科学所求者为是非,本不以功利为指归。舍此原则而杂以功利之考虑自必贻害,张氏实为殷鉴。
复次,因粗疏、失考或轻下结论而致之失误,在张氏亦所多有,此在其所搜得之督师文物方面,尤其明显。就科学研究言,固应力求正确,然错误亦所难免,不当苛责,故不深论。
张氏表彰袁督师之成绩与问题互见,就总体言,究属用心良苦,功不可没。其精神、其成绩,有待发扬,其问题、其不足,则有待澄清与克服,张氏生于旧社会,身处旧官场,独能以表彰袁督师之爱国精神为职志,理宜为继起研究督师者所肯定,特别是其“家本约素,乃罄其俸糈所入”,悉力营护督师在京故迹,“无毫发顾吝”,[70]而父子两世,未尝在京置产,始终赁居,则允堪赞许。
“篁溪桥梓彰乡献,胜迹千春蕴古香。”[71]其间之苦心孤诣,功过得失,实堪论列。际兹督师诞生四百周年学术讨论盛会,不揣翦陋,述之如此,姑充袁督师研究史之一章,谨就质于同好。
注:
[1]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增订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初载《新民丛报》二卷四期至三卷二期,1903—1904年。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3]李白凤:《水围坊记·序》。载《东莞乡土丛书》,1965年油印本。
[4]孟森:《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序》。1941年拜袁堂排印本。
[5]张伯桢:《篁溪年谱》。稿本。
[6]《沧海丛书》凡刊五辑。《中国丛书综录》仅著录一至二辑,盖未睹其第三至第五辑。
[7]韩寿萱:《纪念张篁溪先生》。载北平历史博物馆编:《张篁溪先生捐赠物品清册》卷首。
[8]张次溪:《四十年录》,稿本;《张仲锐自传》,稿本。
[9]姜纬堂:《张次溪与北京史研究》。载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年9月。
[10]张伯桢:《袁督师遗集·跋》,署1908年,载《沧海丛书》第一辑。
[11]罗桑彭错:《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闻录》。载《正月半月刊》一卷十二期,1935年6月。
[12]同[10]。
[13]伍崇曜谓此书“亦随手掇拾而刻成者”,是。以其载嘉庆间请以督师从祀乡贤之《呈祠》、《奏稿》,且为伍氏重刻之包据,可断其当为嘉、道间物。伍氏说见其重刻该书跋,载《岭南丛书》。
[14]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版。
[15]沈云龙辑,1973年台北文海出版社版。
[16]为其所辑印《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之卷一。
[17]《莞乡烟水录·袁督师遗稿》:“《东莞诗录》云:‘所遗诗文,奏疏数十卷,久存东莞。数年前,其嗣人圣恩自粤西来取去,……,是为督师遗稿流落广西之证。……颜冰庵丈往见《三管英灵集》载督师遗诗多首。余访此书,迄未得它。”《莞乡烟水录》为张氏晚年所著关于东莞乡土史迹之笔记,收入所编《东莞乡土丛书》。
[又17]《北京岭南文物志》记此联作:“子美诗开史世界,伯阳集见道精神。”误。此据北京龙潭湖公园所存当年袁督师故居木联。该木联“文革”中不幸沦为该园渔船上之垫板(反面使用)。近为该园有关同志发现,始再作文物珍藏。参见姜钝夫:《袁崇焕书联失而复得》,《北京晚报》1984年9月23日。
[18]《莞乡烟水录·袁督师遗物记》。章行严,即章士钊,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汪公岩,即汪鸾翔,时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检罗氏已刊著作无此跋。此据张次溪辑《崇饰袁督师祠墓经过》后粘附无题无署之剪报。其来源俟考。
[20]于之夫:《“赖文光题袁崇焕藏砚”是假的》。载《光明日报》1956年3月15日《史学》第78号。
[21]伦明:《督辽饯别诗图·跋》。
[22]《明蓟江督师袁崇焕传·引言》。
[23]连载于《正风半月刊》一卷七期至十八期,1935年4月—9月。另有《附录》,载该刊一卷十九期,1935年10月。又有《补遗》,载于该刊二卷一期,1936年1月。后复将三者厘为四卷,于同年刊于北京,为《沧海丛书》第四辑之—。刊本与《正风》原发表者,内容基本相同。惟标题等多有删落,复增加序跋数篇。
[24]连载于《正风半月刊》一卷十二期,1935年6月;二卷三至四期,1936年3~4月;三卷五至六期,1936年10~11月。
[25]陈三立评语。《正风半月刊》一卷十八期,1935年9月。又见《沧海丛书》本,陈氏《序》。
[26]孟子微:《袁督师遗稿二三事》。载《艺林丛录》第一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1年9月初版。
[27]收入《京津风土丛书》。1938年10月双肇楼校印。
[28]孟森:《袁督师后裔考·序》。
[29]收入《燕都风土丛书》。1938年6月燕归来簃校印。
[30]孟森:《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序》。
[31]《呈文》,载《袁督师配祀关岳议案》卷一。
[32]《意见书》,载《袁督师配祀关岳议案》卷首。
[33]梁士诒:《覆张篁溪书》。载《袁督师配祀关岳议案》卷三。
[34]收入《沧海丛书》第二辑。1915年初刊,1932年续刻。
[35] 《袁督师配祀关岳议案附识》。
[36]此联署“壬申夏月”。“壬申”为崇祯五年,已在督师身后,故可断为伪。
[37]王树楠:《袁督师庙记》。
[38]1926年刊于北京。
[39]邓华熙:《重修广东旧义园记》。载叶恭绰、张次溪编:《北京岭南文物志》。1954年印。
[40]王尧忠:《重修广东义园碑记》。载《北京岭南文物志》。
[41]靳志:《袁督师故宅记》。载《龙潭袁迹志》。
[42]张次溪:《龙潭袁迹志·自序》。
[43]同[41]。
[44]张次溪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
[45]1926年刊于北京。
[46]蔡廷锴:《北京岭南文物志·序》。
[47]张次溪:《崇饰袁督师祠墓经过》。以下关于崇饰始末,凡不另注出者,皆据该书。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49]《龙潭袁迹志·自序》。_.
[50]尚未正式公布,此据其《修改草案》。
[51]《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闻录》。
[52]《篁溪年谱》,稿本。
[53]卢围:《袁崇焕籍贯查证》。栽《广西历史人物传》第一辑,广西政协地方史志研究组1981年编印。
[54]张四都:《佘家馆》。载《北京日报》1956年6月9日。涵江:《龙潭的袁督师庙》,载《北京街道的故事》,北京出版社1958年初版。按:张四都为张次溪所用笔名,涵江之涵,即张次溪。
[55]张次溪:《北京市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上市长书》。见《崇饰袁督师祠墓经过》,稿本。
[56]张次溪:《莞乡烟水录·袁督师在京遗迹》。
[57]周文郁:《边事小记》卷一。《玄览党丛书·续集》本。按:周随督师入卫北京,故其所记最为权威。
[58]《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闻录》。
[59]姜钝夫:《袁崇焕墓和祠堂》。载《旅行家》。1958年第2期。
[60]《莞乡烟水录·李慈铭记袁督师葬地之误》。李说见《杏花香雪斋诗·已集》。
[61]吴闿生:《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序》。
[62]《篁溪年谱》,稿本。
[63]《丁丑杂咏·吊袁督师墓》。收入《沧海丛书》第五辑。
[64]钱基博:《袁督师故宅记》。载《龙潭袁迹志》。
[65]何寿谦:《袁督师事略书后》。载《(同治)藤县志》卷。
[66]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载《骨董琐记全编》,三联书店1955年版。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载《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7]《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闻录》。
[68]载其所刻《袁督师遗集·附录》之末。
[69]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薄注》卷二。
[70]王树楠:《张篁溪生塘志铭》。载《篁溪年谱》。
[71]卢慎之:《为次溪题龙潭袁迹志》。
更多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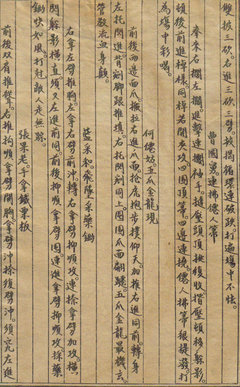
转载 张氏短打拳谱完整版 张氏短打拳第二路
原文地址:张氏短打拳谱(完整版)作者:少林德勇武术秘籍校勘记壬午岁末,予友李东来,于京都购得古传武术秘籍旧钞本,携来示予,以求校勘。予自少年即喜武术,年至弱冠而从军塞外,尚武禀赋难改,遂欣然应之。张氏短打拳,亦称绵张拳,为宇内名拳,渊源古老,
『华夏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与源流考。』 华夏幸福迁回石家庄
华夏张氏图腾华夏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与源流考【请全球张氏宗亲提供资料线索,以便完善。】陕西省通派同州派我張氏一脉一世祖玉端公,唐代同州刺史沛公之后,生于陕西同州府(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华阴派流公居之华州华阴县钦若公之

张馨之全裸宣传环保有何企图? 张馨之
近日,一场大型公益计划“人·沙·敦煌”的沙裸艺术行动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此次活动,诸多明星和演员成为志愿者加入其中。其中,名模张馨之大尺度挑战自我进行裸体彩绘写真的拍摄,身体力行呼吁环保。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全身涂满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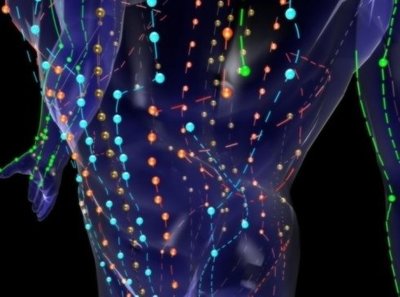
转载 学医心得张涵之我见 转载 教研员培训心得
原文地址:学医心得张涵之我见作者:上善若水学医心得张涵之我见http://pyzhanghan1.blog.163.com2009-08-1721:40:06|分类:中医类|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学医心得张涵我在随恩师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心得和体会,因为资质愚钝,当然属于一些

杨氏之子导学案 杨氏之子朗读配乐音乐
课题:杨氏之子 课时:1-2课时 主备人:罗秋兰级别:五年级语文组 使用日期:学习目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