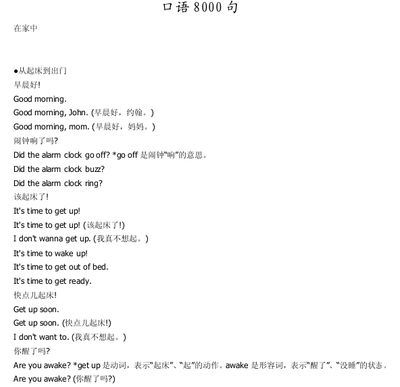早上醒来,照例翻阅微博和朋友圈,发现很多人都在讨论蔡国强在上海为其个展做的“白日焰火”表演,褒贬不一。作为局外人,第一眼看到焰火的照片,还是会情不自禁为之惊叹。实际上,我一直很惊叹他的想象力与艺术手法——他把天空、河流甚至城市作为画布,烟花作为水彩,用如此不可掌控的方法在虚无的空间和准瞬即逝的时间里完整地勾勒出他心中所要传达的画面。在我的印象里,蔡国强在国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甚于国内,或者说,国内公众接触到他的作品,是隐藏于所有国家公共事件中的,而他似乎也不太计较这些个人标签。08年奥运会,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目和整齐划一的团体操,都已经被人们渐渐淡忘了,而那一串从永定门到鸟巢的脚印,却一直在我的记忆上空萦绕。只是蔡国强这个名字,并没有像他所有的作品那样耀眼。我看到网上一个文艺青年朋友发了焰火照片,另一朋友留言说,哎呀,蔡明亮来了,怎么不叫我。朋友怒而回复,是蔡国强,我还蔡国庆呢。这当然是笑话,但也足见蔡国强并不是一位活跃于国内公众视野的艺术家。
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实际上都集中于指责蔡国强的艺术手法污染环境,和对这样的焰火是否算艺术的质疑。于是我看到更多长篇累牍循循善诱解读蔡国强作品的文章,当然也有高贵冷艳觉得公众不懂艺术就懒得与之较真的态度。很多人的逻辑是,蔡国强在国外主流艺术圈受到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同样性质的作品到了国内,受到的待遇却截然相反,如果不是国外顶级艺术家的审美问题,那只能是国内公众的欣赏能力问题了。
事实上,我对国内公众的反应一点也不惊讶。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公众的质疑也是艺术作品的延续。
初到纽约,我曾对这个所谓“世界之都”大大小小的事情嗤之以鼻,我们见过太多雄伟的建筑,了解太多可供追溯的恢弘历史,这个年轻的现代城市乍一看并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否源于自己的不自信,还是内心真的已经逐渐丧失了赞美与惊叹的能力。而纽约让我真正感觉到它的艺术魅力,并不是MOMA里每日络绎不绝受人瞻仰价值连城的名画,也不是大都会博物馆一整天也看不完的各种收藏品,反倒是那些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猝不及防的“偶遇”。
纽约地铁车站里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就会像桑拿房一样热。上周在纽约最热最拥挤的“34街车站”站台,被一个美国行为艺术团体改造成一个临时桑拿房,团体成员穿着浴袍围着浴巾在站台里晃悠,座椅边架起烤炉并不断加水,甚至搭了几张临时的床当众进行按摩。这个在纽约成立了十几年的团体叫ImprovEverywhere。“improv”意为即兴表演,据说这个团体的主旨就是随处表演随处搞笑。按照创始人查理•陶德(CharlieTodd)的说法,其目的是“制造一些令人惊讶的时刻,从而使行动者在自己的余生里对其曾经做过的举动津津乐道”。此前我对他们印象最深的创意作品是“静止的中央车站”,他们召集了两百人,在中央车站里装作普通行人,然后在一个约定好的时刻,所有人突然静止,就仿佛时间凝固了一样。一分钟过去,大家继续此前活动,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四散离开。视频记录了这场活动发生的一切,和在站台蒸桑拿的行为一样,那些不知情的路人最后也不自觉地参与了其中,他们的惊讶、疑惑、欢笑,似乎也成为了整个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那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相比,这个所谓搞笑艺术团体带给我的震撼与冲击也许更大一些。
纽约每天都会上演各种各样艺术活动,有高大上的,也有像Improv Everywhere这样并不热切标榜自己是艺术的艺术家。在这个自由散漫的城市,艺术的边界也变得格外模糊。纽约同样也有受到指责的行为艺术,有人在地铁里往自己身上泼油漆,便有人指责他破坏公共环境。有人用皮草作为绘画材料,自然也有动物保护协会的人站出来抗议。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造物,可是两者都支不起城墙。你喜欢一个城,不在于它有七种或七十种奇景,只在于它对你的问题所提示的答案。”我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形容艺术。
我并不相信每个亲眼目睹蔡国强作品的上海人都对他创造的奇妙场景无动于衷,也不觉得大家的愤怒和不解来源于审美上的不够“喜庆”。有时候,艺术的感知更多的是和个体的经验紧密相连。很不幸,在一个一年大部分时间心情都会被雾霾左右的国家,以烟雾为基础材料的艺术作品,带来的抵触情绪远远超过视觉感官的享受也就不足为奇了。置身事外的人看到的是图片,是影像,是视觉享受,但更多的上海市民,可能只是透过高楼缝隙看到烟花过后城市上空久久消散不去的黑色烟雾,和经过黄浦江边时闻到空气里弥漫的粉尘味道。
我理解长期处于雾霾生活中人的无奈与抑郁,就好像你无法要求一个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在第一眼就能马上去欣赏一个热气腾腾的面包如何充满创意。而我觉得更多时候需要警惕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心和感知力不受“雾霾”的蒙蔽——那种由愤怒、冷漠、傲慢组成的挥之不去的雾霾。
上个月美国独立日,我和一群朋友无所事事,听说梅西百货每年都会在国庆日放烟花,于是决定凑凑热闹。对于所有中国人而言,烟花实在是太稀松平常的事了,我们对看烟花并无太多热情,纯粹只是为了体验别人的节日。烟花秀定于九点半,而六点钟在河边集合的时候,布鲁克林大桥以及附近所有的路全部被警察封了起来,人行道被人流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过于低估纽约人凑热闹的疯狂程度了。整整半个小时,所有人坐在马路牙子边,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仰望天空,看完了整场烟花秀。人们欢呼,鼓掌,对天幕上出现的图案尽情表达自己的惊讶与欣喜。结束的时刻,我听到身后楼顶有人高喊:“Ilove newyork!I love USA!”我和站在一旁的中国朋友面面相觑,第一反应是觉得可笑,美国人也太容易被感动和少见多怪了吧。不就是看个烟花嘛,至于激动成这样么?
我承认在他们欢呼的一刹那,内心也自然而然地升出某种优越感。从小到大,我们见过无数比之更盛大更绚丽更神奇的烟花,也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热血澎湃过。我已经回忆不起自己童年时代看到烟花的欢喜雀跃,也不知何时才能重温那样的感觉。可是,反观自己近似麻木的平静,在那一夜的人潮中,我突然有些羡慕这些”单纯“得近似幼稚的“外国人”,那些站在我身边比我年长却对烟花依旧怀着赤子之心的成年人。
蔡国强在一次采访中说:“艺术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保留我童年梦想的状态。我们在大千世界,慢慢成熟,面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慢慢现实起来,但是艺术能够使我保留住童年对世界的憧憬,想当艺术家的梦想,当艺术家的热情和小小的野心。最重要的在于保留小时候想当艺术家的梦。”于是,他在上海滩灰蒙蒙的天空下很努力造了这样的白日梦,又缤纷又伤感的梦。有人说,艺术就是同床异梦。我觉得,有时候梦到什么不重要,最恐怖的事并非噩梦,而是一个人再也没有能力做梦了。
文章刊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