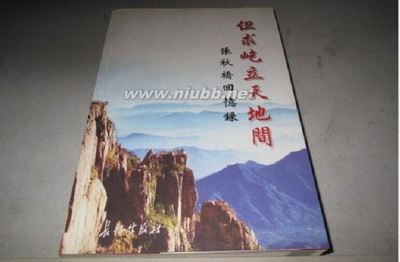上海曾经发生两次炮打张春桥。我只亲历了第二次“炮打”,虽事件爆发来去倏忽,但前奏、尾声却不短。相关发生的事或大或小,多为亲历,或许其中有某种逻辑关系。时隔四十余年,看到一些回忆文章,觉得有些重要史料未曾道及,联想到人生命运也因政治运动而曲折坎坷,似乎有所体悟。于是努力搜寻记忆,小大由之地写下这篇亲历记。连带所及,本着存史(有些渺小到其实是个人的某些经历)的原则未加割舍。
前奏
1966年12月,红卫兵运动已经完成打倒本单位党委的使命,大学生开始走上社会,参加重要单位的斗批改运动,或接受其他相关任务。我班有一批同学自愿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运动。除了该厂与文学相关,接触明星(尽管他们正晦气当头)大概也是潜在原因。还有几位同学到虹口的鲁迅纪念馆参加运动,后来顾姓同学被馆内某女士相中,成了乘龙快婿,成就一段佳话。
那时候王洪文初起,希望复旦大学中文系派人去为他编《纺织战报》,帮他造势。他虽已号称工总司司令,实际上能驱使的还只是以纺织系统为主干的力量,耿金章那拨人就不买账,工人队伍有分裂迹象。同学们不愿介入社会上的派性斗争,而且毛泽东已经发出大团结的号召,所以无人肯去。所幸无人肯去,否则若干年后将会又多几名政治殉葬品。
我和樊堂荣被分配去参加接待遭受印尼当局迫害而回国的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驻上海市复兴西路62号。参加接待的成员来自上海32个造反派联合组织,奇怪的是,工总司派来了一名重量级人物——常委蒋周法。其人身材不高,剃光头,阴森冷漠,令人莫测高深。他对接待工作漫不经心,不担任具体工作,行踪诡秘,身边常有不三不四的人相随。他也从不与我们交谈,也不去五原路里弄食堂吃饭,手边常开着成听的高级饼干,并且从不与大家分享。
后来才知道,蒋周法另有重任,他来复兴西路是为了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以便参与指挥康平路武斗!我们的驻地对面安福路口是上海市工人造反第三司令部,不远处就是上海市委所在的心脏地区康平路。在康平路正聚集着工人赤卫队和工总司两派大量人马,为保卫和打倒上海市委,斗争趋于白热化。
我只管接待印尼华侨的工作,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康平路。但是有一天我们的驻地忽然来了三名不速之客:王洪文、王秀珍和一个大块头保镖。他们与蒋周法低声嘀咕几句后,王洪文就一直站在我的宿舍隔壁房间的电话机旁,声色不露,不时打个电话。约半小时后就离开了。当晚就传来武斗消息,工总司粉碎了工人赤卫队,很多赤卫队员满脸是血,缴获的袖章堆成了山。我可算从侧面目击了康平路事件冰山一角。
“一月革命”在我身边发生了。我却浑然不觉。
张春桥真不可小觑。旧上海市委大多数人都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他却一贯正确,且能左右两派,呼风唤雨,闹得上海天翻地覆。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下旬上海各项接待准备工作就绪。我与上海体育学院的林金钟,还有一位上海机械学院印尼华侨陈老师等三人奉命到北京向中侨委领导汇报上海的接待工作,请示下一步如何迎接四十一名青少年英雄来沪活动。当时廖承志、方方已自身难保,靠边站了,国务院外办领导李一氓出面接待。一氓同志详细听取了上海工作,询问了很多细节,最后指示,可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求批准上海的活动计划。于是由我执笔写成六百字(这是给总理打报告的要求)的报告,上呈周总理。次日总理便有批复,同意成行,希望上海隆重、热烈、破格接待。我们真是说不出的兴奋。一月廿九日铁道部特批专列,我们陪同四十一名小英雄兴冲冲回到上海。
谁知道就在一月二十九日返回上海的时候,惊闻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了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委员会)炮打张春桥事件。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反对炮打,并要追查后台。满街宣传车不断宣读着中央特急电报,连南下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也参加了呐喊。红革会惨遭整肃。原来上海的造反派早就对张春桥生疑,按造反派的敏感和性格,就导致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造反派不成熟之处是,他们还不能从全国的大局分析张春桥的站队,打狗不知其主。难怪乎栽了。须知生死定夺在人不在理。若用得着,流氓、叛徒照用不误;若已用过,随时会被抛弃;若有忤逆,再大的功臣也活不成的。
我没有参加这次炮打张春桥,而是很认真地坚持按计划圆满完成了接待印尼爱国华侨青少年的任务。
回到复旦大学。一进校门就觉得气氛寒气侵人,十分压抑。军队武装接管了复旦,解救了被红卫兵关押的徐景贤(此人曾关在学生宿舍的六号楼333寝室)。
高涨的革命热情遭到劈头盖脸泼来的冰水,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是非常难受的。春节在即,大家不约而同决定回家过节。于是很快人走楼空,校园一片死寂。
阴谋家心肠是最歹毒的。张春桥躲过一劫,却不肯轻饶炮打他的红卫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便是对复旦大学红革会头头如赵基会等人的追查批斗,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郭仁杰甚至被迫害跳楼自杀。复旦大学在上海媒体上已经沦为二流,效忠张春桥的同济大学东方红战斗队的头头陈敢峰(复旦人为其看风投机,蔑称他“陈看风”)成了新时期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同济大学风头盖过了复旦大学。
压是压不服的。反张受压的红卫兵誓把张春桥拉下马!
一、“中央文革”与“中央军委”矛盾的公开化
张春桥错呼口号
张春桥文革中地位飙升,1968年初身兼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诸要职,可谓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可是,政治野心是没有止境的。面对毛泽东设定的接班人林彪,江青张春桥视之为上升通道中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中央文革派与中央军委派之间一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1967年初造反派发动“一月革命”,在上海夺权之后,张春桥即剑指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反军祸心毕露。但是与中央军委的对立情绪的公开暴露则是一次大型集会。
1968年3月22日,老将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与江青之流的斗争中被毛、林当作牺牲品抛出,文革派自然大喜过望,上海市迅即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讨大会。我们也列队参加了大会,亲眼目睹张春桥赤膊上阵,与会发表讲话。吊诡的是,一向阴沉不乱的张春桥在结束讲话,高呼“打倒余立金”的时候,却喊出了“打倒吴法宪”的口号!吴法宪时为中央军委办事处五人小组成员,是林彪麾下大将。张春桥的错喊口号实在是喊出了他的心声,是密室里的阴谋下意识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为何张春桥一反常态,乱了方寸?原来当时确有某种至今难解的迹象:中央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两次解决杨、余、傅的会议,张春桥不得与闻,无缘参加。上海方面不得不派人专门了解有关动态。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召开“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后,上海慌忙召开不下十万人规模的同题大会表明紧跟的政治立场,明打杨、余、傅,心恨中央军委办事组,这才有张春桥赤膊上阵错呼口号的故事。
揪住了狐狸的尾巴,好戏便在后头。
“红旗”飞舞,穷追不舍
张春桥的反军口号造成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军界立即有了强烈反应。
当时在社会上能够表达派系态度的军队系统只有军事院校。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两派斗争就很激烈。两派对峙,剑拔弩张,时有武斗。某派在校门口的海报中出示的武斗中致伤的照片,触目惊心:女学员的臀部及大腿被对方打得一片紫黑。不久前我在长海医院切除扁桃腺,医护人员和病员出入病房,都要经过武斗工事,钻进钻出。
其中占上风的一派称“红纵”(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是参加“一月革命”夺权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之一。
另一派称“红旗”(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兵团),“一月革命”后处于下风地位,曾直面抗议张春桥支持“揪出上海的陈再道”的反军行为。据传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是其中成员。
二医大信息灵敏,因为从来军事院校多高干子女,二医大有各种渠道通往北京是非常自然的。据云周恩来有一名养女在该校。周恩来之所以能及时了解上海的斗争动态,与之不无关系。
在张春桥错呼口号后,“红旗”如获至宝,立即扬起战旗,声讨张春桥的倒行逆施。二医大校园上空的高音喇叭连续播出张春桥错呼口号的录音,犹如法庭上出示罪证,又像绑着张春桥游街示众。“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之类的标语铺天盖地。
斗争的发展耐人寻味。人们很快发现“红旗”后面的指挥者是远在北京的中央军委!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得知,“红旗”的标语口号从内容到字幅的大小,到张贴的区域,甚至保留天数,都受命于中央军委。比如,起初,标语只张贴在校内;某日,张贴到虹口;再过几天张贴到市中心,竟然都是来自北京的指令。
更引人遐想的是,在那个疑云重重的日子里,江苏、浙江两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道里,新华总社的电讯稿中,删去了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只称其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一现象煞费猜详。
从此,上海蓄积着的反张力量都摩拳擦掌,密切注意着“红旗”的动向,酝酿着与张春桥的决战。
二、复旦园,军宣队态度暧昧
来自空四军的军宣队进驻复旦大学,原来是为了控制复旦大学的运动走向,使之行不逾矩。邪恶的淫威岂能强暴大学生高贵的自由精神!曾经参加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的复旦人被压制了一年多,反张情绪高涨,早已近乎着火点。只待时机一到,瞬时便可怒发。来自二医大的反张动态,在复旦自然备受关注。两校的互相走动空前增加。人们似乎听到了反对张春桥的隐隐雷声。
我与徐枫等同学贴出署名“虎山行”的大幅标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事后我们看到,这幅标语的照片印上了上海市革委会的内参,为此颇捏了一把汗。
人们非常急切地要知道复旦大学军宣队的态度,不断向军宣队询问情况。可是军宣队态度暧昧。比如,有人问道:“张春桥是不是还是南京军区政委?”答非所问的是:“张春桥仍然是中央文革副组长。”
军宣队对二医大和复旦大学出现的反对张春桥的活动持放任态度。在“4·12”反张运动爆发前和当天,军宣队几乎不见踪影。
军方的微妙态度暗示着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斗争,背景非比寻常。
三、“4·12”二次炮打张春桥
事实上,与二医大、复旦大学行动遥相呼应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长朱锡琪等人早就觉得张春桥反军不得人心,此时也公然奋起炮打张春桥,4月12日发出讨张传单,上列十条口号,揭发了叛徒张春桥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反军等罪状。朱锡琪是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八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八人小组成员是: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朱锡琪),他能就近了解张春桥的反动嘴脸,又有途径了解北京的信息,他的造反,不啻在张春桥心窝捅了一刀。
1968年4月12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四条宣战式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校园内盛传文汇报造反,炮打张春桥。有确凿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叛徒,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以党性担保坚持揭露张春桥曾经叛变。又传来北京消息称,“在中央还没有表态前,张春桥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奇怪的是,此话当时似传为姚文元所说,不知今天有人能证明否?),意味着张春桥确有问题,其地位已摇摇欲坠。
复旦校园顿时如炸药引爆,反张怒火轰然而起。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校园内很快出现大批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与本班一拨同学奔赴外滩,在南京东路沿街橱窗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幅标语,还有几位同学在永安公司楼上用高音喇叭作宣传鼓动。
四月十二日,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巨浪。民心相背,公道自在人心。不管权势如何煊赫,高压如何逼人,对高压的反弹所释放的能量可以排山倒海!
“中央文革”与“中央军委”决斗的前哨战在上海打响了!
四、尾声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熄火
因为实际决战时机尚未成熟,中央军委决定止兵熄火,反张斗争当日夭折。12日晚,中央军委李作鹏三点指示:贴张春桥大字报是错误的;部队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反击。反张热潮顿时浪平潮退。
据说毛泽东对善后有指示,所以张春桥尽管恨得牙痒,却没有像第一次遭炮打后那样立即制造大规模白色恐怖。校园一片沉寂,人们不知道厄运何时降临。复课不成,但学生们还是重拾书本,回到了阔别多时的图书馆。
上海红卫兵运动熄火

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实际结束的标志是1967年春军宣队和工宣队对高校的进驻。复旦大学实行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入驻的双重管制:每个班级配一名军宣队员,每个宿舍都掺沙子派入1-3名工宣队员,红卫兵对社会的介入已被全面限制。如果说军宣队还比较温和通人性,那么工宣队就显得更左更革命。尽管多数老师傅确实淳朴可亲,但另有一拨则不知天高地厚,居高临下,动辄教训师生,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撬地板,翻箱倒柜地搜查整张春桥的“黑材料”,一片恐怖。连吃饭前急切奔向窗口,没有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山呼万寿无疆的学生,也要遭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的严厉责罚。同学们连调羹撞击饭盆的声音也遭到校工宣队长张扣发的怒斥。小将们涉世未深,有此番经历,总算初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1973年响应毛泽东号召拉练,复旦大学师生风尘仆仆步行来到安徽广德,我正好在广德参加一个会议,便激动地在路边迎候母校的老师。极为扫兴的是,正亲切地与我讲话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李庆甲先生,被中文系那位工宣队赵连长当着我的面厉声呵斥,为的是竟然没有自己去领取打地铺的稻草捆!尴尬屈辱,斯文扫地,欲哭无泪啊!
全国红卫兵运动熄火
红卫兵读书还不多,但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古训应已听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国各省全面夺权之后,小将们利欲熏心,开始争权夺利,妄图瓜分享有胜利成果。他们的互斗互杀行为是丑陋的。而自命最革命,忘乎所以,恣意妄为,干扰毛泽东肃清异己的战略部署,甚或反军,反对正在使用的力量,那就是添乱制造麻烦。这就是当年所谓的“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对彻底熄灭轰然而起的红卫兵运动虚火有二计,一是釜底抽薪,还有一法便是彻底扑灭。张春桥心狠手毒一心扑灭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则采用釜底抽薪之计,打发他们远离政治舞台,结束他们的前锋使命。毛泽东发出了“接受再教育”和“四个面向”的最高指示。
毛泽东是性情中人,据云他在接见北京大学生造反派五大领袖,告别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与蒯大富相拥流泪。红卫兵运动从此灰飞烟灭。忠诚的红卫兵坚决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从此,同学们迎来了艰苦曲折的别样人生。
噩梦如影随形
一九六八年七月,复旦大学1962级(1967届)同学毕业分配。去向很分散,比66届分配方案差多了,像样的对口单位很少,但毕竟还有新华社名额。十二月份1963级(1968届)同学毕业分配,去向更惨。中文系的分配四散全国,全班84名同学分配到新疆、青海(人民出版社)、宁夏、四川、云南、广东(牛田洋军垦农场)、广西、湖南(五机部)、陕西、河南(8181部队农场)、山西、安徽(南字143部队农场)、江西(鲤鱼洲农场)、浙江(农场)、江苏、上海(插队落户)、北京(北京军区)、天津(塘沽盐场)等地。“四个面向”指示得到坚决贯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确实威力无穷!
1970年2月从安徽军垦农场再分配的复旦学生中,我们九个同学(中文系陈建清、笪远毅、谢树敏、许双元,哲学系胡传玲、项伟君,国际政治系席家生,生物系洪雨文,历史系萧昌雄)被分到宣城县工作。抵达宣城当日,即有上海市公安局来人逮捕了毕业于历史系的萧昌雄。萧曾经是“炮司”的要员,炮打张春桥的干将。张春桥到底不饶人。
宣城县五七办公室的陈善春饶有兴趣地对我和谢树敏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诱捕萧昌雄的过程。我们一身晦气,炮打张春桥的魔障如影随形,似觉自己也成了戴罪之身,如今流落宣城,已交由专司下放工作的县五七办公室直接处理,于是默默地接受分配,一个个被打发到远离县城的山隈水滨。我与谢树敏相约,所幸有大米可吃,今后争取五年内调到通公共汽车的集镇,十年进城。远期目标回家乡。昨日的天之骄子今天已全然没有救天下舍我其谁的磅礴气概了。
弱女子洪雨文以典当得到的几个小钱,坐小船孤身去了水阳水产养殖场;胡、项两口子随着嘎吱作响的独轮车,到黄渡中学安顿小家;陈建清风雪旅人,去了盛产猎户高僧故事的山乡;我则紧握仅有的一角二分钱,沿青弋江上溯,乘运草船来到建在河埂上的红杨树小镇,到一个古庙改造的“帽子中学”报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