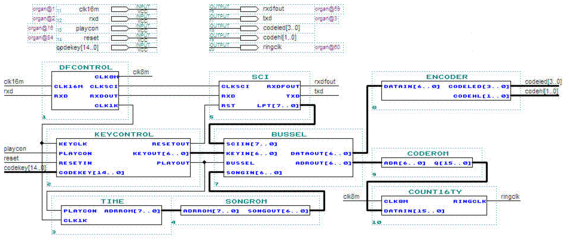僵持了几分钟,见张玄始终没露面,谢非猜想他可能对案子根本没兴趣,所以才一直让手下跟自己磨时间,他不是个不懂得察言观色的人,见既然如此,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站起来告辞,没等钟魁挽留便急匆匆地出去了。
“等我一下。”
钟魁见谢非情绪波动很大,赶忙追出去,照顾他的面子,等走出一段路才说:“他们平时说话也是这样的,你别在意啊,其实我们不是不帮你,我再……”
“我懂,”出了门被冷风吹到,谢非逐渐冷静下来,打断钟魁的话,说:“没关系,突然拜访,我想我也是唐突了。”
他把铜镜从斜肩包上解下来,交给钟魁,钟魁接住后手往下一沉,没想到看起来不大的镜子居然这么重,他忙还给谢非,“这镜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吧?那就不要抵押了,如果张玄的价码真得很高的话,我可以先帮你垫着……”
“你有钱吗?”
被问到关键问题了,钟魁挠挠头,他现在所有的花费都是跟张玄和马灵枢借的,只好说:“这你就别管了,我来处理就好,大不了先借再垫上,再想办法还。”
谢非冷笑一声,要不是太了解钟魁的为人,他一定把这话当成是在耍弄自己,张玄又不是傻瓜,没好处的话,他为什么要借钱给钟魁?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自己被算计。
“你太不了解张玄了。”他说。
“欸?”
无视钟魁惊讶的反应,谢非问他,“你信报应吗?”
这话问得既古怪又唐突,话题跳太快,钟魁不知道谢非想问什么,谢非也没再多说,拉过他的手,将铜镜背面朝上,让他拿好,郑重地说:“这次生意我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完成,如果我失败了,麻烦你把镜子还给我师妹,就是张雪山的女儿张燕桦。”
说到这里,谢非苦笑了一声,那天他跟张燕桦见面,张燕桦还几次交代说他最近时运太低,不要接活,他却没听,总觉得大难不死会时来运转,现在看来师妹的灵力果然高于他,他虽然从小学道,却不信什么报应,但连着经历了两场事件后,他想也许自己该信的,任何事情都有因有果,不是报应在当下,就是报应在后世中。
马灵枢事件还可以说是他倒楣,但这一次他想或许是他自作自受。
钟魁不知道谢非的心思,见他精神恍惚,很担心地问:“我可以帮你转交,但你要去做事,还是拿着镜子更好吧?”
“这是面照妖镜,据说威力很大,我的功力还控制不了它,你也不要照自己,免得出事,”谢非交代完,又对他笑笑,“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他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直到他走远,钟魁还是没弄懂他想表达的意思,看看手里的镜子,嘟囔:“我想,应该是你不了解张玄。”
他知道谢非的顾虑,但张玄才不会对一面小镜子感兴趣呢,能让张玄真正放在心上的这世上只有董事长一人。
更何况这镜子是不是真有威力还不知道,钟魁的好奇心涌了上来,把谢非的提醒抛去脑后,拿起镜子,将镜面朝向自己,可是镜面灰蓬蓬的,像抹了层浅墨,完全看不到他的模样。
“看来我还算一个正常的人。”
他美滋滋地把镜子放进口袋,觉得身为鬼魂的自己没被镜子照出来,要么是他还可以在人间混吃混喝,要么就是镜子根本没有谢非说得那么神奇。
钟魁回到家,银白已把坐姿换成了躺姿,懒洋洋地蜷在沙发上,一下下抚摸手腕上的黑蛇,汉堡则将茶几当成了练功场,一本正经地在桌上做运动。
谢非被气走了,这两个肇事者还一副没事人的样子,钟魁很不高兴,走过去,说:“你们刚才很过分,就算谢非以前有错,但人家都已经改过向善了,现在遇到问题,过来求我们帮忙,你们不帮就算了,干吗合伙报复他?”
“澄清一下,身为阴界使者,我没那么小心眼,”汉堡举翅膀反驳:“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帮他分析问题——没钱,在张家真得是行不通的。”
钟魁把目光转向银白,后者用嘴叼住黑蛇的颈部,正在跟它玩耍,被瞪,他放开黑蛇,说:“谢非是好是坏跟我没关系,他以前也没得罪过我,我为什么要报复他?”
“可是……”
“钟魁,要想在阳间过得久一些,做一个好鬼是对的,但不要做笨蛋鬼,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银白话里有话,钟魁忍不住问:“什么意思?”
因为银白的耍弄,黑蛇生气了,趁着他不注意游开,被他及时揪着尾巴拽了回来,手在蛇背上抚摸着,口中发出冷笑:“你刚才没看出来吗?谢非根本没跟你说实话,是谢老板家死人,不是他家死人,身为从小修道、又常年与鬼怪打交道的天师,他至于激动成那样吗?”
“是懊悔吧,毕竟他收了钱,却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导致对方家人死亡,所以会很在意吧。”
话虽这么说,但被银白这么一提醒,钟魁也觉得刚才谢非的反应有点过激了,至少他隐瞒了一些事情,而导致说话吞吞吐吐。
他的解释换来其他两人齐声冷哼,汉堡说:“相信我,亲爱的钟钟学长,一个天师他从小最先学的不是怎么捉鬼,而是学习怎样保持平和的心态,尤其像谢非这种薄情的人,他不会为了别人的生死而耿耿于怀,还有那个谢老板,他家接连死人,要做的不该是报警吗?至少要四处拼命求助吧?为什么一定要在谢非这个三流道士身上吊死?”
银白接下去,“一个人解决不了麻烦,跑来求别人,却不说出真相,证明他完全没有诚意,如果我们帮忙,很可能让自己陷入险境。”
“也许他有难言之隐呢?”
“经历告诉我,如果一个人骗你一次,他就会骗你第二次,你说对吗银墨?”
颀长手指抚上黑蛇的头部,银白话声温柔,黑蛇却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似的,突然拼命挣扎起来,钟魁这才发现银白掐的地方居然是蛇的七寸,而且下劲很大,根本无视黑蛇的痛苦反应。
汉堡也注意到银墨的不妥,跳过去叫:“喂,你要掐死他吗?”
银白松开了手,将黑蛇温柔地放到身上,换成一下下的抚摸,无视两人紧张的表情,他微笑道:“这只是我们兄弟间的玩笑。”
看着黑蛇因为不适发出激烈的喘息,身躯紧张地扭动着,钟魁跟汉堡都很想说——这是玩笑的话,那也开得太过火了吧?
不过这是他们兄弟间的问题,外人不好多嘴,钟魁拿出谢非的铜镜摆弄着,寻思找个机会再跟他沟通一下,看到他手里的镜子,银白神色一动,说:“给我看一下。”
钟魁还没回应,汉堡先笑了起来,“这是照妖镜,照你不太好吧?还是让我来照一照,看能不能照出阴鹰的原形。”
它飞到钟魁面前好奇地打量照妖镜,怕他们的争执牵连到镜子,钟魁赶忙放回口袋,汉堡不屑地撇撇嘴,“真小气,一面镜子而已,照下会死啊。”
正吵闹着,楼梯上方传来脚步声,张玄飞快地跑下来,还顺便往身上套衣服,看到他们,打了声招呼就跑去了厨房。
钟魁跟过去,见他拿了两块饼干塞嘴里,嚼着饼干又跑进隔壁书房拿文件,便问:“张玄你忙吗?”
“忙啊,”张玄匆忙中看了下腕表,“快迟到了,都怪招财猫,害得我晚起……”
“张玄,要是我想拜托你接案子,你会有时间接吗?”
“要算钱的噢……”

张玄说完,没等钟魁回话,马上又一秒改主意,冲他摆了摆手指头,“就算有钱我也没空接,小兰花丢下一大堆麻烦给我,我都快被他搞昏头了,那个混蛋!”
接下来钟魁完全没有再说话的机会,就看着张玄飞快地将饼干吃完,拿了外衣匆匆跑出去,动作利落迅速,证明他现在的确很忙,根本无暇理会谢非的事。
“看来萧兰草的事有点麻烦啊。”银白说完,见钟魁还站在那里发愣,他好心地说:“马先生的朋友十点就到机场了,他好像安排了你去接机。”
“啊,糟糕!”
被提醒,钟魁猛地想起自己的工作,拍了下额头,也跟张玄一样快速整理仪表,然后拿了饼干边吃边跑了出去,没几分钟,大厅里只剩下汉堡和银白兄弟了。
两人大眼瞪小眼互看了几秒,汉堡清清嗓子,先开了口。
“直觉告诉我那个谢老板不地道。”
“是的,”银白将黑蛇蛇尾绕在自己指间上随意转着,说:“如果我是当事人,在一家人生命受到威胁时,会想尽办法求生,而不是把赌注压在一个不熟悉的人身上。”
“反正闲着没事,要不要去查查看呢?”
汉堡兴致勃勃的提议一秒被打回,“我要冬眠了,你要是去查的话,回头记得公布下答案。”
所谓冬眠就是练功,见银白没兴趣,汉堡也懒了,拍翅膀飞回水晶灯上继续补觉。
“直觉还告诉我,少管闲事才能长命百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