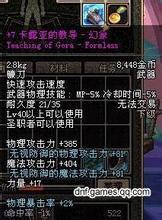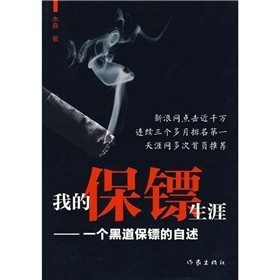15 黑道老大
昭潮阳被送回牢内不多时,佟富兴紧跟着也被调到了107号牢房。
年过六十的佟富兴手里握着厚厚一摞钱票一进牢门便神态自若的笑道:“我可是带着买路钱过来的啊,不是过来剥削大伙来啦……”
“哈哈。”
看到身宽体胖肥头大耳的佟富兴像弥勒佛一样和善,大喜过望的昭潮阳立刻释然笑道:“佛爷来啦,上铺吧。”而后又转头冲小笨娄招呼道:“小笨娄,给佛爷把被铺上。”
“谢谢。”佟富兴微笑着冲昭潮阳谢道。

……
随着日光灯被电流冲的闪了几下后,电视屏幕现出了画面。
“歇板看电视。”昭潮阳多此一举的吆喝道。
“谢谢昭哥。”牢内人不厌其烦的谢道。
“哎!这不是佛爷吗?!”章卫看着电视惊呼道。
电视屏幕上现出了佟富兴被捕时的镜头:
……佟富兴因涉嫌贪污巨额公款二百余万元于本月四日在沈阳桃仙机场被捕……
“哎!快看,这佛爷的老板包里倒出来的怎么全是避孕套啊?!”
“哈哈。”
“这年头儿的人呢!只要你有点儿事儿就拿避孕套儿往你脑袋上套,给你弄成个屌样!”佟富兴泰然自若的笑道。
“要不拿啥埋汰你啊!”昭潮阳附和道。
“这还给佛爷套了一堆套儿呢?!”
“哈哈。”
“弄这些事儿我倒不在乎,主要我得找举报我的人说道说道……”佟富兴意味深长的喃喃道。
……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提审员老刘突然出现在107号牢房的小铁窗前吆喝道:“昭潮阳,出来辨认。”
昭潮阳心里一惊,然后才故作无所谓的调侃道:“还认啥呀,长得这么帅,要是小姑娘别认完再看上我了。”
“哈哈。”
“长得倒还真是人模狗样的,净干坏事了!”提审员老刘望着眉清目秀的昭潮阳笑过后又说道:“再出来五六个人陪你。”
牢内的人顿时兴奋的站起了十好几个人。
“五六个就行啦,用不着那么多。”提审员老刘说道。
“都想放放风,辨认、多几个人能咋的啊,啥也不耽误。”昭潮阳心虚的说道。
……
昭潮阳一行七八个人在提审室对面排成一排站了下来,昭潮阳竭力向每个提审室的屋里扫视着,但因为窗玻璃的反光什么也看不到。站了好一会儿后,一个值班管教拿着一件看守所的黄马甲从提审室的大门走到提审员老刘面前说道:“把马甲让嫌疑人套上。”
见到提审员老刘把马甲递过来后,昭潮阳顿时大为反感的叫喊道:“凭啥啊,我不穿,凭啥让我套马甲啊?!”
“穿上马甲就认不出来你啦?”
“哈哈。”
“你给我穿上听见没?”值班管教指着昭潮阳威吓道。
“我不穿你能把我咋的?唬我呢!”昭潮阳怒不可遏的叫嚣道。
“你要是不穿,我马上给你砸上镣子扔小号里。”
“你别拿小号唬我,我刚从里面出来。”
“千山万水脚下过,再进一次又如何。”大尖慢条斯理的喃喃道。
“哈哈。”
“臭小子耍驴啊,还怕认啊,让刘叔难堪啊?”提审员老刘拍着昭潮阳的胳膊劝道。
身着便服的办案刑警突然出现在提审室的大门口吆喝道:“行啦,完事啦。”
……
几个月很快过去了,转眼已是深秋时节。
昭潮阳倚墙坐在靠后廊的大铁窗下,眼睛不自禁的越过后廊的大铁窗飘向外面的远山,山巅那缥缈的绿色以黯淡下来,并已有了一些枯黄。天空是那种很柔和的蓝色,云朵却很厚重,小块儿的云朵同那腾腾直上的炊烟连在一起时,便融成了几乎是同样的暖灰色,而大块的云朵便显得越发沉闷了,被遮在后面的太阳虽然竭力放着光,也不过给这些云朵镶上了一道儿亮边。铁丝篱里的杂草也已有了这深秋之色,虽然还不明显。铁丝篱上还缠绕着一些爬藤,一些尚未凋落的牵牛花虽然还吊在上面,却透出了衰败的苍凉。藤蔓的尖梢已无力再去抓住什么附着物了,悬在铁丝篱上随风摇动着。有一小块儿曾被锄过的地方又长出了嫩草,中间还开出了几朵孱弱的小花,同样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并且那小草的嫩绿和小花的娇白之色也同样是抑止的。
后廊窗外是那么的静,杂役犯都不知去了哪里。地上只有几只苍蝇时落时起,似乎连那恼人的嗡嗡声也无力发出了,前些日子还在这杂草丛中飞舞的蜻蜓突然都不见了,昭潮阳还清晰的记得那些蜻蜓,在那清冷的阳光下,蜻蜓的翅膀像似被揉皱了似的不再坚挺,落在一处后便久久不再飞起了。一只小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进了那片儿杂草丛中,也飞进了昭潮阳的视线中──当春天来时,最先看到的便是这小蝶;当冬天来时,最晚离去的也是这小蝶,真不知道它这早来迟去的一个过程是为了什么……
走廊上突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脚镣拖地的哗啦声,声音由远而近,昭潮阳起身走到小铁窗前向外看时不禁大惊失色,镣铐加身的傻得胜在六七个特警刑警和管教的押解下走到107号牢门前停了下来。
随着牢门上的铁链子哗啦一声响过之后,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的傻得胜面无表情的从半开的牢门下钻进了牢中。
昭潮阳紧握拳头站起身凝视着傻得胜,目空一切的傻得胜如入无人之境似的直视着墙壁,连看都不屑看牢内人一眼。
“给他锁墙上。”提审员老刘把一把铁锁从小铁窗外递进牢中。
“铐子不摘啦?”昭潮阳接过铁锁关心的冲窗外的周管教问道。
“不摘,晚上多搁几个坐班的看着他点儿。”周管教面色凝重的答道。
“进号就宣倒,这个事儿不小啊!”大尖望着傻得胜脚上的特号脚镣喃喃道。
看到既不给傻得胜摘手铐,又给傻得胜锁在了墙上,昭潮阳这才松了口气。
“滚上去。”章卫站在铺边冲傻得胜低喝道。
傻得胜默然抬脚向铺上迈去,昭潮阳这才注意到傻得胜两腿剧烈的颤抖着,死灰一样的脸色和死灰一样的眼色中看不出有丝毫惧意,紧闭的嘴深含着一口气,看得出身体完全赖以这口气撑着才没倒下去。
昭潮阳在把傻得胜的脚镣锁在墙环上时一次又一次的凝视傻得胜,下意识的希望傻得胜能注意到自己,但傻得胜那无视一切的目光总是停留在他对面的墙壁上。昭潮阳感到一言不发的傻得胜像没有人类思想的某种少见的兽类一样令人难以捉摸,不过长了个人形而已,同时又感到半死不活的傻得胜像自己在严管号中遇到的那只垂死的小蜜蜂一样没有危险性,于是闲心难忍的冲小笨娄吆喝道:“小笨娄,给他讲讲规矩。”
小笨娄愣了一下后转向锁在墙上的傻得胜语无伦次的嘟哝起来:“嗯、让你家来投钱衣服和吃的,不来、就死屁了,嗯、现在是经济改造——嗯、给家里打电话要钱要衣服,要吃的,烧鸡花生米什么的……”
“哈哈。”
“对,要油大的,经饿的,二斤一个的,香肠一百米,花生一麻袋,咸鸭蛋一筐……”
“这小笨娄饿蒙啦!”
哈哈。”
“小笨娄、继续说。”待到众人大笑过后,意犹未尽的昭潮阳冲小笨娄吆喝道。
“嗯、不来钱,就死屁了,昭哥是管号的,和昭哥别撒谎,昭哥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有事和昭哥说,别说话;挨打要说谢谢,是帮你改造;嗯,管教提你、出门先蹲下;管教问你什么别撒谎,问你号里有来钱的没有,你就说没有;问你号里有打架的没有,你就说没有;让管教通知家里投点儿衣裳再投点儿钱;送你回来,要说谢谢管教……”
“没想到小笨娄讲规矩讲的不错啊!”
“哈哈。”
昭潮阳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监规冲章卫示意道:“把监规给他让他背。”
“三天内把监规背会,这是政府规定的,你要是背不会,三天内要是背不会,干死你听到没有?”章卫把监规递给傻得胜时看到傻得胜直视着墙壁不接,于是在把监规摔向傻得胜脸上同时又猛的朝傻得胜的背上踹了一脚。
傻得胜的身子向前一栽一口血吐在了铺板上。
“我操,郝仁进号喷屎,你进号喷血,再来一个还不得喷下水啊!”昭潮阳冷笑道。
“算啦,他在办案单位被弄的就剩一口气儿了,别沾包。”佟富兴意味深长的冲昭潮阳劝道。
“佛爷说的是。”昭潮阳凝视着半死不活的佟富兴不禁陷入自己被抓进刑警队时的一幕:
“……自己和汪晴喝的红酒竟是死去的卓军留下的,真晦气!虽然自己喝了多半瓶红酒,但神志是清醒的。当自己被刑警戴上手铐时还并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只是汪晴母亲的大哭小叫令自己慌乱不安。
‘汪晴,你怎么这么傻啊——作孽啊,她才十六岁啊——汪治国,你害苦我们娘俩啦……’汪晴那胆小怕事的母亲哭叫着扑上前却没敢打自己,而是狠狠的给了汪晴一耳光。
‘你打她干什么?’刑警难以理解的拉开了汪晴的母亲。
‘你妈看不上我也用不着这样啊……’自己故作无所谓的和面无表情的汪晴调侃道。
……
直到自己被押进审讯室才开始感到焦灼不安,恐惧后悔,不能面对,只想逃避。自己本能的对抗审讯,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耳光拳脚,但自己并不感到有多疼痛,只是感到无助和羞辱,当自己被脱得赤条条的被摁趴到凳子上并且四肢都铐在凳子的四腿上时,那种难为情和羞辱令自己痛不欲生,生怕被人看到,生怕被认识的人看到,生怕被史裕恒看到,生怕会有女刑警进来,自己的精神肉体和防线在政策攻心和不断加大审讯力度下最终还是崩溃了……
自己在审讯室中走完过场后,被押到了二楼的一个办公室内铐在暖气管上等候送看守所,自己在极度的焦灼恐惧中几乎崩溃,只想逃离,无论何种方式,哪怕是用死逃离。自己唯一能够摸到的只有放在窗台上的一把黑色折叠伞,当自己冒出把折叠伞上的铁搭扣吞下去的一瞬突然从隔壁走廊上传来一声女子的尖叫,随后楼下响起了嗵的一声,楼内顿时引起一阵骚乱,自己伸头向楼下看去,一个瘦小的女孩趴在楼下的地砖上剧烈的抽搐着,血从口鼻中涌了出来,染红了灰白的地砖。
‘……她要逃跑,我站得离厕所门远了点儿,一把没扯住……’走廊上响起了一个男人苍白的辩白声。
自己在听到那辩白的一瞬,顿时打消了吞下那铁搭扣的念头。
‘怎么回事儿?’坐在门边看守自己的刑警朝另一个从走廊上走过来的刑警问道。
‘老刑做得有些过了,那小姑娘就是一个卖淫的,老刑让她说出嫖客的名字,小姑娘说不上来,老刑给小姑娘炼劈叉,小姑娘疼得受不了,借上厕所的空儿一个高从二楼上跳下去了!’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