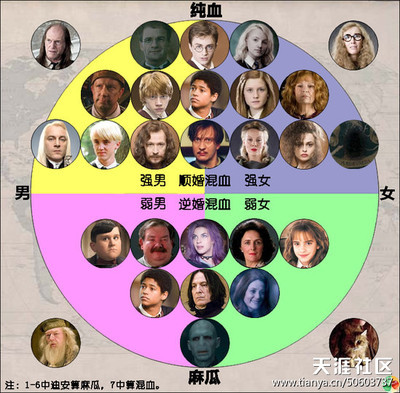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历史教训
作者:海南特区报来源:廖逊19950914
环视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环视在今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行列中,有多少当年的胜利者已经不复存在:在欧洲和亚洲两大战场之下不朽功勋的苏联解体了,今天的俄罗斯毕竟只是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当年最先被张伯伦——达拉第绥靖主义出卖的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了,这一次是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条件下,自己分了家,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而最悲惨的还是南斯拉夫,当年在南共和铁托元帅的领导下,用170万人的生命赢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今天已经完全丧失,全国分裂成为五个相互反目为仇的独立国家,其中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又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一连三年,都是全世界关注的战争热点。
前苏、前捷、前南三国变成了二十几个国家,真不知道这两亿多不幸的人民,今年正在做何感想?而在其中,又以两千三百多万前南斯拉夫人民的处境最为不幸。好端端的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今弄得四分五裂,相当多的人民沦为赤贫,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不错,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南共和铁托的政策有错误,但是又有谁能说今天的前南地区各国人民,比生活在铁托时代更加幸福呢?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有国家的统一,有领土的完整,有国内各民族的和睦相处,有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前提——政局稳定。
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分析家,纷纷从不同的专业角度,探讨了导致前南斯拉夫走向分裂、走向战乱的根源。尽管这些论者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但至少在三个方面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其一是“工人自治”的失误,其二是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其三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上的失误。而种下这些祸根的不是别人,正是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回顾这些历史教训之时,才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哀。
一、“工人自治”的失败
直到十年之前,我本人还对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推崇备至。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苏联传统模式在社会主义各国都走到了尽头,“大政府”事无巨细地包办一切的弊端日益明显,与此相应的、以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为特征的旧国家所有制潜力殆尽。表面上“人人都是主人”,实际上没有人对公有财产真正关心爱护,使所谓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成了无主共有,“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巨大的流失和浪费。当所有这些弊害,都在实践标准的检验面前暴露无遗之际,极度失望的中国学人纷纷把眼光投向了前南斯拉夫。
早在50年代初,南共和铁托同志就撇开了前苏联的教条,另外走了一条道路——“工人自治”。它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直接结合起来,使工人集体在每一个企业,都摆脱了异化心理,变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民主选举厂长经理,企业独立核算、自负赢亏、自担风险,政府不再插手工厂的内部事务,政府的职能大大削减,不再包办一切,退而成为经济的间接调控者。于是,前南斯拉夫就变成了第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学人高度注意。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南斯拉夫同志的这套做法,远远比前苏联的传统模式,更加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本来设想。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论者指出,“工人自治”要比苏式“国家所有制”,更加接近马恩设想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政府也像巴黎公社一样,只承担“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些发现,当时真使我们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当一批又一批中国学人目前南斯拉夫考察归来之后,刚刚燃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他们意外地发现,那些“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变成了工团主义的封闭堡垒。所有的工人集体几乎都对扩大外延性再生产毫无兴趣,一有了钱就想“分光吃净”。强烈的福利主义倾向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改造,而且严重地阻碍了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所有的工人集体,都不能合理地组织经济资源,对于外来工人盲目排斥,绝对不容许别人分享自己的机会;对于本企业的闲置设备、闭置材料宁愿囤积,也绝对不容许之流入社会的短缺行业。正因为如此,前南斯拉夫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各级工人委员会,也都变成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辩论俱乐部”,丧失了必要的决策机能。
前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和所谓“社会所有制”(其实就是工团所有制)的失败,带走了我们依靠直接从经典著作寻章摘句来寻找改革方向的最后希望,不得不真正完全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其结果,就是“中共十四大”和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阐述的那一整套思想。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建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重新摆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使企业像作为微观经济组织者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社会的经济资源能够通过更加自由地流动和组合,达到优化配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一个坚实牢固的财产制度基础。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对前苏联传统模式的某种否定,又是对前南斯拉夫改革模式的某种否定。那种仅仅根据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走不通,就断言中国也将解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走不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民族政策的失误
前南斯拉夫过去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先后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所统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有塞尔维亚、门地内哥罗和马其顿三个独立的南部斯拉夫民族获得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战败解体,六个南部斯拉夫民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王国。由于这个多民族的王国,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塞尔维亚人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各民族之间的摩擦内耗一天也没有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就利用了这一点,明里暗里支持种族仇杀。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共,领导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英勇反抗,以170万人的生命,赢得了自由独立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博得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人民的衷心拥戴。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南共和铁托威名远播,保加利亚国际尔巴尼亚也曾酝酿过与南斯拉夫一起,组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多民族国家。此事引起了前苏联领袖的警觉和反对,导致了此后一连串冲突,和前南前苏的分道扬镳。
在如此艰难的历史条件下,铁托和南共依然坚持捍卫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团结了全国上下。前南斯拉夫没有多数民族,协调各民族的利益矛盾难度极大,但居然能够在东西方阵营的双重压力之下,坚如磐石,这不能不归功于南共和铁托的英明领导。不过在后来前苏前南关系缓和之后,铁托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又频频得手,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工人自治”也引起了东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兴趣,使前南斯拉夫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远远超过了其国力的重要角色。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南共的民族政策,又开始连连失误。
外部的压力减轻了,“工人自治”又远比前苏联传统模式的公有制,对广大工人群众更有魅力,就诱使铁托和南共领导层进而把这种理想化了的模式,进一步推向极端,推向社会管理和民族事务的管理。于是各级政权,也都变成了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议政合一的“自治委员会”。假如前南斯拉夫和波兰一样,97%以上的居民均属同民族,事情倒也好办。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前南斯拉夫是一个没有多数民族、只有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对中央集权的任何放松,都会直接导致各个民族共和国之间离心力的增强。
在民族政策方面,前南斯扶夫与前苏联同志错出同源,都在于片面地理解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概念,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地区之间经济的结构性互补和文化的水乳交融。在这些方面,前南斯拉夫至少有四点比前苏联做得更差:
其一,前苏联实行的毕竟是计划经济,各民族地区和民族共和国之间没有健全的横向市场交流,一切资源的流动,都要通过纵向的行政渠道,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大而全、小而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格局。然而前南斯拉夫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民族地区和民族共和国之间完全有条件发展健全的市场机制,一切资源本来就通过横向渠道流动,应该容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型结构。令人遗憾的是,南共同志们没有从国家的安危和长远利益出发,“趁热打铁”,运用积极的产业政策去促进经济整合,反而满足于表面上的国泰民安,因而坐失了良机。
其二,前南斯拉夫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所谓“通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并没有促进塞尔维亚语的克罗地亚化,或克罗地亚语的塞尔维亚化。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不利的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例如新加坡就把英语确认为官方语言,其实那里真正以英语为母语的居民却微乎其微。可人家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就有那个眼光和魄力,在全民范围之内大力推广英语,而且居然也在所有的公务员和军人之间办到了这一点。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本来对殖民主义者的语言并不感兴趣,之所以接受英语作官方语言,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共识。实践证明,这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前南斯拉夫没有一种统一的官方语言,使人民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是导致其解体的又一个直接原因。
其三,南共同志过于简单地认为,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来源于“资本主义”,而由于“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就不必再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做任何事情。关于这一点,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阿列克萨·吉拉斯,在今年7至8月号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写道:“……各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少。南斯拉夫没有创办任何所有民族的人都能去就读的大学,也没有实行一项鼓励学生们到别的共和国去学习的政策。一位克罗地亚教授很少到贝尔格莱德去教学,一位塞尔维亚教授也很少到萨格勒布去教学。……各个共和国文化和知识上的这种闭关自守,帮助保护了各种集团的传统的民族主义。”
其四,前苏联虽然在表面上也承认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但事实上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之前,从未真正实行过。不像前南斯拉夫,一再通过削弱联邦政府的权限,来扩大地方民族自治权限。“1974年宪法”甚至把整个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联邦议院再实行两院制和代表团制。每个代表团一票,做决定时还要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等于每个代表团都享有“一票否决权”。这就使得地方民族主义可以无限制地膨胀,联邦政府形同虚设。
这样的民族政策,深深地埋下了日后解体的祸根。
三,凝聚力的最后瓦解
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先后出现过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过丰富多彩的不同经济模式。前南斯拉夫模式,是其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也最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本来设想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观察过并热烈赞扬过的“巴黎公社原则”,最大限度地体现在南斯拉夫同志的实践中。不过,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共和国的国情与传统,毕竟与法国多有不同因此在最大限度地贯彻“巴黎公社原则”,最大限度地接近马克思的“自由人”、“自由人联合体”、“政府只承担必要而有限的职能”等设想的同时,南共和铁托还不得不保留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有些方面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从实践效果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补充和发展,对前苏联同志经验的这些吸收和借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南共和铁托最重大的创造,在于1956年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文写入了《南共纲领》。但是,没有健全的财产制度作前提,任何市场经济都不可长久地存在。“工人自治”造成了财产权利方面的巨大漏洞,每天都在消蚀着前南斯拉夫的国家实力。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只要还有南共,只要还有铁托,前南斯拉夫模式就还能够运行下去,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还能够得到维系。这是反法西斯170万人的生命和数百万人的鲜血,换取来的。
80年代中后期,南共各基层党组织又改行属地管理原则,打乱了原有的组织系统。于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全靠伟大的领袖铁托元帅自己的个人威望。一个风烛残年的暮年伟人,成为前南斯拉夫安定团结、国家统一的最后象征。这位高龄伟人一旦去逝,四分五裂的大势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可惜现在我们能够获得的资料太少,否则一定要解开一个谜:为什么一个由各民族共和国、自治省组成的联邦主席团,在一年一度轮留担任主席的荒唐制度之下,还能够把“国家统一”勉勉强强地维持了好几年。这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大市场,没有统一的政令和法律,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兄弟们“各开各的灶,各吃各的饭”,没有一个家长来抽肥补瘦、调剂余缺,只有一个“国家”的空架子,只有一群每年一换、说了不算的联邦主席团主席。这些主席同志,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作为,因为只要有哪一项措施不如本民族共和国的意,主席本人就有可能被罢免,所以他们注定只能做本民族的代言人。而“协商一致原则”,或“一票否决权原则”,又更使联邦主席团主席的一年任期,终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之下,前南斯拉夫的“国家统一”居然还能维持到90年代初,难道还不算是一个“奇迹”吗?这说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结盟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红利”,还没有被最后吃完。
1991年,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在西方国家怂恿和干涉下,最富庶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率先独立,前南斯拉夫土崩瓦解。这也是本文应当总结的最后一个教训:并不是那些平时吵吵闹闹地要补助的“穷兄弟”,而恰恰是那些年年做贡献的发达地区,带头闹分家。无独有偶,在前苏联,最先分离出去的是最富庶的波罗地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而当斯拉夫三大民族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宣布独立,摩尔达维亚也随之独立,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分离出去之后,最为贫困落后的中亚细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依依不舍地扯起独立的旗号。前南斯拉夫与前苏联在解体过程中的这一共同性,虽然绝非偶然,它表明了某种客观规律,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探索。我们对地方、民族分离主义的防范,应当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这也是本文要总结的最后一条教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