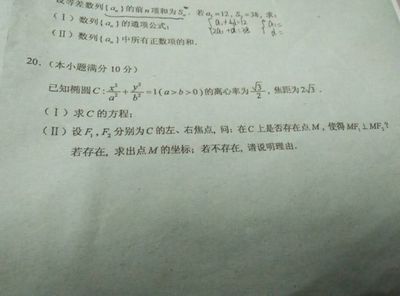抓住情节的情感因果关系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孙绍振
关于这首长诗,网上有一个“优秀”教案,对于文本是这样分析的:
课文把握:文章结构
开端——兰芝被遣
发展——夫妻惜别(再发展——兰芝抗婚)
高潮——双双殉情
尾声——告诫后人
把情节划分为开端、发展(再发展)高潮和尾声四个要素,这种观念,同时又是一种方法,在当前具有极端普遍的代表性。在几乎全部教参中,在见诸报刊的情节分析文章中,莫不以此为准则。这是不是暴露了语文学界知识结构严重的落伍?上个世纪末,我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套以“新”为标榜的课本,曾经指出其理论落当代文学理论三十年。当时,许多人士曾经质疑是否言过其实。今天看来,在情节理论上的落伍,可能不是三十年,而是两千三百年的问题。
这个四要素的弱智理论,是五十年代从苏联一个三流学者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搬来的。这个所谓“理论”在五十年代,就是千疮百孔的。首先,这并不是文学作品所特有的,而是任何小道新闻、末流的花边故事所共有的,并没有显示文学情节的特殊性。其次,它给人一种印象,情节就是四个并列的要素,只有表面的时间顺序的联系。再次,它并没有揭示出这四个要素内在的逻辑关系。其实,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早在《诗学》中,就根据悲剧的就分析出情节(“动作”“行动”)就是一个“结”,和一个“解”,当中还有一个“突转”和“发现”。“结”就是结果,“解”就是“原因”,而“突转”,就是从结果的谜,到原因的“发现”。《诗学》第九章说:“如果一桩桩事情是意外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按: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效果。这样的事情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这个说法,到了二十世纪被英国人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通俗化为情节就是因果关系。他举例说,国王死,王后随之也死了。这是故事,故事只是按时间顺序的叙述,还不能算是情节。情节则蕴含着因果关系。如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原因是,因为悲伤过度。这就是情节了。
这么经典、这么权,又这么简明的论述,我们语文学界视而不见,却在那个四要素中执迷不悟,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语文界的咄咄怪事。
当然,上述理论,并非十全十美,仍然有质疑的余地。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并非一切有因果关系的故事,都可能是具有文学性的。拘于理性的、实用因果,就很难有多少文学性。祥林嫂死,如果原因如茶房所说“还不是穷死的”死的原因,很符合日常理性逻辑,这就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而祥林嫂死了,原因是人家岐视她是再嫁的寡妇,她自己也觉得有罪,给庙里捐了门槛。她以为取得了平等敬神的资格,没有想到人家还不让她端敬神的“福礼”。从理性来说,这有多大了不得呢?何况人家说话很有礼貌“祥林嫂,你放着吧。”给她留足了面子的。然而,她却因此精神崩溃了。失去了劳动力,沦为乞丐,最后死了。这个死的原因,就不是一般理性逻辑能够解释的。这是特殊的情感原因造成了悲剧的后果。用学术语言来说,这是审美因果。这才叫艺术。这个说法,在我八六年代出版的《文学创作论》和2006年出版的《文学性讲演录》中。许多第一线的老师,很喜欢的我的文本解读,却忽略了我的解读的理论原则。
其实前面所提到的情节理论,还是比较古典的。然而对于经典文本来说却是起码的。
这个理论基础和季莫菲耶夫那种弱智的四要素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因果关系,情感性质的,审美价值的因果关系。让我回头来看看,那个优秀教案的问题出在哪里。开端——兰芝被遣,发展——夫妻惜别(再发展——兰芝抗婚),高潮——双双殉情,尾声——告诫后人。这里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要死呢?从理性逻辑来说,本来可以不死的嘛的。对于刘兰来说,改嫁并不是一定走上死路。这个教案的作者,还是有一点学问功底的。他启发学生说:
封建社会禁锢妇女的一整套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汉魏之前,再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汉魏时期,限制再婚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但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尤其那些人品才貌出众者。西汉卓文君新寡,司马相如以琴挑之,一曲《凤求凰》,卓文君便随司马相如去了。东汉邓元仪之妻被休后嫁给华仲,华仲做了大官,偕妻过街市,令邓元仪羡慕不已。东汉末蔡琰(文姬)初嫁卫仲道,后为乱兵所掳,嫁匈奴,曹操用金璧赎回,改嫁官吏董祀。刘备取了刘琮的遗孀。魏文帝曹丕娶了袁术的儿媳妇甄氏。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诸如此类,不可胜数。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到北宋程颐提出“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遗书》),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其侄媳也未能守节。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进一步完备了封建礼教,礼教之风渐趋严厉,寡妇再嫁是大逆不道。
这就是说,从理性考虑,刘兰芝就是被休,再嫁也不失一种选择。尤其是求婚者还是门第高于原夫家的太守。(县令三郎,太守郎君,比之庐江府小吏要富贵得多了)从世俗角度看,再嫁高官,恰恰可能是一种报复和炫耀。但是,这样的原因没有导致刘兰芝再嫁,却导致了她的死亡。其中的原因,就不是实用理性的,而是情感的,也就是把情感看得不但比高官门第,比荣华富贵更重要,而且比生命更重要。
从焦仲卿方面来说,也是一样。休了刘兰芝,他母亲也是作出允诺“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如果要说纯粹为妻室的话,焦仲卿可能活得更好。但是,焦仲卿却自己和刘兰芝的感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长诗可以说是坚贞不屈的爱情的颂歌。
但是,这还只是因果逻辑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焦仲卿的母亲。正是她导致了焦刘二人的死亡。那么她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她的粗暴,是她的无理,她的淫威,她只以自己的感情的发泄为务,“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不但不顾儿子的感情(何乃太区区),而且以践踏其感情为快。她的粗暴,所为何来?来自家长制的权力:(《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管妻子有多少委屈,只要父母不满意,就可以驱逐,就可以施以最大的侮辱。这就使得焦母,完全拒绝自己儿子的申辩,不能理解儿子的感情,“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即使儿子已经说出了不想活的话,她也不是没有听懂,没有认真对待,而是一般的宽解:“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焦刘二人悲剧的死亡,当然是对她的批判,但是,不仅仅是针对她个人的,同时又是对野蛮体制的、专制权力的控诉。
作为个人,她的的无情正是情感特点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家长虽然专制,但是,并不是一架粗暴的机器。
她对自己的儿子还是有感情的。她自以为,自己还是考虑到儿子的幸福的。“东家有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他的理由,显然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性质的,在她看来,只要自己觉得“可怜体无比”,儿子就肯定中就会觉得可爱无比。她所遵循的是自己的情感逻辑。儿子不想活了,她也哭了(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最后儿子自杀了,对于她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两家求合葬”可以看出,她是后悔不及的。她的悲剧在于,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和体制赋于她的权力之间的不平衡。滥用权力,使得自己的爱和儿子的生命一起受到扼杀。
在导致悲剧的原因中,唯一支持兰芝的家长,是她的母亲。她以女儿的情感为准则,拒绝了两次求婚。她如果不是这样尊重女儿的感情,而是说服、诱导女儿改嫁,那只能是另一种悲剧,虽然,也许不是死亡的悲剧。
从刘兰芝的兄长方面来看,其因果是世俗的的:“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个逻辑的因果,是彻头彻尾的实用的,完全不讲情感的。作者把这个兄长的的世俗实用观念设置为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为了反衬主人公的情感因果。
从情节来看,它的特点,是非常丰富的的、多元的情感因果;然而它又是非常单纯的,多元情感因果,集中在一元的结局上。
五个人物,从五个方面,出于五种不同的动机,把压力集中到刘兰芝的焦仲卿身上:要么牺牲情感,屈从世俗的价值准则,各自嫁娶成婚,忍受长期的、隐性的情感煎熬,要么,把情感当成最高准则,以死亡来抗议。从这五个方面的因果统一为完整的结构,可以看出,长诗的情节是非常成熟的。要知道,当时甚至稍后的叙事作品,具备小说的雏形的《世说新语》,魏晋志怪,一般还只是片断的故事,因果关系并不完整,就是完整(如周处除害,宋定伯捉鬼),也只限于理性的,或者超自然的因果。其规模,也只是一个因果。而这里,却多个人物,几条线索的情感逻辑集中到死亡的别无选择上。
长诗的统一和完整,不仅仅表现在叙事情节的统一,而且表现在抒情结构的有机上。
这是一个悲剧,一个抒情性质的悲剧,“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开头就确定缠绵缱绻的基调。而在结尾处,又是大幅度的抒情: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开头的孔雀变成了鸳鸯,在缠绵缱绻的调上高度一致,而且有所发展,枝枝相覆,叶叶交通。仰头相鸣,夜夜五更。在浪漫的欢乐上又有所提升。
其次,五个人物,也从这个完整统一的情节中以各不相同的逻辑,而获得自己的生命。同样的刘兰芝的家人,其母亲与其兄长就炯然不同。也许其兄的粗暴个性显得比较单薄。但是,在情节上,却特别的有机。其兄对刘兰芝具有超过其母的压力,也是刘兰芝最后选择死亡的近因。作者很有匠心地在这个人还未出场就作了伏笔,在和焦仲卿相约重圆的时候,就有提示了危机: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
这一点不可小觑。这种为最后的结果,埋伏结果原因的手法,出现在早期叙事诗歌中,可以说是超前早熟的。要知道,在叙事文学中,这种手法的运用,差不多要等到《三国演义》才比较自觉。在短篇小说中,就是在宋元话本,还不普及,通常是采用“补叙”的手法。《京本通俗小说》中有经典性的《碾玉观音》,写郡王家管绣花的秀秀和给郡王家碾玉、刻制玉器的男工崔宁的爱情故事。郡王家失火,秀秀拿着包袱拉着崔宁要私奔。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结果,作者事先并没有显示充足的原因。相当于把枪弹打出去,事先却没有把枪挂在墙上让观众看到。作者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在这时候“补叙”了几句:原来郡王曾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来嫁与你。”崔宁谢了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死心,秀秀认得这个后生,却指望,但后来郡王忘了,于是秀秀采取了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就抽冷子跟他跑了。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就用这寥寥几笔补叙,不能算是成熟的办法。后来的小说就不是采取这种补叙性的作法,而是事先埋下伏笔。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把这种方法叫“隔时下种,先时伏着”:“《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奕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而已。……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提不来之时,便凭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的手法使得本来关系亲密的人物,在情感上拉开了距离,发生了错位。导致了亲人的死亡。从主观来说,就是兄长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希望妹妹化悲为喜,一心为妹妹打算,却把妹妹送上了死路。发生在刘兰芝兄妹之间的因果同样发生在焦仲卿母子之间。关系越是亲密,心理情感的距离越是扩大,后果越是严重,就越具悲剧性。越是具有悲剧性,人物也就真有个性。
当然人物之间,拉开距离,错位最曲折的,也是最动人的,要算是刘兰芝和焦仲卿。
焦仲卿表面上看起来,对母亲是比较软弱的。但是,第一,这有一定的时代因素,魏晋之际,统治者,“以孝治天下”,不孝父母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是可以治罪的。第二,从根本上来说,焦仲卿对感情是很坚定的。从一开始就声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最后,他虽然屈从母亲,但是这是表面上的,暗地里和刘兰芝密约。这明显是阳奉阴违。相比起来,刘兰芝则不服,而对焦仲卿都有点赌气的:“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而且对焦仲卿的密约,也有点矛盾:一方面,和焦仲卿一样是山盟海誓“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则又担忧哥哥作梗。这个刘兰芝的形象,不像后代类似题材中的女性形象那样比之男性更坚定,而是相反,更实际,更具外柔内刚的性质。她受到哥哥的威逼,居然不屑抗争:“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不但爽爽快快同意改嫁太守之子,而且决计马上结婚。这里显然是,反抗无望,废话少说。而正是这一着,拉开了她与焦仲卿的距离。焦仲卿一下子变得相当激烈:“贺卿得高迁!”,祝贺,已经是讽刺了。接下去更厉害:把当时的盟誓中的“磐石”和“蒲苇”的比喻提出来,几乎是责问:“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最后则是生离死别,分道扬镳,“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个在母亲面前多少有些软弱的男士,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话说得一点余地也不留,可见其神态是有一点决绝的。这就逼出了刘兰芝的话““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可见刘兰芝当时同意再嫁是“被逼迫”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妇女在比之男性更多的是无奈。
虽然从态度的坚决来看,焦仲卿比之刘兰芝更为果断,但是,长诗的作者似乎对刘兰芝似乎更为钟情。这种偏爱十分明显。每逢比较重要的场景,给于焦仲的卿的,就是比较直率的语言,而给予刘兰芝的则是非常夸张的排比和形容,有时达到不厌其烦的程度。例如,一开头是: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
被遣回家时,母亲这样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
从修辞来说,这里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是,重复不要说在诗歌中,就是在散文中,也是大忌。但是这里却是有意为之。虽然,刘兰芝在面对婆母之时自述:“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这种重复,实质是反复提醒读者,事实并不是如此。第二,所重复的句式,从散文观念来说,又属于一种流水帐似的的罗列。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特殊的、铺张的趣味,这种趣味不是文人诗歌的,而是属于民歌的,和《木兰词》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那样对仗工稳的唐诗句式,所代表的文人诗歌的精英的意趣不同,这是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是,从内容来看,却不完全是民间的,而且也是精英的。织素、裁衣属于女工,可以说是平民的,也是正统意识形态规定的。至于“弹箜篌”,“诵诗书”,则无疑有文人的精英意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表现刘兰芝,从民间和文人两个方面进行美化,诗化,从人格修养(如对待小姑,留饰物以待后来者)多方面进行理想化。
铺张的手法在《木兰词》中的叹息,买马、归来,换装有着系统的展示。《孔雀东南飞》把这种手法全都用在刘兰芝身上。每逢有什么重要环节,作者都要不懂笔墨来铺张一番。如离别时:
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以装饰的丰富和华贵来表现人品的高尚,以铺排的句式来表现精神的夸耀。这种手法的运用,似乎并不以情绪的昂扬为限,哪怕就是被迫答应贵家公子的婚事,情感陷入灾难性困境的时候,也不例外。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赍钱三百万”“从人四五百”仍然是一种夸耀,但是,这不是夸富,夸贵,从正面来说,这样的排场只有这样的人品才能匹配,这样的排比只有这样的精神才值渲染。这种渲染,甚至在悲戚的情绪中,也不可缺少。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花在这方面的篇幅,甚至比之她自尽的场面还要多。就总体来说,长诗属于叙事诗,奇特的是,全诗叙述成份很少。但是,除了一些交代性过渡性的叙述语句以外,长诗的叙述,不但精炼,而且情感深厚。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为这个绝命的情节的高潮,诗人营造的环境,是十分和谐,一方面是,奄奄黄昏,视觉暗淡,寂寂人定,听觉宁静。从这里,读者可以感到,在句法上,难得一见的比较整齐的对仗。但,并不如木兰词那样,在平仄上工整。如果仅仅如此,不过就是宁静而已,诗人刻意加上“牛马嘶”,在为兰芝的自杀平添了苍凉意味之时,诗人的叙述突出了惊人的细节“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面临死亡还不忘揽裙脱履,显示了兰芝惊人的从容,可谓神来之笔。
诗人叙述是有工力的,但是惜墨如金。作者显然有意在开头按捺一则“小序”,把情感骨架基本上全都交代了。故一开头,就是兰芝的独白。不但交代了身世,而且把情节推移到危机尖端。几乎所有人物,包括两个主人公,主要是通过对白的呈现,而不是通过动作的描述。
作为叙事诗,通篇却很少叙事,这和与之齐名的《木兰词》恰恰相反。《木兰词》通篇都是叙述,连比喻都绝无仅有。这在讲究比兴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很是罕见。而同为叙事诗的《孔雀东南飞》却极少叙事。全诗364句,连叙述带铺张排比的抒情才128句,其余都是人物的对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首叙事诗,其实是以戏剧性对白为主体,叙事语句,大都是过渡性的交代,“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阿母谓府吏”“府吏长跪告”:“府吏谓新妇”“新妇谓府吏:”作用就是对白之间的串连。偶尔有所描写,如“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像这样有细节的描写,可谓凤毛麟角。
从总体来看,《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词》相比,语言显然要朴素得多。文字上也不免有些粗糙,文人加工的痕迹比较不显著。有些地方,还留下了一些情节上的漏洞。如“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其中的叙述有些混乱。语文出版社对“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的注解说:“这里指向县令复命后,从县令处离去。”对“寻遣丞请还”注解说:“不久差遣县丞向太守请求工作回县。”显然是,脱离了文本把把太守硬推出来,这就有点曲为其解。但是,即使这样,不还是没有理顺。“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显然不应该是县丞向兰芝的母亲说的话。所以注解又说,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两句,应该是兰芝母亲推托的话。这说明,加工者驾驭语言的水平,更多的是民间人士。正是因为这样,民间文学民歌的色彩,要深厚得多。
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有独特的优势。但是,这仅仅限于抒情诗。正是因为这样,到了二十世纪美国才产生了意象派,刻意师承中国古典抒情诗。但是,中国古典叙事艺术却并没有这样的荣耀。究其实绩,中国古典叙事诗传统不能不说是比较薄弱的。经典文本有限,最著名的,只有《木兰词》《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等不超过十首。但是,数量省却带来了质量奇高。如果说《长恨歌》《琵琶行》的伟大成就在于,发挥了中国古典的抒情优长,成功地把叙事融入抒情的话,那么《木兰词》的成就则在把抒情融入叙事。而《孔雀东南飞》以其情节的完整性,在戏剧性的对白带动叙事,其成熟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叙事超前成熟的奇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