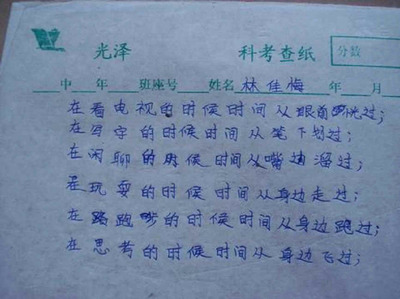题记:神池的端午节又一次来临,滚滚闷雷催我穿过蜂蚁般的人群,抚摸着斑驳的古城墙,走进魂牵梦绕的雨巷,走进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在那座百年老屋前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静静瞧着屋檐水拍打儿时玩耍的石台阶,屏住气息倾听那永无休止的倾诉。
民国三十一年(1943),父亲出生于神池县八角乡张家村马姓财主家,祖上世代书香门第,此时已因种种原因没落潦倒。
就在父亲刚出上三个月的时候,迎来他人生的第一大不幸,生母得病不幸去世。于是父亲被迫托人用羊奶喂养,由于奶水不足哭闹不止,双脚后跟在席子上磨出了白生生的骨头,头顶也在墙上顶成了平顶子。爷爷马启文打听到赵官庄贫农张宝成身边无子,又好成分,便把父亲送给了他,而自己也逃到了口外,以教书度日。于是父亲改性张,起乳名奶蛋。此时义井、贺职、三岔一带的日寇扫荡不断,张家爷爷娘娘整天背着父亲东躲西藏,总算保住了性命。七岁上了本村私塾,先生给他起名世功。村完小毕业上了义井初小,整天不是去南山扛檩子,就是炼钢铁,毕业后考了个五寨师范备取生,最终未被录用,只好回村务农。
父亲虽未当成人民教师,但总是不甘心。当时铁路工人他看不下,政策上不允许孤子从军,去电影队工作养父母怕丢下他们,总是哭哭啼啼。六五年全国搞“四清”活动,父亲经贺职公社马才介绍,被选作借干去五台县的茹村、豆村一带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养父母得了肺病,人们叫老瘊子,下有我们姊妹三人,我才三岁,一家老小五口的担子一下子落在了柔弱的母亲肩上。然而父亲为了有所出息,虽牵肠挂肚却毅然走出了小山村。然而好景不长,仅当了两年借干,又无耐回到村里,仿佛去年的燕子又一次回到老屋子,但没有燕子那样的欣喜。再说养父母不久相继撒手人寰,我们便是父亲挚爱的亲人,也寄托了父亲所有的希望。就这样家乡的重重山岭,弯弯曲曲的山路让父亲走了一辈子。
他赶过皮车,是拉磨干(刹车)的。去轩岗煤矿拉大碳,在县城与乡村间拉电线杆(水泥钢筋做的),都是些重体力活。由于父亲身体瘦小,在抬电线杆时多次弄伤了腰和手指,结果后来落下个腰腿疼的毛病。后来记过工分,当过保管。大概是村里我家独门独户的缘故,又没有本家户门,加上父亲有文化,那是村支书首选的人选啊。就是记工分这个乡亲公认的吃香营生,使父亲遭到一些想要饷银的村民的围攻、谩骂。
两次任村保管员蒙受不白之冤,险点坐牢。第一次,大队的化肥被盗,父亲时任保管,被无辜关在本村学校达一个多月,母亲含泪送饭,还说不是咱偷得他们把咱怎不了,鼓励父亲保住身子。那时我还小,没记住,只是后来听父母声泪俱下倾诉的。至从那次父亲便老了许多,根本不像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第二次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的粮库被盗,父亲又任保管,被多次审问,长达整整多半年时间。我家大缸小瓮被翻了个遍,但始终没有发现半点有价值的线索,后终不了了之。可父母受尽了煎熬,我也初次尝到了人间的冷暖。
岁月无声流淌,父亲再未提起那件件伤心的往事,似乎早已忘记。却是在他的额头上却深深刻下三道皱纹,谁知这里不仅刻满了心酸的往事,而更多的是那如山的父爱。
农村包产到户的时候,父亲分了队里的青苗、一辆小平车和一头小黑骚蛋子(未阉割的小公牛)。其实说分是假,村里作了价,掏钱买回来的。忙了几年,粮食除了上缴渐有盈余,除家用和供我们上学外,略有盈余,攒钱终于买回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虽说栽杆子弄天线架子,只能收看一个效果不太好的山西电视台,父亲和我们其乐融融,有说有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心里缺少了什么似的。
哥哥退学回家,父亲带领母亲和哥哥在村东的东沟里起石头,历经两年多才圈起了五间石窑洞,给哥哥张罗几年才娶过了媳妇,这在深居农村的我家算件大事。
父亲脾气不好,我长大了才理解他,因他几十年来所受的罪与蒙的冤,还有我们的不争气,使他好像变了个人。但在读书上要求我们很严格,姐姐考上了县城羊鼻梁子重点高中,我也连续获得全贺职公社同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父亲确实为此高兴过,额头上的皱纹似乎变浅了许多,小院子里的庄稼似乎有了点点生机。
记得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可看,父亲在天阴雨湿一般喜欢看闲书,晚上一睡下,就磨得让他给讲故事,什么《隋唐演义》中薛仁贵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常此以往,我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在院子南边栽了颗杨树,被猪咬了头,支出三根旁条,母亲说那就是我们弟兄三人,你大大是孤人,你们长大就不孤了。
那时村里冬季农闲总有人减馋,叫打拼伙(众人出钱买羊宰了,炖熟分份吃)。半夜,父亲深一脚浅一脚端着一小碗羊肉往回走,当我醒来闻见一股股香味,由于家里人多,每人只能吃上一两圪垯。我参加了工作后,父母说人老了,什么也咬不下,我信以为真。
可是姐姐两年后高中毕业竟未能上考场,也未去复读,父亲伤心的只顾成天抽闷旱烟,我看着那一圈圈烟雾弥漫了老屋,除了母亲家里没有人敢和他说话。眼看哥哥和弟弟读书没有半点希望,父亲把毕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我身上。可我骄傲自大,自认为拿个“购粮证”像喝凉水一样,整天为文学梦不务正业,差点儿让父母失望,也差点儿让我遗憾终身。
父亲送我走上慢慢的复读之路,久久叹息过,我却对文学痴心不改,几次以寥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而我的散文诗作品被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报纸《语文报》采用。1991年秋,我和父亲在自家院内用连枷打黍子,却意外收到了“临汾工商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当时分数比忻州师专还高),这或多或少给父亲一点安慰吧。
父亲冬季总是闲不住,去偏关贩过瓷器,去内蒙古贩过牲口,于是后来村里有人外出倒贩总要父亲去帮忙或合伙。
父亲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一片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他的希望,那一垄垄雪白的山药蛋花是他的希望,那一浪浪蓝莹莹的胡麻花是他的希望……“四清”借干的待遇组织上一直未给落实,既是伤痛又是他念念不忘的希望。
我参加了工作也不久也成了家,但久久未能立业。几经寄人篱下,曾一度对父亲所做的努力也怀疑过。可是每当父亲拖着佝偻的身子来单位找我,我心中不知不觉涌上一股股酸楚。他言语中的无耐,再加年过半百失去了母亲,孤苦伶仃,多年来和未成家的三弟相依为命,蜗居在村里的老屋,但仍对儿孙们充满了种种牵挂与幻想。
前年的端午节第二天,因修补老屋,去西沟上边的神河路工程处要了一四轮沙子和几袋水泥,从沟顶70多度的坡上下来,不料四轮子失控,把父亲当场摔下来碰得只剩一口气。哥哥和嫂嫂雇上出租车把父亲拉上县医院,已气息奄奄,十分钟后升入天堂,是年69岁。
我和哥哥在县医院给父亲洗了身上,理了发,他头上的鲜血还在往外渗,映红了我的双手,不像从父亲头上流出,倒像从我心里流出,点点滴滴晒在医院急诊室的地上,也映红了我的衣袖。灵车载着已入殓的父亲往回走,顿时天降暴雨,我们在哭泣,老天也在哭泣。
回去自家院里,目睹三间风雨飘摇中的老房子,轻抚父亲亲手栽种的玉米已有半人高,回头再看小路南边的旱烟也郁郁葱葱,此时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那无耐凄楚至极的心情。
几天忙于给父亲办理丧事,总觉得道叉叉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不料竟是父亲的假牙,那是在慌忙抢救中捡到的。叫夜那天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掏出来放入棺内。
回想起,参加工作二十年来未能多次回去看望父亲,实在难受,也非常遗憾。如今父亲已天各一方,我心如刀绞,寸断肝肠。每到村边的路口,流下串串悔恨与无助的泪水,穿越黄花盛开的柠条地,一直洒到父亲坟前。
父亲去世后,留下两件终身遗憾的事情,一是自己的“四清”借干待遇组织上未落实;二是三弟独自一人守着三间老屋子,未能成家留下一男半女。
今年又到端午节,我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发呆,再也望不见父亲佝偻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只言片语。但常常梦见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景,梦见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回念之余,再看自己也早已为人父,“父亲”这两个字怎么这样难写。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