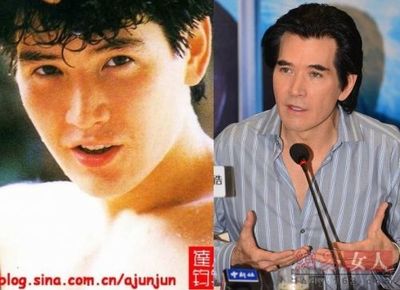子尤呆头呆脑,慢不楞腾,人家五、六个月就长牙了,一对一对的长,他十个月才长,还是一颗一颗的出。走路,也走得晚,老摔跤。说话,就更不清楚了,只有我这个当妈妈的能听懂他。那年我去伦敦经济学院上暑期学院,怕家人不明白他的意思,行前开列了一张清单,把他说的话,用汉语拼音标记出来,像:DE(一声)DEI(三声) DEI(二声),是喝水水;YA(二声) YA(三声)YI(二声)(念牙哑姨),是毛主席。这种奇怪的说话方式,子尤长大后,我们俩曾多次研究过,他的“发明创造”是在声母上还是韵母上,试图总结出一套读音规则来,但是每一次都在哈哈大笑中算了,找不着规律。总之,这个孩子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聪明伶俐,所以,在家里,除了叫“宝子”,也被唤作“儿呆”。
接下来的94年8月2日,子尤爸爸又记下儿呆“诗”一首:太阳公公将我们紧紧地拥抱/我们满头大汗/忽然一阵暴风起来/将汗吹没了。
这是诗吗?这不是每个孩子嘴里都会冒出来的句子吗?那么,诗又是什么呢?
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子尤五岁时的一天,还是去龙潭湖,登上玉带桥,凉风习习,只见西天晚霞通红,桥下水波粼粼,目睹其情其景,他突然高声吟诵: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令旁边一位老者愕然。
诗的好听和可以吟诵的感觉,使它忽然被小子尤抓过来即兴抒情了。这是他对诗的感知,也是诗的魔力。诗里说什么好像不重要,那种朗朗上口和气势,足以推动心中有它的人脱口而出。
后来还记录过子尤稚嫩的“诗”:小孩小时候/这山高又大/小孩长大了/这山低又小。(1995年6月20日)
子尤上小学前我们没有教过他认字和算术,因为经常咳嗽,幼儿园上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没有学到读和算的技术。而五岁生日我送给他的两样礼物----相声磁带和漫画书却在他心里栽下了喜笑的种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相声说相声画漫画编故事是他最好的玩儿伴。看他喜欢,我们就尽情地满足他。比如,买全套刘宝瑞候宝林的相声磁带,买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漫画《父与子》。由笑和幽默,他认识了卓别林,热爱卓别林,我们又为他把卓别林的影像资料应有尽有地收集起来;由卓别林电影又进入电影世界、还有话剧,像滚雪球一样,兴趣爱好越滚越多。原想为他打开一扇扇美丽之门,引他进去看看,喜欢了,就走进去;不喜欢,带上门进下一个房间。没想到,这个小朋友,迷恋一个又一个房间,穿行其中,乐不思返。
诗歌呢?诗歌还会找他。
1997年5月24日,还是在龙潭湖,我记下他说的两段儿,一个是《风景》:远看山哟高/近看山哟小/河水清清流/大树笑啊笑。另一个是《下雨》:天上下雨/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水落到河里/就象琴中的美丽。
如今回看,对于小孩子来说,诗是什么呢?诗不是文学,不装腔作势,不高大,是孩子的第一语言,是他首先会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去打扰他,诗就住在孩子心里,他可能会一直吟诵下去。只不过,大人常常打断他,打断这种自然天成的美妙语言,换之以一种称之为语文和算术的技术,以及其他很多门类技术,在技术的磨炼中,随着知识的增多诗的天性消弥了。
当诗的这种天性被大人从孩子的天性中抽离走了以后,有时又被扮上神秘鬼怪的样子,于是,给人们一些印象,有的写诗人是另类,玩儿高雅,搞行为艺术,抑郁自杀……。
在子尤这儿,有意无意中,我们没有剪断他和诗相连的那根脐带,通向诗歌的天窗始终敞开着。所以他一口相声,一口诗歌;一边乐呵,一边抒情,跳来跳去,平易平常。
此时,子尤更爱相声和漫画,在他写的一些顺口溜似的小诗旁都要配上漫画。诗、漫画、相声在他心里是一样的,可是,在世人那里,它们是大雅大俗。子尤不吝,不嫌弃,不骄傲,好玩儿的,有意思的,新鲜的,美的,统统收下。它怀揣着这些宝物,“一路快乐而美好”(子尤语)。
1996年9月子尤上西城区红庙小学,他继续玩积木、编故事、讲故事、说相声、模仿卓别林,迈着卓别林的步子上学,小朋友叫他“卓别林大师”。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老师在作业本上写:上课唱歌,多次制止还唱。这是怎么回事呢?子尤解释说:上着上着课,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来卓别林的电影音乐,于是便唱了出来,老师批评他,过一会儿他就忘了,还是情不自禁地唱。
从八岁起,我开始较多地带子尤背古诗。子尤爱模仿,一边背,一边开始自己写。我们家里公认他的第一首诗是讲泰坦尼克号的,名字叫《沉船》,诗云:船在海上飘/人往水里掉/要问为什么/撞上冰山了。(1998年7月5日)背了词以后,子尤也试着按格式套写,比如一首《丑奴儿》他写的是:有个孩子叫子尤/他真可怜/他真可怜/可怜时代好几年。/爸妈逼我学弹琴/特别没劲/特别没劲/希望找个新事情。(1998年10月1日)
它控诉了我们对他的逼迫,讲了自己的心情,现在来看,令我难过和自责。子尤从五岁开始学琴,学的不好,挨了不少打。显然这种生活是他不想要的,当要写诗时,首先就用来表达这份心思了。真是我手写我心啊!好在不久之后,我们停掉了琴课。又过了几年,一部萧邦的传记片《一曲难忘》令他燃起了对钢琴的向往,称要做箫邦第二。这一次他主动要求学,于是,又为他找老师学琴,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跟学技术方面实在是表现不佳,比如,他常常不按照谱子上标记的指法,自创一套,别扭而高难度,还课时令人尴尬。随着上中学功课的繁忙,我们又中止了。
子尤8岁时还用《丑奴儿》的词牌写过一个里夫演超人,最后几句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从早到晚直出气”。这成了我们家甚至朋友们的口头禅。动不动我们就说:不容易啊不容易,一天到晚直出气。
八岁时候的诗歌,最有气概的要数《中国落后时代》了。那大概是看过《火烧圆明园》的电影之后所写:披发三千丈/足有黄河长/不知何时禁止/谁能往里闯。……`
这显然是借用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在说了一年的“顺口溜”之后,子尤开始了自由诗篇。
那是2000年1月21日,子尤9岁。我们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听诗歌朗诵会,走北海、景山、故宫一路。行至故宫角楼,只见底下青光,顶上月光,交相映射,子尤吟诵起来:“北京城/你这苍老的风/我将伴随你一生……”。我真激动啊!沿着故宫围墙经过护城河,我跟子尤讲我们小时候在这儿滑冰,那时这里不这么冷清,满是奔驰的孩子和欢声笑语。“从这里延伸到平凡的滑冰场/那是我妈妈青春时梦想的地方/她在冰上自由的飞翔/不时重重地摔上一跤/嘴中的微笑却在荡漾。”他的嘴里又溜出来一段儿;到了中山公园东门,站在路灯下,雪花从天而落,“银雪轻飘/落在我的脸上,头上/一种轻爽感觉在我身上流淌/回头仰望,天边茫茫。”“在这古城中/在风雪环抱中/伟大的历史重重/雪犹如繁星,飘落、飘落/夜风习习,我在叉枝下高歌这美丽的时刻/耳边响起天空里深不可测的声音,----那是过去与未来的大钟……”。我飞快地记录,惟恐丢失。
此前,他并没有读过自由诗,并不知自由诗为何物。

接下来一首写于万圣书园的《梦幻》,也是这样。在书店里,我们各自看书,他拿起一本傅雷译《米开朗基罗传》翻看,突然走到我身边说,诗兴来了,要写。快给我一支笔,不然我的诗就要跑了。我们翻出纸笔,他坐在长方形的大木头桌子上写起来了----“那里是书的王国/我对于观书人来说太小/一个是聪慧顽固/一个是用文明之火将自己燃烧。”以后,这首诗成了他在北大附小朗诵的保留节目。
就是在九岁,子尤开始了大规模的阅读:《西游记》、《水浒》、《战争与和平》、《飘》、《简爱》、《悲惨的世界》、《巴黎圣母院》、《射雕英雄传》,从此,博览群书、涉猎古今。再次声明,这是抄子尤博客里的文字,请柳妈妈原谅。
文章引用自:http://blog.sina.com.cn/u/485cdf81010007rc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