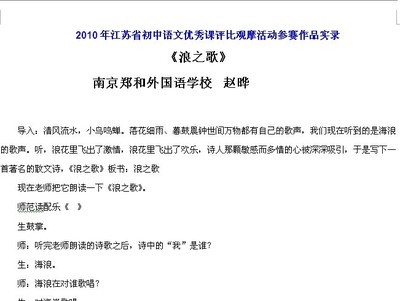评《赤子之歌》兼论贾西贝的社会抒情诗
刘光荣
贾勇虎(贾西贝)诗选集《唱响中国心》即将付梓,诗集中份量最重当数第一辑《炎黄集·中国之心》,而这辑中又是以《赤子之歌》为起因,使作者这几年来专功社会抒情诗的。诗集即出,不妨以《赤子之歌》为文本,展开述之。
《赤子之歌》是描写军转干部林强感人事迹的社会抒情诗,先后被《解放军报》《国防时报》和《作家文汇》刊载,而《解放军报》刊发近三百行的长诗,在近十年内是不多见的。诗界与评论界也随之作出相当多的肯定与评介。虽然这些肯定与评介对这首抒情纪事诗并无故意拔高之嫌,然而,我以为无论是诗界还是评论界,似乎对《赤子之歌》所显露出来的艺术形式与美学特征尚显认识不足,甚至有以讹传论之疑。读诗掩卷而答疑,遂成此评——
社会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的分野
社会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体文本,有完全不同的范式特征与功利目的,从廓清谬讹误读回归文本出发,两种文本应予划清界限。
《赤子之歌》的作者,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军旅诗人,有着相当长的军旅生活经历,正是与林强有相同的经历,他对林强的认知便显得更加敏感,当林强的事迹见诸媒体,诗人聚到了一块儿,几杯酒,一夕谈,对现实存在的失望与希望,冲撞而成为情感的激流,以林强之事而反观世态,于是便成就了这篇长诗。《赤子之歌》是作者情感寄托的产物而非某种特定意义工作的需要。
与所有的文学样式一样,社会生活是诗的母土,诗所反映的对象应当也只能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以及基于对生活原生态解读之上的理想、想象与幻象,正是个人对生活体验的不尽相同,促使诗的文本显得多种多样:或浅唱低吟,或慷慨悲歌,或吟风弄月抒一己之块垒,或感时伤怀饮族群之酒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用语言符号营造某种氛围与意境的诗,原本有普世的美学价值而没有特定的倾向性诉求,而赋予诗功利性诉求的,恰恰是诉求者本身。
政治抒情诗是20世纪特定时期的产物。在政治标准王霸天下的时候,当政治诉求高于一切诉求的时候,与所有的文学样本一样,诗被误读为一种解读政治的通俗性文本,而成为政治家的附庸或工具,工具说使诗失去了她应有的美学特质,异化成政治学卡通类小人书,这正是人们至今一谈起政治抒情诗就满脸不屑的根本所在。
文学不是工具,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承载人类文明信息的宝贵艺术品。既然是艺术品,美质则成为第一要素,作为文学样本的诗,借助意象传达具有普世价值的审美观,既是文本的出发点也是文本的最后归宿,而所谓政治抒情诗,取法于某些阶级或某个集团的政治教义,不讲艺术性或只把艺术性作为文本的陪衬,口号似的大喊大叫成为操纵时尚的强力,它所宣扬的是一种文字暴力,从文本本义去考较,无论以强力形式出现的短句具有多少穿透力、杀伤力,与其说这类文本是诗,倒不如说是分行式政治宣言或标语口号更恰当。社会抒情诗则不同,她不仅把艺术性作为文本的灵魂,而且不惜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去宣扬入本主义的普世价值。
《赤子之歌》所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用意象营造的普世价值观。“……深埋的煤层里藏着火,微弱的蜡炬还亮着光,当他的燃烧抵达所有的心灵,就会唤醒千里花丛,点燃万道霞光!”煤者何也?或窃火者普罗米修斯,或根本就是火焰与温暖。蜡炬象征光明,光明所至,黑暗消退。有句成语,叫雪中送炭,讲的就是对弱者的关怀。对人的关怀不是政治符号也不是宗教符号,而是人类互助互济的道德诉求。“大凉山冷了,你是火塘!阿达和阿嫫饿了,你是一碗香气腾腾的荞面汤……”如果说“煤”与“蜡炬”是两个传统意象,那么,“火塘”与“荞面汤”则是两个完全取材于凉山民族地区人民生活中的具象。我们通过对诗中镜像的解读,发现这两种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道具,经过诗人之手的创新运用,更显示出人道主义和道德诉求的强大亲和力。
道德不是说教,更不是强势机器。道德是约定俗成的行为范本,是人类社会积数万千年文明进化成果而成的、维系人类有序活动的支柱。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教条,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铁血机器,唯有人类的基本道德,才具有普世的价值意义。事实也正是如此,一旦社会失去了道德的支柱,就会秩序沉沦,人妖颠倒,晦明不分。贪欲者,“恨不能将国库,全搬进他的私房!……恨不能将民脂,全刮进自家的钱仓!”无权者,“对高官厚禄的暗自艳羡,对豪宅名车的莫名窥望,对美艳佳人的痴心妄想,……”没有道德的统治者是最丑陋的传教士,“当他把财富百万、千万地狂聚,当他把官阶两级、三级地攀上,当他把一百零八个情妇的头发像古玩般收藏,那些女人的发丝啊,正绕成绞索……”绞索绞杀的不仅是贪官恶吏,更是对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与人们对社会公正信仰的绞杀,前腐后继、贪污贿赂、声色犬马,社会群体性腐化心态,就是对普世价值观失落的惟妙惟肖的诠释。当人们也包括诗人无法寻求公权对恶仆现象的根本消灭时,他们就只能转向对道德的诉求。不仅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有着这种情结,基督教的末世审判,不正是放大了的清官情结吗?只不过,在东方人眼里,审判者是位好官好君主,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人类道德抽象化了的上帝。
社会抒情诗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
喧嚣于中国文坛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只是文学艺术极端个人主义的滥觞。后现代派的文学虚无主义与伊沙等人的伪经典,则是这种极端主义的标本。
当“后现代”诗评者用干涩的声音宣扬中国文学已经死亡的时候,当他们唾沫横飞用诅咒去颠覆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都举着一面相同的旗帜。后现代诗或许是一个东西,起码它拓宽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途径,丰富了后工业时代文学艺术的描述对象与叙事方法。这就像基督教或许是一个好东西一样,创造基督的教士与虔诚传播终极关怀的教士,大多是一些身体力行的苦行僧,而弄坏了这个东西的,倒是那些言必称基督的伪教士与“二毛子’,一个具有极大文化包容性的民族之所以会发生“拳乱”,与这些伪信徒的横霸乡里的暴行是分不开的。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既有文学艺术的颠覆者和谋杀者,倒是那些试图用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来限制甚至剥夺别人话语权的人,他们颠覆和谋杀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多样性,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社会良心与责任感,同时,也是对它自身的颠覆与谋杀。他们在自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送终时,并没有奉献给人们新的文学样本,甚至,他们也无法逃离自身文学主张与文化视野的局限性,当他们拔着自己的头发享受飞天的快感时,即使在他们编来钱沽名誉的伪“遗忘的经典”中、存有一些好诗好文句,也无助于他们对沉沦的自救,因为其中的许多人许多诗早被他们颠覆和谋杀过了。这些并不具备客观性与包容心的人,自大而近乎疯魔,前傲后恭表现出来的这份难得善心,让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
毫无疑义,社会抒情诗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式范本,它是对传统抒情诗文本的继承,是对文学的社会观照与人文关怀传统的继承。社会抒情诗大多意象鲜明,语言贴近社会人群而且善于歌中寓讽或讽中藏歌,具有黑白拼图式的效果,诗人的拷问与歌颂,都易于引起读者的共鸣。正因如此,在与政治抒情诗划清界限时,社会抒情诗也与以描写小我与病态的所谓中国文坛之后现代主义划清了界限。乍看上去,《赤子之歌》难免“歌德”之嫌,只有在读完全诗后,人们才会发现,“歌德”与拷问在这里是并行不悖的:歌当歌之人之事,问当问之事之情。用歌颂标高者来拷问丑陋者,扬清以击浊;用彰显德高者来梭视自己的日常行为方式,更利于净颜面正衣冠。于是,对一人一事之歌颂,通过一扬一抑、一褒一贬,由小而及大,由局部而多角度,扩张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道德观照。“歌德”在这里是一把利刃,是一面镜子,被解剖被镜照的是百态社会人生。
“也许,我们貌似正人君子,也许,我们态若清纯娇娘,但我们毕竟还不是——不是屈原不是范仲淹不是文天祥,不是刘胡兰不是张志新不是丹娘!崇高与腐朽,只在一念之间,此刻,我应该跪在我的诗行里,恳请天地正气,赏一记耳光!从今后,以光明为榜样,做事——得讲天理良心!做人——绝不卖乖说谎!”
诚信,是道德社会的基石。离开了诚信,背弃了诚信,管理者没有道德,被管理者也没有道德,整个社会必然会发生道德危机,一个道德失范的社会,对个人对人群对民族对国家,无异于天崩地裂的大灾难。
诗人的攻讦与诗的整体逃亡:中国诗坛之怪现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迄今,中国诗坛现状只能用两个词来描述:乱象丛生,每况愈下。
中国诗坛的乱象,始于冬种创作流派的兴起与相互攻讦。但这还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对诗的本质的曲解和诗人自身素质的问题。
中国60年代与“新时期”十年,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两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文艺流派多样化与表现方法多样化,成为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动力,创作者相互借鉴与兼收促成了文学艺术的鼎盛繁荣:更为重要的是,与多样化发生相对应的,是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感,作家的社会自觉使文学艺术终于摆脱政治标签而回归文学的本位。一批张扬精神与普世价值观的文艺作品,以振聋发聩的力量冲击社会生活,让整个社会耳目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抒情诗,以激情、忧患意识、富于理性的反思和传统语词与意象运用,使人们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渗透力,并在国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也因此受到人民的尊敬。
人们在衷心欢呼取得的胜利,而此时的中国诗人却开始了胜利大逃亡。
诗人的逃亡似乎源自于对传统的反叛,却又不尽如此。
传统的文人相轻陋习,较后出现的更年轻的一代诗人们对既有诗体的不屑,以及在反叛工具时,把一些非诗艺的政治命题,与诗人的责任和社会的人文关怀,不加区别地一概视为强加给诗体的难以承受之重,予以否定。诗人在倾倒浴水时,把沐浴的孩子也倒掉了。诗人们群起追逐生命之轻时,乱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新锐诗人打着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旗号,各领风骚三五日,在诅咒传统的同时,也进行着血腥的互相攻讦。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原本只是一些描述后工业时期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写作技巧与解读方法,并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性。然而,一些出于某种需要的人,却把新出现的写作技巧视为洪水猛兽,硬贴上腐朽意识形态的政治标签而大加挞伐。而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的一些人,在反批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自己意识形态化了,以暴抗暴,甚至以暴凌弱,以群体形式,对所有新时期以及之前的作家个体进行最无耻的暴力语言围殴和羞辱,同时拾起文化虚无主义的破旗,把围殴上演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盘否定。
与小说家和其他的艺术家相比,中国诗人的神经是极其脆弱的,在意识形态的攻防战中,诗人退缩进了个人主义的小木笼,神经质的个人情绪反常宣泄,神秘主义的符号组合,生命与生活变成了苍白的专用名词,中国诗人整体性为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诗,抛却“难以承受之重”时,却给诗神戴上了非理性的“难以承受之轻”的枷锁。就在中国的新锐诗人们大声宣扬自己的胜利时,诗却退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视野,成为小圈子里的风花雪月。
对于鄙视众生的诗人,无论他们自己宣称自己如何伟大如何天才,众生仍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的天才之作,只成为他们装饰自己的塑制品般的镀金王冠。
诗与人对社会责任的逃逸,使诗的颓废成为必然。中国众生并非不喜欢新诗,而是不喜欢泛滥成灾的那些个人主义自大狂的伪诗——他们许多人连自己写的什么东西都不能解读,于是宣称留给后来的某个世纪的诗歌爱好者去解读!!!阅读是个人的习惯,无论自称后现代主义的诗人的语言库中藏有多少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对根本不读伪经典的读者众生来说,即使慈善者手里牵着比尔•盖茨,他们也绝不为孓萤独照的诗人买单。
中国文学史,从某个角度去看,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诗歌史,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也是读着这部诗史长大的。从诗言志到文兴邦,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到今天的艾青贺敬之郭小川李瑛或舒婷郭沫若闻一多,无不讲的是诗的代民立言,甚至为民请命,只有诗歌敢于代民立言,诗人敢于请命,诗和文学才能获得空前的发展。新时期十年,诗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无不与此有关。如果说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兴盛是一面镜子,那么,当我们用这面镜子来对照这之后的中国诗坛,我们就可以为冷暖两重天的诗坛公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当代诗坛的颓败,是因为那些自称为天才的诗魔谋杀了诗和诗神。

就在我们为当代中国的诗潮黯然消退而扼腕叹息时,一篇《赤子之歌》赢得了媒体的追捧,并获得数位公认的老一辈社会抒情诗人的好评与批评界的青睐,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究其原因:仍然是诗篇中一以贯之的道德力量与艺术力量,是诗人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
“你日日忧的是——/民情、民灾、民荒……/他夜夜想的是——/权力、金钱、娇娘……/你想把心血全部献给大众,/他要把天下全部填进荒唐!”“也许你的功绩会带来加官晋爵,衣锦还乡。你还会不会时时刻刻,惦记着‘他人瓦上霜’?是否会,一掷三十亿;像陈良宇那样:狂妄,荒唐?”“到明天,面对钱权围剿,你能否招架?而对糖衣炮弹,你也许不能,像当年听到冲锋号那样?”
无论社会抒情诗以传统派或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道德拷问、社会拷问与良心拷问,无一例外是这类诗体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一基本艺术价值取向,赋予了社会抒情诗极大的道德震撼力与艺术生命力。“崇高与腐朽,只在一念之间,”离开了这一基本特征,社会抒情诗就失去了她的社会性与人民性,堕落为某种“工具”,于此,给甘心做这份工作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提一建议,无妨据此对当代诗歌进行一次梳理,精选出一部社会抒情诗选或者大全,为寂寞的诗坛重新寻回生机。
全能的诗人与全能的读者:镜像与法相
无论是传统的中国诗人还是后现代主义诗人,似乎总喜欢以全知全能者的面貌出现在读者众生面前。
前者板着一副圣人学究的面孔,唯恐孺子不可教也:后者则拿着“先锋”的洋枪洋炮,不屑与贩夫走卒甚至他们的老祖宗为伍。岂知,圣人学究的诗人首先是普通的职业人,在当今社会,更是专以诗文换钱沽醉的职业鬻诗者,如果圣人学究们自己尚不能“言为心声”,如果自己尚不得精神自由,又何以能教化天下呢?这些人陶醉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环里,自大而狂妄,实则他们不是“人”而只是工具——即使是一部百科全书,也只是工具而已。而那些自命不凡的“先锋”与新锐,他们自以为是为上帝立言,为后世规范,要么视读者若无,并羞于与其讨论诗艺旨趣,要么则一开口就满嘴洋大人语录,吓唬读者也吓唬自己,其实,他们的先锋与新锐,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而且是最蹩脚的拾牙慧者。如果再仔细看看他们手中的洋枪洋炮,那上面隐隐约约却真真切切地写着“中国制造”的方块文字。
中国诗歌无疑是世界上发育最成熟的文学样本之一。从《诗经》到盛唐,再传至宋,历经千年,从诗体到流派,中国诗歌都达到了至今无法逾越的高度。中国古典诗歌20世纪初叶被译介到了西方,在诗歌界所引起的反响,无异于掷下了一颗原子弹。一批后来获得诺奖的外国诗人,对中国诗的意象构置与意境营造有着一种如饮醍醐的感悟,并以此去改造被他们称之为传统的表达方式而获得成功,创作了一批意象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诗作,最终获得读者与社会的认同,正是这批诗人,被文学界(史)称之为“意象派”或“现代派”的新流派,无几工夫,便蔚成文学艺术的创作主流。如庞德等。这些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得新的表达方法和创作方法的诗人,怀着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感恩心态,自称为孔夫子的信徒。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诗不需要再发展,我们是要说,对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们要学会敬畏与尊崇,对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与精神自由,要学会继承与发扬,对中国的读者,要学会尊敬,并承认他们的再创造力和再创造权力。
与上述两类诗人相反,《赤子之歌》的作者对优秀传统的敬畏与尊崇、对忧患意识与精神自由的继承与发扬、对读者的尊敬,都具有镜子的作用,很值得我们的圣人学究与先锋诗人去效法。
一般说来,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意象、意境乃至意义,都处于一种自在之物的状态——对于作者来说,它是自由的,而对于读者来说,它是非自由的。如果说作品是一面镜子,作品所蕴含的意象、意境以及意义,就如同镜中之像,不同的读者,以至同一位读者,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心态时,都可能解读出镜像所蕴含的不同意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作品所进行的再创造的必然结果。此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本《红楼梦》,理学家读到的是“礼”,政治家读到的是阶级斗争,经济学家读到的是社会经济运行结构,而当今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学家”们,读到的却是秘史秘闻与花边新闻。对同一镜像作出如此众多的解读,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某一读者不强求所有的读者都按照他的解读方式去阅读,这就像诗人并不把自己的解读强加给所有的阅读者一样。如果诗不是刻意让人只看到一个极其模糊甚至暧昧的镜像,无论是意象的构置,意境的营造,语言的运用,其实大可不必故弄晦涩的。新奇是一种技巧,清新更是一种大技巧,新奇而清新,才能为读者之所爱。
这也是《赤子之歌》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该诗全无故意猎奇的技巧卖弄,诗中的意象,全然来自现实生活,语言晓畅易懂,其中闪耀着的思想火花,绝不会因为阅读不畅而产生歧义。
“苦了你们哪,/阿布洛哈的老乡!/从此,省城来的这位处长/就是你们:阿布洛哈的子民!/你们的路窄,我愿用臂膀,/把山路垫宽畅:/你们没有电,我愿用热血,/让山村的星斗发光……”
诗人用近乎白描的方式,用口语似的语言,把一位视山民为亲人的“清官”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紧接着,诗人仍然用同样语言,描述了林强关心山民生活疾苦不惜倾尽自己家财的崇高之举,使这个“清官”形象因此而获得极大地丰富,升华成一种人格与道德的力量。尤其可贵的是,诗人的歌声并未就此而打住,而是展开类比联想,把美与丑、清廉与贪婪、爱民与虐民、清与浊、此时与彼时、此人与彼人,此人与诗人,以黑白拼图的方式,用道德的光辉去烛照,用道德的力量去检视,全景式地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真实存在现状。
用社会存在的真实性去实现诗歌形象的真实性,是社会抒情诗的又一特色。正是这一特定的表述方法,使社会抒情诗具有超越个人抒情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巨大的社会生活容量,使诗歌能从更加宽阔的社会视野去表现人文精神,有效地传播普世价值观。
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就是诗歌的法相。无此法相,当代诗歌就只能走进死胡同,而彻底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借用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有的人的诗,千百年都有人读;有的人的诗,他自己都不爱读。
(作者系著名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曾任《当代文坛》编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