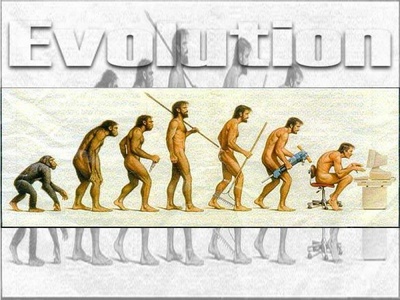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禅学:不仅要口说(明白),更要心行(修行)。要做到心口一致。综上所述,可见心学与禅学是一而不是二。他们都把人摆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元明以来,理学笼罩和窒息了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使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了一派灰暗沉闷的现象。人们用理学所圈定的哲学观去观察天地万物,认为这天地万物都只不过体现了“天理”或“道”;用理学所规定的封建伦理去束缚人的生活与行为,认为人的种种欲望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要求和情爱、友谊、嗜好、追求等精神生活要求只不过是种种肮脏的欲念,而它们必须服从于所谓“天理”;用严格的等级尊卑、上下有序的政治观去维护封建制度,认为人们的一切都应该围绕着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目标,恪守三纲五常的原则;理学还渗透了文学、艺术、史学等各个领域。
在沉闷而禁铟的空气中,很多士大夫都感到了压抑和痛苦。物极必反,在举世陈旧得令人厌倦的思想氛围下,却激起了一股挣开手眼,别求新格的时髦思潮,正象围困在破旧不堪的大堤之中的洪水,一旦堤岸出现缺口便四处横溢那样,厌旧喜新成了一种时代心理,王阳明以陆氏心学及禅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氏心学,便是这种时代心理的产物。《日知录》卷十八《心学》说得很对:
“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其从来,而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
据说,有一天王阳明漫步走进一所寺庙,各间禅房都大开着门,只有一间是“铁将军把门”,关得紧紧的,僧人不让观看。可是王阳明执意要进去,僧人无可奈何,只得让他进去。王阳明进门一看,原来里边龛中供着一个入定的和尚,这和尚长得与自己一模一样。沉思良久,忽抬头看见壁上题了一诗:
“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 始信禅门不坏身。”
于是心中一动,思绪万千。① (明刘仕义《新知录摘抄·王阳明》、(《纪录汇编》本卷二一六)。)
说王阳明是禅僧转世固然是无稽之谈,但王阳明心学乃是禅学变种却不无道理,否则就不会有人这么编造故事了。王阳明自己就一再说过: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②(《阳明全书·重修山阴县学记》。)
的确,在王阳明那里,“性善”论与禅宗的“本心清净”论是合二为一了,孟子的“求其放心”即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和禅宗“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是融为—体了,禅宗的“直指本心”的简便解脱方式披上了儒家的冠冕衮衣,还取了个名称叫“致良知”,就象禅宗南宗的简易功夫击败了北宗的繁琐方式一样,直截明了的王氏心学逐渐取代了步步推进、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王阳明有一首《示诸生诗》说得最明白: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
业,漫从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
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③(《阳明全书》卷二十。)
你看,这不是禅学又是什么?据《池州府志》说,王阳明曾与池州太平山禅僧谈禅,你来我往,心下欣然有悟,便作了一首偈语:“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到巉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留得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时,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看来,王阳明是把禅宗的那一套从里到外都弄得滚瓜烂熟了。所以当时一个著名学者陈建说他是“一生所尊信者达摩、慧能,而于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满”。①(《学蔀通辨》卷九。)而刘宗周就干脆称之为“阳明禅”②(《刘子全书》卷十九《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
正如陶望龄所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③(《歇庵集》卷十六《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之十。)王阳明公开扔掉了反佛的儒家原则,填平了儒佛之间最后的一道沟壑,心学便率领着士大夫们掀起了禅悦之风。
一个巴掌拍不响,士大夫向禅宗眉目传情,禅宗也向士大夫们频送秋波,他们一面清理门户,批评佛教末流、狂禅之风是“大言不惭,不守毗尼,每自居于旷达,不持名节,每藉口于圆融,迨一旦逐势利,则如饿鬼觅唾,争人我,则如恶犬护家。”④(明释元耒《续寱言》。)憨山禅师还告诉人们,“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①(《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九《学要》。)他们不仅这样向传统儒学靠拢,而且还投士大夫所好,雪浪以诗书与士大夫交游,“三吴名士,切磨殆遍,所出声诗,无不脍炙人口,尺牍只字,得为秘珍。”②(《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十《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翁大和尚更指示禅宗僧人们“以禅教为本业,然欲通文义,识忠孝大节,须先从儒人”,所以聘请了儒生文人来教授四书五经子史诸书,以改变僧人们与士人不能交谈,举止粗陋的现象。而达观、德清等名禅师还跟在王阳明心学后面,七嘴八舌地对陈旧的程朱理学进行批评,并宣称朱熹的那一套只有五百年寿数,到这时已经应该寿归正寝了。因此,他们赢得了“厌常喜新”的士大夫的青睐③(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紫柏评晦庵》。)儒禅携手,缔结了两家的姻缘,花样翻新,吸引了众多苦于沉闷空气的士大夫,功夫简便,又解放了许多压在四书五经繁琐细碎功夫和八股程文之下的举子。禅悦之风并没有随着异端运动一起消亡,士大夫们仍然醉心于习禅礼佛、静坐焚香、交结僧人,只是在这时起作用的不再是禅宗的积极叛逆精神而是消极保守的出世哲学,不再是一种异端思想而是士大夫正统思想之外的精神补充了。到明清之际,很多有气节的士大夫躲进和尚堆里,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们的气节,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禅宗虚无主义人生观和自然清净生活情趣的影响。这后一方面对于士大夫的影响,一直到清末始终未曾衰减。至于清代禅宗与士大夫的交往,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清代一方面重兴儒家经学,士大夫在主导思想上大都仍然恪守传统观念,以讲求义理、训诂考据为己业,心理上都是极封闭内向的;另一方面禅宗在士大夫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补充结构,成为他们闲暇时表示高雅澹泊的一种手段,失意时使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我安慰。所以,禅悦之风依然很盛。清初人李元阳说:“故达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托而逃……其淡泊之
操,凝静之域,又岂浅学所能测。”①(《云南通志》卷十三引。)其实,他并不必故弄虚玄,逃禅,只不过是“涉世”之余的出世而已。清代士大夫大都如此。所谓“淡泊之操,凝静之域”,只是在内心世界中追求尘世所难以获得的心理平衡。它与儒学——理学那种“三省吾身”、“求其放心”、“过犹不及”的人生哲理一起,作为传统人生观中积极入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补结构,一直保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因此,禅悦之风从宋代到元、明、清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回到了宋代原来那个起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就够了。受禅宗影响的王阳明心学与禅宗人生哲学,甚至还包括西方思想文化合力影响下的产物。李贽与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三度相会”,极力赞扬利玛窦为“极标致人”①(《续焚书》卷一《与友人》。)。焦竑也与传教士们颇有往来。传教士从西方带来了一些科学知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及稀奇古怪的洋玩艺,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士大夫的眼界,特别是利玛窦,曾在中国画过世界地图,是最早把世界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来的学者,无疑这会使中国士大夫为之一惊。李贽曾着《四海说》一文,也论述了“正西无海也,正北无海也,正南无海也……所谓海者,仅仅正东与东南一带耳。”这使得士大夫们顿时感到“世人之所见小”②(《雪庵清史》卷一《清景?十洲》,参见《涌幢小品》卷十六。)。不过,心学与禅宗应该说是这场狂飚式的思想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它提供了基础的话,心学、禅宗与市民思潮的碰撞,则是在士大夫中掀起这场思想运动的主要推动力。这场思想运动的中坚人物如李贽便是禅宗思想的狂热信徒与心学的大胆引申者,更不消说他本人曾落发为僧过了。袁宏道同样也是禅宗的信奉者,他给他女儿起的名字就“禅那”③(《珂雪斋近集》卷三《袁氏三生传》。)可见这个当父亲的热烈追求的目标。据说袁宏道十分自负自己的禅理知识,认为天下仅李贽可以与他匹敌,而多年修行的和尚们都常常败在他的手下。这固然有些过头,不过董其昌倒是的确看出了他与众不同,说:“迩见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镜录》与冥枢会要》(道教著作——引者)较精详,知其眼目,不同于往时境界矣。”①(《画禅室随笔》卷四《禅悦》。)汤显祖则自己承认“师明德夫子(心学大师)而友达观(紫柏禅师)”②(《法苑珠林》卷八十五。),极心服李贽,对禅宗也十分崇敬和信仰。其它一些骨干人物如董其昌、陶望龄、王思任等,也无一不是禅宗居士,与紫柏、憨山、雪浪等禅师关系极为密切。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禅宗思想与他们的异端思想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首先,禅宗的大胆怀疑和叛逆精神影响了这批士大夫,启迪了他们的异端思想。禅宗呵佛骂祖、横说竖说本来是从“我心即佛”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对于禅宗来说,一切外在的戒律、神圣的偶像、经典的教条都是多余的,我的心不仅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又是一切行动的天经地义的出发点。是邪非邪,全凭我的主观判断,所以,禅宗极力主张的是“不疑不悟,大疑大悟”。过去早期佛教拘泥于一字一义的穿凿领会,如《大集经》说:“菩萨为于一字一句之义,能以十方世界珍宝奉施法王”,《大方便报恩经》说“为闻佛法,乃至于一句一偈一义”②(《法苑珠林》卷八十五。),而禅宗却蔑视经典,认为它只是“拭疮疣纸”,“卖田账簿”,否定拘泥于教条的僵化方式,只承认自心的权威性,所以常常“非人之是,是人之非”,如《龙修济禅师语录》中有一则:“僧问:古镜未磨时如伺?师曰:照破天地。曰:磨后如何?师曰:黑漆漆地。”①(《御选语录》卷十五(《禅宗集成》本册十三)。)《水月斋指月录》卷九又有一则:“(智常)入园取菜次,乃画圆相围却一株,语众曰:辄不得 动着这个。众不敢动。少顷,师复来,见菜犹在,便以棒趁众僧日:这一队汉,无一个有智慧地。”m老老实实听话是无智慧,不听话反是有智慧,镜不磨能照破天地,磨了反而黑漆漆地。看来颇为奇怪,其实正是禅宗本色,因为禅宗认为人人本心是最神圣的,从这个本心理解去,便必然是对的,对他人言语行动有疑,才能合符自己的思考,才能顿悟。这就叫“若是其人,唤作游戏三昧,逢场设施,无可不可”②(《长灵和尚语录》(《禅宗集成》本册十四)。)。因此,禅宗把有悟性的人叫做疑者,认为参禅者必须有“大疑情’③(《禅家龟鉴》(《禅宗集成》本册四)。),明代禅僧成正所集的《博山和尚参禅警语》卷下说:
“做工夫贵在起疑情,……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
悟,不疑不悟。……通身内外只是一个疑团,可谓搅浑世
界,疑团不破,誓不休心,此为工夫紧要。”而与李贽、汤显祖、董其昌等交往最多的紫柏也说:“唯彻悟自心者,即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矣。”④(《紫柏老人集》卷十五《跋黄山谷集》。)因此,明代中后期异端思潮正是从对理学的怀疑开始,由专唱反调而大盛的。在程朱理学笼罩一切的时代里,王阳明开了第一炮,紫柏、憨山等禅僧也加入了对理学的批判大合唱,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等人正是沿波而起,张而大之的主力军。倒是两个保守派官僚看出了其中的奥妙,邓元锡说:“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①(《明史?邓元锡传》。)中国禅宗的崛起、兴盛、衰亡,也证明了这一“整合”作用的客观存在:正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玄学之风与士大夫日益高涨的理论思维兴趣,使印度佛教逐渐中国化,正是这一时代士大夫追求适意自在的生活情趣,使佛教禁欲主义人生哲学逐渐转向了适意自然人生哲学,正是中唐社会危机与士大夫生活信念的变化,士大夫既想解脱又难以忍受苦行的要求,使禅宗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正是宋代社会表面的繁荣与内在的虚弱和士大夫空虚、幻灭感的上升,使禅宗达到鼎盛;正是市民思潮、士大夫对理学长期禁锢的厌反情绪与王阳明心学的携手,促使了禅宗在明中叶的再度重盛,并起了对传统观念冲击的作用。当然,这本小册子也从“积淀”的角度分析了禅宗出现之后给中国士大夫的心理性格、人生哲学、审美情趣等方面带来的影响。禅宗是从印度禅学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内省反思方式及主张内心清净、生活澹泊以自我解脱的思想,促使了中国士大夫心理越加封闭、狭窄、脆弱,性格越加内向克制,越加追求一种清静悠远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越加忽视逻辑思维而偏向直觉思维。这就是历史的逻辑的演变线索,通过“积淀”,与“整合”,我们是否可以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变化怎样作用于社会心理,并通过社会心理影响各个文化领域的变化,是否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怎样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心理,并对于社会的变化施加了它的影响力呢?

| 中国禅宗历史-六祖慧能、坐禅顿悟修行(1) | 禅宗人生哲学的演进-从禁欲到适意(2) | 宋代士大夫与禅宗的交往史-苏轼、程颐、黄庭坚(3) |
| 王阳明心学与禅宗思想发展(4) | 禅宗人生哲学的演进-从适意到纵欲(5) | 禅宗人生哲学的演进-狂禅与纵欲(明代)(6) |
(分类:禅宗历史以及公案解读系列之三NO.3,读书笔记整理,共 6 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