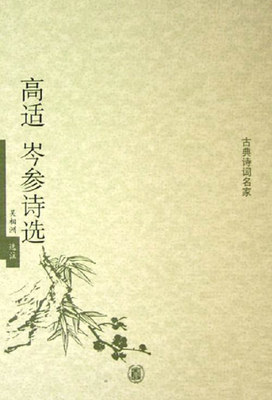高适和岑参皆为以边塞诗著称的盛唐诗人,与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不同,高岑二人都有着亲临边塞的生活体验,因同样强烈的入世精神而诗风相近。然而,高岑诗中的“悲壮”风格亦有所差异,在《燕歌行》和《走马川行》两手代表作中,即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

两首诗通读下来,自然而然会使人联想到西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两甥舅将军——“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燕歌行》,词采质朴,沉雄质气和雄浑骨力一如卫青将军,坚毅隐忍,是一种低沉的悲壮;《走马川行》则不然,“虎骑闻之应胆射,料知短兵不敢接,车行西门伫献捷。”的大气磅礴,字里行间流露英雄年少,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壮志,大有冠军侯霍去病的青年蔡俊之意气风发,是一种激昂的悲壮。可以说,同样是描写飞沙走石,征人未还的悲壮场面,高岑两人却呈现出两种感情基调。前者悲胜于壮,后者壮免于悲。高诗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日落斗兵稀”大漠孤烟、金戈铁马的战场冷酷无情,戍守边关的将士们奋勇杀敌,终落得功名未定,马革裹尸的凄惨结局,与此同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京城里依然君臣同乐,沉溺声色,夜夜笙歌,面对战场冷酷,将兵日亡而不自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描写得真挚感人,不忍卒读,悲凉之意溢于言表;而在岑参的《走马川行》中,“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烽烟飞起,大将出师,在细节中刻画行军的苦寒,笔墨酣畅,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不畏艰难困苦的战斗豪情,雄浑刚健的内容与急促有力的节奏契合无间,更增激越的豪情壮志。
除了在感情表达上高诗低沉浑厚,岑诗高昂铿锵外,二者在内容描写上也各有千秋,侧重点不同,高适的《燕歌行》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上,而不再自然,在叙事抒情中伴有写景,不脱现实主义本色;岑参侧重在自然物象的描摹,多表现塞外的雄奇壮丽,使诗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比如说,《燕歌行》中写道,“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战场厮杀惨烈的壮大场面,对人民的高尚爱国之情予以充分的肯定,热情的赞扬。而岑参在《走马川行》中写塞外的严寒,狂风的威力,“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在大漠中本该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条件,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奇伟之景。原本真实壮阔的塞外场景,加之夸张的想象,而且笔力警拔,便具有了“壮”而“奇丽”,“壮”而“俏逸”的趋向。与高适寓情于景,缘情写景,创“有我之境”的“铁衣边戍辛勤久,玉簪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人物刻画为主不同,岑参在处理情和景上,大都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创“无我之境”。如《走马川行》,写大军出师的雄壮声威,诗人却写了云海茫茫,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紧接着写行军的艰苦:“风头如刀面如割,毛马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寒风扑灭,痛如刀割,滴水成冰,严寒无比。通过一系列严峻阴恶的景物描写,从侧面显示出唐军的英勇无畏,雄视一切,预示出战胜的必然之势,故而结尾以“车师西门伫献捷”,表现出岑参的乐观豪迈。
第三,高适与岑参在写作手法上亦表现出了截然相异的艺术特点。岑参诗风“奇峭”,诗作中常常注意锤字炼句,以达到意奇语亦奇的同意,如《走马川行》中的这几句,“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马毛带雪汗气蒸”,“黄”、“吼”、“蒸”几个动词,寥寥七字便已十贴切传神,黄山满天,形容词或用作动词,瞬间将静止的画面活了起来,;夜黑风“吼”,吼出了环境之险恶,最后一个“蒸”字,将肃杀的寒气跃然纸上,不可不谓之“神”也,高适却不大追求奇字奇句,对景物亦不大注重细致的描绘。如《燕歌行》结尾四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不仅意态苍凉,而且呈现出一种质朴浑厚之美。作者在诗中不忌讳言征战的艰苦,但不失奋发高亢的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中,更平添了出赛征战的慷慨悲壮。故全诗虽多用对偶,却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取胜。
简言之,在《燕歌行》和《走马川行》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高适、岑参的诗歌,在“悲壮”的总的风格之中,又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高诗悲壮而质朴,岑参的诗却悲壮而奇峭。
其实印象中,总觉得唐诗是最早接触的文学,现在想来,似乎也全然不算了解,高岑的诗歌都没有好好读过,写个作业全靠东拼西凑,果然还是很不通顺,没有思想和主题可言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