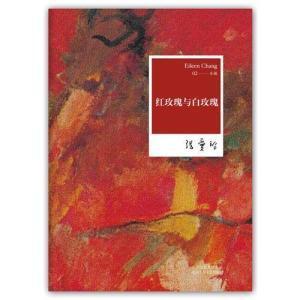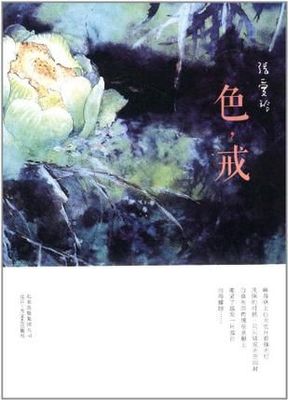平剧艺术里存在着以张君秋为代表的张腔,四十年代风靡一时,至今仍是广泛传唱的主要腔派。相应的,小说界亦存着“张腔”。小说界的张腔以张爱玲肇始。张爱玲以其独特的作风与细腻的文笔,屹立了文坛五十年。一九九五年,才女张爱玲在香港遽逝,众人皆悲叹惋惜,但张派并未因肇始人的仙逝而从此中断脚步。自一九六一年始,夏志清教授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首次以专章讨论张爱玲,将这一上海通俗女作家首度放入了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为整个文学界对张爱玲的认识都提出了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六十年代后一辈辈的港台作家,甚至海外作家,不少都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过模仿,亦逐渐形成了张派,使张爱玲的写方式与风格得以延续。张派传人,中港台海各有代表:大陆有生于上海的王安忆,台湾有“张腔胡说”,多重折射的朱天文;而相对于香港而言,似乎传人较少。当代以来,香港作家中被认为颇有张派余韵的,当中莫属钟晓阳与黄碧云。
张爱玲生前独步于上海文坛,又于一九三九年考入香港大学专攻文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念欣指出,香港与上海的双城关系,使得香港著名女作家一出道就依稀是半个张派门生,然而关键在于“才女”的身份。(《花忆前身——黄碧云VS.张爱玲的书写焦虑初探》,《十二女色》附录,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当代香港的张派传人钟晓阳与黄碧云二人恰恰似乎都合乎这一条件:才情横溢,少年老成。尤其是黄碧云。在黄碧云的首部小说集《其后》的背页有一段由出版社形容她的文字:“如此年轻,如此才情横溢,却又如此苍凉酸楚,这‘扬眉女子’也算是世纪末香港的独特产物了。”在这一段文字中,出版社将黄碧云定位于“年轻、才情、横溢、苍凉、世纪末”,而这一系列定位,实在有张爱玲的影子。而这又仅是在文字表面所呈现的一些张派的特征。纵观张爱玲的生活背景与生活环境,思想意识与写作姿态,实在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黄碧云本身对张爱玲的写作提出过质疑:“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很精到。语言华丽。但却是没有心的小说。我以为好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人文情怀:那是对人类命运的拷问与同情:既是智性的亦是动人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属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好像一个饱受什么命运蹂躏的老女子,喃喃的在黑暗房间里数钱,一边埋怨自己命运坎坷,一边喃着要将穷租客赶走,租客已经什么钱都没有,又病,又有孩子,好麻烦,没钱就睡街,不要租她的房子。张爱玲好势力,人文素质,好差。”且不论黄碧云对张爱玲的认识是否存在偏颇,言论是否有过激之处,仅凭她的话就可以看出,黄碧云在写作理念上与张爱玲是有所不同,甚至差异深远的。即使如此,黄碧云仍然在小说的各部分细节中表现出了张派传人的特征,其人生路途也在某些程度上与张爱玲有着相似之处。
城市与张、黄二人的女性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五四”开始,似乎女作家的创作就与“城市”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当代海派传人王安忆有观点认为,现代都市是为女性而设的,同时亦为女性提供了实施发展自我的空间:无论是一九二零——一九四零期间的女作家丁玲、庐隐、张爱玲,还是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张洁、陈染,甚至台湾女作家林海音、三毛等,似乎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女作家都有城市生活经历。这一现象也就意味着现代都市对于女性作家的写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并存在有孕育女性作家创作的深厚土壤。那么,现代都市产生以前是否存在有完全意义上的女性写作?
古希腊文明催生了欧洲文明,欧洲文明进一步催生了现代文明的产生。由源头可知,现代文明在本质上具有“城邦文化”的特征。现代哲学家罗素指出:“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文学上的卓越人物全都是和富庶的城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些城邦往往被野蛮人环绕,但希腊文明本质还是城邦的”。当城市文化具有个体自由时,科学与艺术才能得以发展。而“城市”的产生,需要“城”与“市”的结合。“市”是进行商业活动的根本场所。没有商业活动的逐利行为,城市也就随之失去活力。而各地商业活动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城市的差异性。相对于乡村村社文化中整齐划一的要求,城市中商品文化的繁盛构成了对个体、自我的尊重与宽容,并逐渐演变为都市文化的特性。都市文化中所具备的容纳与包容性更能使人的个性得到释放与张扬,更易为女性活动提供发展空间。这也使女性作家天生具备的细腻观察与品味生活的特性得到了自由发挥。无法否认的是,古代出现过女性写作。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增进了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业随之兴盛。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父权的集权型,中国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社会边缘,只有贵族女子才有权利接受教育。同时,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评价标准中的典范女性形象被要求与市井保持距离。这一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女子观察社会的视角是狭窄的。所以,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女性作品多为写闺怨的诗作。在体裁上,出现散文的情况几乎为零。这时期的女性写作表现的是在父权控制下的幽怨心情,并未表现出更积极广泛的视角。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不能算是完全意义的女性写作。
丹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与周围风俗。张爱玲兴盛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与上海四十年代特殊的精神气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上世纪四十年代,最具影响性的事件是上海的战事。八一三事件爆发后,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战事的爆发,原计划去英国留学的张爱玲被迫改入香港大学学习文学,香港沦陷后又不得不重返上海。因为战争,张爱玲做出了以文为生的选择。这一点不仅与其自食其力的个性有关,因为“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6页)。于是,一九四三年张爱玲带着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拜访了周瘦鹃,二稿很快得到了发表。随后,张爱玲更多的作品面世,在已成孤岛之势的上海掀起了一阵“张爱玲”热。
张爱玲生活的主要范围是上海与香港。自小生活在上海社会里的张爱玲,对上海形成的城市文化也更有认同感。张爱玲出身于上海城市的发展,自然也给张爱玲这样的女性作家提供了空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外滩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都市大街车水马龙,一派兴盛的都市景象,“形成了一个杂糅的城市空间”(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P12)十九世纪后接连而起的起义及战争爆发、军阀混战,使得江浙一带的地主士绅纷纷前往上海避难,给上海杂糅了华洋的城市空间增添了几分遗老遗少气息。而张爱玲也时常通过这些来展现上海的都市生活。张爱玲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而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也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上海城市中特有的一种华洋、中西文化杂糅的状态,从而展现出一幅沦陷时期上海人所特有的性格面貌。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遗老遗少还是新公寓里的洋场新人,都沾染着一股都市环境逼压出来的世故练达、精明算计的“上海气”。
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但实际上,张爱玲小说中的战争无处不在。张小说中的战争,通常表现为家庭内部冲突引发的战争及男女情感之间的角逐。小说《倾城之恋》在一开始发表时,就有注释“两个人的战争”。事实上,出现在《倾城之恋》中的战争,绝不止白流苏与范柳原二人的情感角逐,亦包含着白流苏与其兄嫂之间的家庭内部战争。白流苏与范柳原为情而争,与其兄嫂为钱而争。离婚后回到娘家的白流苏因兄长做投机生意败光了自己的本钱而心生不满,而兄嫂又因其常年吃住在娘家而怀有怨言。流苏的前夫一死,所有的事情都推上了台面。流苏的哥哥首先劝流苏回去奔丧,继承家产,以便落叶归根;当流苏点明他是花光了她的钱而怕她多心时,兄长就收起了虚情假意的面孔说道:“你住在我们家,吃在我们的,喝我们的,从前也还就罢了,添个人不过添双筷子,现在你去打听打听看,米是什么价钱?”四奶奶先以“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起钱来”作为开场,随即引出了真心话,将白家兄弟做金子做股票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白流苏的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白流苏受到兄嫂排挤,只得寄希望于寻一门可靠的婚事,并通过这桩婚事拜托自我的生活困境。白流苏与家人的战争不仅表现于此,更表现于对范柳原的争夺上。范柳原本是介绍给妹妹宝络的对象,四奶奶虽然暗中为女儿使劲,但会跳舞的流苏最终赢得了范柳原的青睐。流苏自此也就决定用自己的前途下注,与花花公子范柳原周旋。流苏需要的是一份靠得住的婚姻,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兄嫂的排挤,而范柳原寻找的却是一时的情感刺激。范柳原将白流苏带至香港后,流苏算是基本上结束了与兄嫂的战争。但由于范柳原不打算结婚,流苏与其的战争也由此正式开场。“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两个人经过了一番一张一弛的较量,最终总算是走到一起。但刚同居一周,范柳原就要前往英国,白流苏为此相当苦恼,她深知“没有婚姻的保障,留住一个男人的心是很痛苦很困难的事”。但没有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范柳原只得中途返回与流苏结婚,过起平常的生活。至此,两个人的战争也算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张爱玲就是以家庭内部争斗及男女情感角逐来表现战争,从而来展现特殊时代的上海城市气息。因战事的爆发,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涌进了不少避难的遗老遗少;同时,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租界的存在,上海的氛围呈现一种杂糅的文化氛围。战事的影响使得居住环境变得拥挤逼窄,都市生存出现巨大压力。在两个条件的综合催促下,沦陷时期的上海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世故练达、自私重利的商业精神,生存在沦陷区的人们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以求自我生存。亲历了沪战与港战的张爱玲,在战争中充分体会到了世事的无常与人情的淡薄。时代的战争可以结束,但是出现在人与人之前的战争,即使结束了,阴影也无法消除。在张爱玲看来,“个人即使等得及,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张爱玲所提到的“惘惘的威胁”即是她在战争里所感受到世故练达、人情淡薄的城市气息。而这一切,都成为了张爱玲细腻内心下的书写状态。读者通过作品所认识的张爱玲,细腻幽怨,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诠释女人内心及两性关系。这些女作家与生俱来的特质,也在城市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可以说,现代都市文化释放了女作家张爱玲的女性气质,提供了让她书写的题材与空间。
相对的,黄碧云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正式发表小说要到八十年代。黄碧云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战事的影响,但丝毫不妨碍她表现出现在属于她的特殊时代的城市风貌。黄碧云处近二十世纪末的香港,而此时的香港文化处于西方与东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将西方看成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在这种话语前,东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香港的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香港在逐渐脱离殖民地处境中,由于教育问题使得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隔膜,对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样难以深刻洞悉,因此,这种不中不西的处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但是,香港社会的开放性变成毫无选择地输入外面的东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来不是由于真正的国际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与自我认识。香港文化的历史资料散失,缺乏研讨和整理,教育方面从没有本土文化历史的反省,同时,本土的文化活动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识。然而相对于本土文化而言,香港人民自幼所受到的西方文化教育更占上风。加上香港社会的开放性,更促使了香港人民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到了二十世纪末,因为殖民历史所造成的影响经过演化成了新的后殖民环境。
张爱玲小说中同样具备有一定的异国情调,但是,小说中写洋人透彻异常,而处在殖民世界的中国人“仍不脱‘共谋’与‘抵抗’两种心态”。(黄念欣,《花忆前身——黄碧云VS.张爱玲的书写焦虑初探》)而黄碧云从小生活在开放的、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社会,并且有多国游历求学的经历,因此对于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认同性。这一点通过观察黄碧云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便可以得知。黄碧云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多变,心理表现复杂,比张爱玲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要丰满多变得多。黄碧云的许多小说中有大量外国人作为主角,长篇小说《血卡门》中,许多被书写的跳舞女性都是西班牙女子;小说《其后》中的日本男子平冈与《温柔与暴烈》中的孟家拉男子阿撒都展现出崭新和复杂的异域视角。黄碧云书写外国人形象是完全以平等的视角,在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英国人不再具备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也不是单纯地为了猎奇而探求东方色彩,例如小说《失城》中,伊云思生死烦恼也是其困扰;在《血卡门》中,小说中的西班牙女子为了爱一个乐手,同样饱受着爱情的折磨。香港的开放与逐渐形成的后殖民环境,给了黄碧云后殖民叙述的机会,且作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运用于小说之中。黄碧云因为拥有游学多国的生活经历,这对其视野的开拓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黄碧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并获得了犯罪学的硕士学位,这就意味着作家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同样有着一个更理性的思考方式。因此,黄碧云小说中的后殖民叙述与张爱玲作品中所带有的殖民主义不可同日而语。黄碧云的后殖民叙述与时代相关,这一点也得到她个人的认证,“这一点当然不是跟人能力的问题,二十时代和环境让她走出局限而已”。(黄念欣,《花忆前身——黄碧云VS.张爱玲的书写焦虑初探》)
由此可见,城市文化对于张、黄二人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作用。王安忆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本身就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并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当现代都市诞生以后,女性的边缘地位得到了改变。女性在现代都市中不再是完全的弱势群体,而是逐渐变成了优势。女性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气质个性,在现代都市中也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发挥。“都市释放出来的文明气质,潜在的要求人变得文雅、礼貌、卫生、整洁,这些特质,更多地具备女性特征”(仵埂,《城市与女性写作——以张爱玲王安忆为例》,《小说评论》,2008年第3期)。在现代都市氛围的影响下,作家张爱玲与黄碧云能够得以细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同时又因时代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两位女性作家的殖民主义叙述与后殖民主义叙述两种不同的方式。
温柔与暴烈:张、黄二人的女性写作风格
比较张爱玲与黄碧云的小说便可以发现,在小说风格上二人还是有一定的渊源。黄碧云出道之初的创作与张爱玲的小说就存在着相似之处。然而,张、黄二人的小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因此也有人认为,将黄碧云作为张爱玲在香港小说界的传人,实在值得斟酌。细读张、黄二人的小说后发现,张、黄在风格上仍然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张爱玲的小说风格更显女性温柔一面,而黄碧云的小说则多暴烈气。张爱玲与黄碧云的相似之处颇为可观,而比较二人的相异却更容易。时代因素、个人因素与理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的张、黄二人,也就在小说中分别表现出了温柔与暴烈的基本风格。
一、乱世与盛世:时代背景下的张、黄女性写作
张爱玲与黄碧云都生活于变革的时代,在小说中也一直表现出了一种苍凉、世纪末的味道。与此同时,张爱玲与黄碧云都可以成为是“与其伸出时代抗衡的作家”(黄念欣,《花忆前身——黄碧云VS.张爱玲的书写焦虑初探》),但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二人在写作理念存在差异,因而在书写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不同的格调。张爱玲的生活环境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足以用“乱世”概括,在抗战时期讲究的是小市民的生存智慧与生存方式,这一点,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中就有所体现。白流苏深知范花花公子范柳原只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而对自己青睐,她也知道“没有婚姻的保障,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是很痛苦很困难的事”。当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精明计算的人终于走到一起时,同居还不过一周的时间,范柳原就要前往英国,一年半载才能重新返港。二人都未预料到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柳原也只得中途返回香港,与白流苏正式结婚并过起平静安慰的生活。然而对于白流苏而言,这场战争的爆发,即使一个城市颠覆万千人痛苦,但是却以一种“倾城”的方式成全了白流苏。在这样的炮火中白流苏同样以小市民的智慧生存着,炮火给予了白流苏成全,让她与范柳原柳暗花明。这也就是乱世之下所需要的一种智慧与特殊的生存方式。
相比之下,黄碧云所处时代已是世纪末的盛世图景。黄碧云的创作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正值香港的转折时代——经济转型和政治过渡期。香港步人了后工业时代;殖民地历史走向终结,使香港进人了一个家国意识同本土地方意识矛盾交融的政治过渡时期。香港文化形态上相应出现后现代的景观,产生了商品无处不在、无孔不人的大众消费文化。处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个人的主体意识被瓦解、消失。人在感叹城市变化的同时也心生疏离感。在缺乏人性的都市环境中,享受着现代化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又陷于精神无所依归的疲惫之中。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内化为黄碧云的创作意识、审美意识,使其小说形成了书写现代都市的整体风貌。八十年代,香港社会处于消费文化、优皮文化当道的盛世,而在香港这样包含有双重文化的盛世中,战时小市民的生存智慧已经不再适用。在盛世香港的文化氛围中,爱情也不是战争时代一时的小恩小惠就能使恋爱双方满足,而是变得更为客观更为现实。所以,在黄碧云的《盛世恋》中,男女主人公没有了刻骨铭心的誓言,反倒如同白开水一般相识、结婚、离婚。黄碧云以《盛世恋》为题,是因为故事中的女主角程书静渴望爱情与生活共同完美,却与寻求稳定婚姻、生命活力早已萎缩的男主角方国楚共同遭遇了失败。女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是世纪末的香港,在如此社会氛围下的程书静,习惯于独立,习惯于一种“形而上”的爱情,也就要求她的恋人学识、阅历、青春、真诚等一样都不能少。而方国楚在生活中已经被磨平了棱角,需要的只是一份稳定的婚姻生活。程书静试图利用血红色的周祖儿来激发方国楚身上失落已久的生命活力,并误以为取得了成功。此时的方国楚有了学位.有了教职,只差一个象样的婚姻,朱先生一番良苦心使他有了这样的机会。正是如此的两个人在经历了死亡之后,在森森白骨旁下决心去共同编织爱情和婚姻的谎言。事实上,方国楚只有在过去的状态下才是鲜活的,“他根本不在等她。他整个人只是过去式,他把他自己也扼杀了”。而程书静也绝不会去迁就如此一般的形式上的婚姻。因此,在一场打着“盛世恋情”的标签背后,隐藏着作者对人物的巨大讽刺:“她错了,她嫁给一个老人了。或许是她害了他。她嫁给他,完成他做人的责任。她搬出了家。安静地说:和我离婚,好不好。水到渠成,没有纠缠,香港巾环风起云涌的街道上。这原本的夫妻被人群冲淡,各自没人新的生活。”
乱世与盛世的时代差异造就了两位风格各异的女作家。战争促使了张爱玲将更多的视角投入到市民生存的哲学中去,观察市民生存的智慧。而到了属于作家黄碧云的盛世,生存智慧固然需要,却不再是战时小恩小惠便可以满足的精打细算的生存方式。到了盛世,身处于消费与优皮双重文化的社会氛围,人群在这样的社会中失落的实际上是人性。黄碧云的小说大部分都缺少一般女性作家所具备的温柔气息,而是以冷漠的笔触书写生活中的病态、悲剧以及罪恶,如同王德威教授评述的“异象与疯狂”是她小说的底色。她将人物置于极端的境地,在丑陋、肮脏、血腥乃至死亡的面前,拷问人的灵魂,揭示出当代都市人病态乃至变态的精神状态。使读者映照自身精神面貌的畸形,警醒着人们自身的罪恶。
二、小女人与大女人:个人与社会的女性写作意识
张爱玲与黄碧云的小说不仅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同时还存在着个人与社会视角的差异。有关黄碧云小说的讨论大多也都集中于其利于展现人性之幽暗以及暴力问题,而关于张爱玲小说的讨论,则集中于其所致力表现的一种“上海气”。张爱玲对上海文化具有一种认同感,同时也乐于展现小市民的处世智慧,在政治方面反倒显得冷感。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作家批评张爱玲视野狭窄。而黄碧云从事过记者与律师行业,在写作中自然带有社会使命感及人类关怀。而前文所提到的黄碧云对张爱玲的一段评价,无论对错与否,首先也显现出了作家黄碧云本身所具备的一种“人文素质”,“她对五四精神‘以写来改变人的思想’的信念、对世情的洞察、人类困难处境的同情,都可以在她多练来载于《明报周刊》的专栏上找到。然而她又并非故作高调而忽略现世生活零碎试炼,反而有时候对小市民的心态与香港社会俚俗的一面有非常精到的描绘”。(黄念欣,《花忆前身——黄碧云VS.张爱玲的书写焦虑初探》,《十二女色》附录,台湾麦田出版社)

张爱玲身处于乱世,1943~1945年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代,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而言,张爱玲的小说就显得边缘化、细节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抗日救国成为文坛的主流,而此时的张爱玲却把眼光投向了“爱情、婚姻、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生的飞扬的。”张爱玲致力于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尤其是表现和时代有一点距离的“旧式女人”的生活命运,这一点与时代文坛主流相悖,也就因此导致了张爱玲的小说在长期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张爱玲笔下的“旧式女人”的生活命运,在时代精神下,可以称之为“小女人”。张爱玲的故事中由于存在着对上海文化的认同,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对于展示小市民处世智慧的兴趣,而似乎刻意对政治冷感。在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因为香港沦陷,才最终“挽留”住了范柳原。这或许正是张爱玲将小说命名为“倾城之恋”的原因:“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中,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成千上万人痛苦着”(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上卷P262)。在作家张爱玲的眼里,香港沦陷这样的事变只是为了成全白流苏的爱情。作家看到的只是白流苏的个人化命运,“刻意”将政治淡化,而是将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精打细算的爱情推上台面。香港沦陷这样的政治事件,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仅仅只是淡化成为一个背景。日本人发起的太平洋战争在张爱玲的视角中隐去了,香港面临的危局也淡化了,她关注的只是个人命运和个人爱情起落。有评论家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视界狭窄。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本身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女人”,关注的是“旧式女性”的命运。在这样的关注中,社会事件被淡化,“巧妙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读书》2008年第4期,P54—P55)
相比而言,香港作家黄碧云显得更为“人文”。黄碧云在香港《明报周刊》专栏“暂且”中曾经提过对张爱玲小说的“小女人”气质:“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很精到。语言华丽。但却是没有心的小说。我以为好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人文情怀:那是对人类命运的拷问与同情:既是智性亦是动人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属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好像一个饱受什么命运蹂躏的老女子,喃喃的在黑暗房间在数钱,一边埋怨自己命运坎坷,一边喃着要将穷租客赶走,租客已经什么钱都没有,又病,又有孩子,好麻烦,没有钱就睡街,不要租她的房子。张爱玲好势力,人文素质,好差。”且不说黄碧云本身是否对张爱玲的理解是否有偏差,但是,可以从这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黄碧云对张爱玲“小女人”的女性写作风格提出了质疑。黄碧云对于张爱玲的质疑,关键就在与“人文素质”一点。黄碧云香港大学新闻系毕业,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犯罪硕士,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律专业文凭。通过黄碧云所受的教育就可以看出,黄碧云身上具有很强的一种社会使命感。黄碧云在写作中讨论人性幽暗以及暴力问题问题,她的小说主题是多元化的,而暴虐、死亡、漂泊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黄碧云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环境敏感且投人,以冷漠的笔法叙述生活中的悲剧、悲情或罪恶。黄碧云的小说相对于张爱玲而言,有一种“大女人”的气质,更多的具备一种“洞察世情、同情人类困难处境”的信念。黄碧云之所以培养起这样的信念,与其的生活背景也有一定联系。黄碧云回顾自己的童年,指出自己在一个有暴力并且成员性格古怪的家庭中长大,坦言小时候因为离家出走.被父亲打得很严重,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并表示:“我爸爸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可以吃着饭突然就哭起来,跟着又什么事都没有。有时候他脾气又很激烈,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发觉我没办法,人是很难捉摸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家里人很多类似性格,我童年就在这种惊吓之中长大。”(颜纯钩,《颜纯钩黄碧云对话录(访谈)》,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黄碧云在许多小说中都表现出其对社会的关怀,在小说《暗哑事物》中,黄碧云书写了大量对人生的体验,呈现出人性的幽暗与对世情的关怀,员工陈越每天很努力的工作,什么事情都会抢在前面做,公司里的OL还是看轻她的职业,叫她做“陈屎”;在做社工的女OL已经将所有的职业看作是执行程序,对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也早已丧失了帮助的耐心:
“我每一次都答:你都没预约我只给你五分钟。
“她说姑娘我只有你了。我犹如猎物被紧捉。
“照顾者。这是我的职责与荣耀。如果这对我还有一点意思的话。”
张爱玲的“小女人”气质与黄碧云的“大女人”气质,与两位女作家的经历相关,同时也与其思想倾向相关。张爱玲对小市民生存智慧的书写,对“旧式女性”命运的关注与黄碧云对整个社会的关注,在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挖掘与洞察,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进行洞察。张爱玲和黄碧云相隔半个世纪,虽然有着极大的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的差异,但是,两位女作家感知城市、人性与社会的阳光还是带着一定的相似度。王德威教授认为如今的时代是可称为是一个对张爱玲模仿的时代,也认为黄碧云可算是张爱玲的传人之一,但黄碧云更致力于对人性的阴暗面的表现,她对人的内心的鬼魅的刻画以及残酷的笔法上,大大超越了张爱玲。而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超越其时代的意识,“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张爱玲,《张爱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张爱玲在“规避”政治事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只是方式比黄碧云更细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