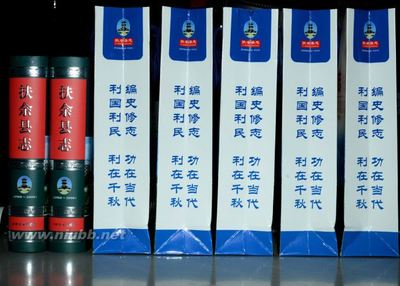第五章 (上)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宿舍楼和一些辅助设施都建起来了,地主的老屋改建成了食堂,路也修出来了,而这时所谓的“工厂”在哪里还不知道,所以剩下的工作就不是很忙,也不是很累了,这让知青们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生活是单调乏味的,除了上工就是政治学习,业余生活几乎一片空白,不过这反而让这些远离家人的女孩子们变得心灵手巧了:她们点起小煤油炉就能烧出可口的饭菜,拿起毛线就能织出花样百出的毛衣。更巧点的姑娘则是绣花、勾花、做鞋、酿酒,样样通。涧云对女红并不特别爱好,她更愿意花时间多看书写字;但她又是个不甘落后的人,别人会的她都会用心去学。因此,她做的女红,连她的“师傅”也不相信是新手做的;她酿的米酒,甜甜的;腌的辣酱,香香的;一次,她仅用鸡蛋和红萝卜就做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踏雪寻梅”,惹得同宿舍的姑娘赞不绝口。
有一个星期天涧云和伙伴们逛镇上小街(路修通了后下山也方便了),叮咚突然谈起了尼克松夫人访华时穿的红色裙式大衣,很羡慕地说:“你看我们,本来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可是身上穿的不是蓝就是黑,最‘作噱(xue)’的也不过就是‘土八路’军装,不男不女,老气横秋的,什么时候也能穿上那么一件红的大衣呀、裙子呀什么的就好了。”涧云心一动,立刻到商店里买了一块花布——严格说来不叫花布,只是白底上有点黑色格子而已,但比起大家常穿的蓝、黑和“土八路”绿来,这就算是“花”了。回到宿舍,她把布摊在床上,拿起自己一件短袖衣放在上面,操起剪刀就剪。叮咚惊呼起来:“你又没做过衣服,不怕糟蹋了布?”涧云笑笑答道:“我就不信,我做不出尼克松夫人的裙式大衣,还做不出一件短袖衬衣?”
当涧云穿上自己做的短袖衬衣时,叮咚大为赞叹,连夸涧云真能干,做什么像什么;并不服输地宣布要自己动手做条裤子;刚好来看涧云的杨晓霏则说她回去就学做鞋子。
鲁广泉写信来,说他要结婚了,涧云立即动手给他绣了一块桌布,勾了一幅窗帘。看着桌布上一对自由游弋的金鱼,摸着窗帘上一双亲密相偎的熊猫,她暗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给自己绣这么一块桌布,勾这么一幅窗帘呢?
姑娘们“你追我赶”的争做“巧妇”,引起了连长穆自立的不满。穆自立和最爱“与人奋斗”的军代表一样,总是觉得十五连的“阶级斗争弦”绷得不紧。女知青们热衷女红,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为了“夺回无产阶级阵地”,他决定乘指导员因病回老家休长假,他主持连里全面工作之际,赶快“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他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他一方面大大加强了“抓思想工作”的力度,逼着知青们利用各种会议或是自己“斗私批修”,或是检举揭发“坏人坏事”;另一方面三天两头开各种类型的“批斗会”——或是批判连里像柯绍恩这样的“老运动员”,或是紧跟中央“批林、批孔、批周公”……
叮咚不满地私下向涧云抱怨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生怕不折腾一下人家不知道他有权!有这个精力,怎么不想着给我们把热水问题解决?”确实,这个说起来很小的热水问题实则是一个拖了很久的“大问题”。食堂里只能基本保证每天喝的开水,热水却无法保证。夏天,大家都是到小溪去洗澡,春、秋天则凑合着洗洗冷水,可现在眼看着就要立冬了,尤其是女知青,没有热水怎么过?涧云她们每天都要到食堂去“抢”热水,运气好的时候,能抢到一瓶,勉强够用;稍晚一点,就只能打到一点点,连喝都不够,甚至一点都打不到。
一天,涧云班收工晚了点,跑到食堂去的时候,已经一点热水都没有了。她愣怔怔地注视着空空如也的开水桶,心里一阵心酸;其她姑娘们则有的在抱怨,有的在哭泣。这时,恰好易凝从厨房里出来。原来,自从突击队任务完成下山后,他总会寻找机会上山。这一次十一连派先遣队员上山来筹备烧炭的事,他又主动请缨。刚才他打了开水后,进厨房找熟人聊天,恰好碰到涧云她们。
他把自己仅有的那瓶开水倒给了涧云她们。看着姑娘们千恩万谢的离去,想着涧云偷偷投给他的感动的目光,他伫立良久,毅然去敲开了康援朝宿舍的门,把康援朝拉到门外,跟他嘀咕了许久。他和康援朝谈不上有什么私交,但他的建议获得了康援朝的首肯——康援朝认为,接受他的建议,对自己没有任何坏处。
第二天,康援朝找了相关的一应负责人员,经过他的慷慨陈词,说服了有关人员,克服了一些困难。总之,知青们,尤其是女知青们欣喜地发现,一个新的土灶打出来了,这个灶专门用来烧热水,而且规定要优先保障供给女知青。这一下,大家对康援朝简直有点感恩戴德了,说他才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呢!
而穆自立,还在忙着抓他的阶级斗争。不过,他折腾他的,人们每次跟着他喊过闹过后,很快又一切回归平常,女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就“热爱学习”——那些枯燥无味、千篇一律的报刊实在提不起她们的兴趣,所以她们仍是热衷于女红,只是背着穆自立而已。穆自立心里清楚,但一时也无计可施,总不能为这去抓“反革命”吧?何况,大家都这样,抓谁呀?倒是涧云,做女红只是赶一时的新鲜,她还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这个“学习”和穆自立的要求不同,她是抓紧时间偷偷地看世界名著。她的书来源很广,不但有易凝提供,其他知青弄到了书也会给她看,条件是看完了讲给大家听。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十五连是“一人学习,人人进步”。
连里的男同胞大多数认为涧云只会读书不会女红。涧云觉得有这种误会也好,因为她发现,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许多男战友已经开始寻找各种借口接近她们,其中不少人就是以找她们帮助打毛衣洗被子为借口的。而涧云,宁愿在别的方面帮助他们(比如送粮票)也不愿在这方面帮,因为她认为缝衣洗被已经越出了一般的男女关系,她不想跟什么人都把关系弄得那么亲密。
寒冷的冬天很快就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这年冬天似乎特别冷,冷得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忙于十五连的基础建设,防寒用的木炭还没烧,而炭是取暖不可或缺的。往年都是各个连派部分男知青上山烧炭,但今年十五连的基础建设差不多完工,暂时也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何况他们就在山上,不需要再另外考虑住宿问题;于是被全部派去烧炭,而且他们烧出的炭还要供应山下的连队及营部。而别的连,只派出了少量像易凝这样的先遣队员。
山区的冬季显得特别的寒冷和荒凉。雪下得特别大,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三天,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在雪底下,房屋、树木、毛竹、公路偃卧着,仿佛已经消失了,到处像死一样寂静。
晚上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房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躺在被窝里象是躺在冰窖里。实在扛不住了,涧云和叮咚、小不点学其他知青们的样,把床拼起来。叮咚是没有垫被的,涧云那床用旧棉衣旧棉裤拼接的垫被也没有用了。她们把小不点的垫被和涧云的盖被当褥子,上面则盖着叮咚和小不点的盖被,三个人挤进一个被窝。冷,冷到骨头里去的冷!三个姑娘抱成一团,一边颤抖着一边流着泪,一边还在想着那曾经温暖的家乡。
(图片来自网络,谢谢!)
清晨,雪下得小了点,知青们便出发去烧炭了。山路两边被雪压弯腰的毛竹形成了一道道拱门,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迈进,身后留下一串串深深的雪窝。转过山路岔口,是一段往上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越来越险: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前人留下的许多个被茅草掩盖了的“老农洞”,不时还有被冰凌和大雪压断的树木和毛竹横躺在路上,稍不留神一脚踏空,就会滚下万丈深渊或是跌进老农洞,连踪迹都找不到。
知青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着,好不容易来到窑洞口,女知青负责将一段段砍好的木料传进窑洞,易凝、柯绍恩等男知青则钻进窑洞将木料码放整齐。木料上积满了冰雪,一段段“冰块”在女知青们手中传递着,不一会儿,每个人的手都冻得通红,尤其是手指头,冰得麻木;疼,钻心的疼从手掌直传到心里,渐渐地手和脚仿佛都冻僵了。“完了,我的手要冻残了。”涧云一边想着一边机械地传着木料,一点儿也不敢偷懒,因为稍一懈怠就可能被视作对革命的不忠,那她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许就会被打成反革命了。
“我不传了,我要回家!”一连几个小时这样的传递让小不点再也受不了了,她把手上的“冰块”一扔,放声大哭起来。几个干部连忙上前安慰她,这让涧云、叮咚等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很是羡慕——她们也不想传了,她们也想回家,但她们不敢像小不点一样做。如果她们敢这样,说不定一顶顶的“高帽子”就飞到她们头上了;但她们多么想像小不点一样扔掉手中的“冰块”,放声痛哭一场啊!涧云忍住泪,无助地把眼光从小不点身上收回来,茫然地向四周望去。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易凝关切的目光——这温暖的眼神,让她感到心头一暖,本来哭丧着的脸上竟然绽放出了一丝甜甜的笑容;而这笑容,又像一股暖流,流进了易凝的心头,使他觉得身上也暖和了许多。
几个干部商量了一番后,康援朝顶着漫天的风雪下山了,又踏着厚厚的积雪连夜赶了回来。他带来了一个对女知青来说绝对是好的消息:经过他的坚决要求,营部已经答应马上通知各连队抽调男知青上山烧炭,把十五连的女知青撤回去。
女知青们高兴得又哭又笑,她们感谢小不点那勇敢的一哭,感谢康援朝的风雪夜行。涧云在高兴之际又有点不舍和担忧,她在人群中寻觅着易凝。当两人的眼神相碰时,易凝欣慰地颔首示意:只要涧云能“脱离苦海”,他就无忧了。
(下)
烧炭任务完成后,1973年的元旦也来临了。为了表示慰问,团部专门派放映队来给山上的知青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文化教育“万马齐喑”的时代,人们已经厌倦了几部革命片,几个样板戏一统天下,因此一部《卖花姑娘》居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山下人看了几遍还不辞辛苦往山上赶,远近听到消息的农民也顶风冒雪赶来了,整个山上格外的热闹起来。“地保”叮咚前几天就在女生宿舍宣布:大家一定要多准备几条手绢,听看过的人说,观众是从头哭到尾的。别看涧云表面上挺坚强的,但小说和电影却很容易赚她的眼泪,于是她还真的准备了好几条手绢。
天快黑时,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但这丝毫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山下还不断有人上来。急性子的叮咚等人早早吃完饭,把能穿上身的衣服都套上,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到操场上去占位子了。所谓操场,就是连队平时集合的一块空地,放映队在正前方两棵树之间挂了块白色的幕布。涧云一向爱磨蹭,所以等她到了操场时,发现黑压压的一片尽是人,根本无法靠近叮咚她们。正在一筹莫展时,耳旁响起了一个轻轻的声音:“跟我来!”她回头一看,又惊又喜:是易凝!也来不及多想,涧云就随着他挤出了人群,向宿舍西边的小路走去。
走了一段路,涧云觉得不对了:她起先以为易凝是带她从旁边绕到叮咚那儿去,后来发现他们竟远远地离开操场了。她不解地问易凝:“我们这是往哪里去?电影马上要开演了!”易凝边走边答道:“看什么电影!没听说吗,‘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打打闹闹,越南电影鬼哭狼嚎,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你还没看够啊?”“可是这场《卖花姑娘》据说相当好看哩!再说咯,你不是来看电影的么?”涧云颇有些不舍,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
“什么相当好看,就你们这些女孩子眼泪没地方抛要往那里抛罢了。我们已经活得够不自在了,何必还去寻不开心?你如果真舍不得不看,等有时间下山时,我陪你到镇上电影院去看,何必坐在雪地里看?小心冻僵了!”易凝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小包,放到涧云的手上。涧云感觉到暖暖的,问:“是什么?”
“打开看看!”易凝故弄玄虚。涧云解开毛巾,一个热烘烘的、软软的烤红薯露了出来。“啊!”她不由惊喜地叫了起来。在冰天雪地的此刻,见到又热又软的,已经久违了的烤红薯,这种喜悦之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涧云激动得眼眶都有点湿润了。
易凝微笑着看着她说:“快吃,再不吃就冷掉了,冷了就不好吃了。”
涧云掰下一半递给易凝,见他不肯接,说:“你不吃我也不吃!我才不相信你已经吃了呢!”
见涧云态度非常坚决,易凝只好接过半个红薯,两人边吃边走。看着月光下漫天飞舞的雪花,易凝说“看,雪越下越大了,我们这样走一走还暖和点。等下我们去前面的地里看看能不能挖到点肥田萝卜,顶着风雪吃萝卜,虽然没有吃这热烘烘的烤红薯舒服,但也别有风味的!”
涧云虽然还有些想着《卖花姑娘》,但又实在无法抗拒易凝,因为他的提议挺有吸引力的。路面显然有人扫过,并无积雪。望着眼前这条不知通往何方的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涧云有点伤感地叹道:“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走出这条小路?”可是她马上又想到,两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个相聚的机会,实在不该讲这些让人伤心的话,于是她连忙改口道:“听说离这里约摸二十分钟的路边有一个山洼,那里曾经有个工厂,现在废弃了。奇怪了,工厂建到这里来干吗?多不方便啊?”
“确实有个废弃的工厂,我去看过,但有人守门,没让我进去。”易凝说,“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时从城里迁过来的。听说是个纺织厂,原来女工很多,但没过多久就嫁的嫁,跑的跑了;后来从农村招了些女工,可她们干了不久也不干了,说还不如回家种田。”
涧云点点头道:“哦,是这样!听说有这么一句话:重工业不重,轻工业不轻。讲的就是号称轻工业的纺织业工作很累,而号称重工业的金工、翻砂等,对女的来说并不累。不过,依我看,能跨进工厂的大门就不错了,管他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呢!”
正说着,他们发现路边有一破烂小屋,大概是用来堆农具的。易凝叫涧云等等,他要进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小铲子之类,可以用来挖地里的食物。
涧云在雪地里跺着脚取暖,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便连忙闪到小屋的门洞里。不一会儿,只见有个女子急匆匆地往小路尽头走去。虽然那人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一条大围巾把头全盖住了,但涧云还是从她的背影认出了那是她们的副排长沈凤婕。
沈凤婕出身于令人羡慕的人民警察家庭,她本人读了司法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洵绵山劳改农场工作。文革爆发时,她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瞬间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把这个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她成为了农场造反派头目,但不久就在派系斗争中被打倒,知青下农场时她还是被批斗的对象呢!所幸她出身好,父母在文革中不但没受到冲击反而连升三级,所以她很快被“解放”了。由于她是中专毕业,按国家规定享受干部待遇,所以涧云她们上山时,沈凤婕便被任命为副排长。官虽然不大,却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干部,比知青中那些因出身好而担任副排长以上职务的要“硬”哩!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在文革初期“碰得头破血流”的沈凤婕不再起劲了,虽然当个副排长,她却不多管事,凡事能躲则躲。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说她又不是知青,谈恋爱是无人干涉的,于是便有热心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却连面都不肯去见,说这辈子就愿当个老姑娘。她爱唱歌,嗓子也不错,经常在宿舍里给大家唱“李铁梅”、“小常宝”等样板戏。此刻她不去看电影,却急匆匆地出现在这里,是要往哪里去呢?涧云怕惊动她,不敢跺脚了,只是不出声地轻轻抖着脚。
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上,静谧且充满寒气,神秘而又苍凉。就在这时,一阵悠扬凄婉的箫声从竹林中飘过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撼人心魄,催人泪下。涧云不由地停住了脚步,凝神静听。她发现沈凤婕也停住了脚步,而沈停步的地方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岔路口。涧云认出了那是通往就业人员家属区的岔路口,那里住着就业人员老莫一家;她知道老莫有个很会吹箫的儿子,她和伙伴们常常会借着夜色悄悄地跑到路口去听小莫吹箫。想起了人们私底下议论沈凤婕好像挺喜欢小莫,涧云不由得为他们担起心来:他俩的差距太大了呀!
“老莫”是知青对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宿舍楼设计者的称呼。老莫的父亲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教授,自己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赴苏留学后回国。就在他准备大展宏图时,一场“反右”,毁了他的一生,也毁了他们全家。老莫在洵绵山垦殖场劳改,刑满后在此就业,把家人也接过来了。他儿子被知青们称作“小莫”,小莫在逆境中没有消沉,而是用美丽的音乐来为自己那灰暗的人生添上一抹亮色。幸运的是他在学习音乐中得到过不少专家和大师的指点(和他父亲一起劳改的有不少名家大师),所以他才会把箫吹得那么好。可是在这个年代,箫吹得再好有什么用?涧云根本不相信沈凤婕和他会有什么结果!
缠绵悱恻的乐曲声越来越清晰了,是《小路》!“这是一首诞生于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烽火硝烟中的歌曲,歌颂的是年轻的姑娘追随心上人上战场的故事。曲调优美而不柔弱,情深而不缱绻,歌声中透着坚强和勇敢,给人一种向往美好,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被箫声深深打动的涧云突然有了一股强烈的想跳舞的欲望,尽管她平时并不怎么跳舞,但心灵的强烈震撼使她不能自抑地就是想跳。积雪的山路上不好尽情施展,但她不管不顾,随着箫声,含着热泪舞了起来,动作舒展、婀娜款摆,“泪痕尚尤在,笑靥自然开”。她很随意地跳着,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释放。她没有想到的是,此刻那吹着箫从竹林中款款而来的不是小莫,却是易凝!
和着凄美的箫声和激情的舞蹈,一个清亮柔和、饱含深情的女声响了起来,这是沈凤婕在唱。她以为是小莫在吹箫,便情不自禁地和了起来。而此刻的小莫,虽然明知道沈凤婕就在路口,却站在屋里一动不动,他的父母则在一旁叹气。易凝的箫声响起时,小莫就拿起竹箫打算和他。易凝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吹箫,但刚入门就因为家庭变故中断了学习。在山下时,易凝听了小莫吹箫,便悄悄地拜他为师。所以箫声一起,小莫就知道是易凝在吹,打算去和他。但沈凤婕的歌声响起,反倒让他止步了。他不是不知道沈凤婕的心意,可看看饱受屈辱的父母,看看这个他们赖以栖身的简陋窝棚,他揪心地抱头蹲下:两个家庭身份的悬殊,不啻是天壤之别,他哪敢心存半分妄想啊!他又怎么忍心让沈凤婕跟着他过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呢?他含泪抚摸着手里的竹箫,只有任由那美丽而又忧伤的旋律像流水般在他心头缓缓流淌。
在他们的上空,在浩瀚的苍穹里,正飘渺着那动听而又动情的歌曲:
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迹
没有脚步也听不到歌声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
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我的小路伸向远方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
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那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深邃的意境,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在这扼杀浪漫、扼杀柔情的岁月里,在这让人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的绵延小路上,苏联歌曲那抒情、真挚、纯朴、浪漫的旋律,滋润了两对年轻人情感的荒漠,也滋润了他们渴望释放真情的心灵。
(图片来自网络,谢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