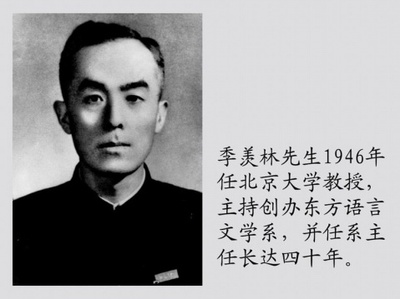那盆昙花养了整整六年,仍是一点动静没有。
我想我对它已是失掉希望和耐心了。 时常想起六年前那个辉煌的夏夜,邻家那株高大壮硕的绿色植物,几乎在一瞬间变得银装素裹,像一位羞涩的新娘披上了圣洁的婚纱——从它宽大颀长的叶片上,同时开出了十几朵雪白的昙花。它们像是从神秘幽冥的高山绝顶上飘然而来的仙鹤,偶尔降落在凡尘之上,都市的喧嚣在那一刻曳然消散,连树的呼吸都终止了。
邻居请我去,是为了给她和她的昙花合影。第二天一早,我得到了一只小小的花盆,里面栽着两片刚扦插上的昙花叶,书签似地挺拔着。它是那盆昙花的孩子,刚做完新娘接着就做了母亲。
年复一年,它无声无息地蛰伏着,枝条一日日蓬勃,却始终连一丝开花的意思都没有。葫芦形的叶片极不规则地四处招摇扩张,长长短短地说不出个形状,占去好大一块空间。窗台上放不下了,怜它好歹是个生命,不忍丢弃,只好把它请到阳台上去,找一个遮光避风的角落安置了,只在给别的盆花浇水时,捎带着用剩水敷衍它一下。心里早已断了盼它开花的念想,饥一餐饱一顿地,任其自生自灭。

六年后一个夏天的傍晚。后来觉得,那个傍晚确实显得有些邪门。除了浇花,平日我其实很少到阳台上去。可那天就好像有谁在阳台上一次次地叫我,那个奇怪的声音始终在我耳边回荡,弄得我心神不定。我从房间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回房间,如此反复了三回。我第三次走上阳台时,竟然顺手又去给冬青浇水,然后弯下腰为冬青掰下了一片黄叶。我这样做的时候,忽然有一团鹅黄色的绒球,从冬青根部的墙角边“钻”出来,闪入了我的视线。我几乎被那团鸡蛋大小的绒球吓了一大跳——它像一个充满弹性的橄榄,贴地翘首,身后有一根绿色的长茎,连接着那盆昙花的叶片。绒球锥形的尖嘴急切地向外伸展着,像是即刻要开口说话……
那不是绒球,而是一枝花苞——昙花的花苞,千真万确。
我愣愣地望着这位似乎由天而降的不速之客,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后来我用全身力气,轻轻将花盆移出墙角,慌慌张张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搬到了房间里。然后屏息静气、睁大眼睛纵览整株花树——是的,上上下下,它只有绝无仅有的这一个花蕾。也许因为只其一个,花苞显得硕大而饱满。
那个蹊跷的傍晚,这盆唯有一个花苞的昙花,由于无人知道,更难预测它将在哪一天的什么时辰开放,那蛇头似弯拱的花茎,在斜阳下笼罩着一层诡秘的光晕。
我想这几天我就是不吃不睡,也要守着它开花的那个时刻。
昙花入室,大概是下午六点左右。它就放在房间中央的茶几上,我每隔几分钟便回头望它一眼,每次看它,我都觉得那个花苞似乎正在一点点膨胀起来,原先绷紧的外层苞衣变得柔和而润泽,像一位初登舞台的少女,正在缓缓地抖开“她”的裙衫。昙花是真的要开了么?也许那只是一种期待和错觉,但我却又分明听见了从花苞深处传来的极轻微又极空灵的塞窄(窸窣、悉索)声,像一场盛会前柔曼的前奏曲,弥漫在黄昏的空气里……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那一枝鹅黄色的花苞渐渐变得明亮,是那种晶莹而透明的纯白色。白色越来越醇厚,像一片雨后的浓云,在眼前伫立不去。晚七点多钟的时候,它忽然颤栗了一下,颤栗得那么强烈,以至于整盆花树都震动起来。就在那个瞬间里,闭合的花苞无声地裂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喷吐出一股浓郁的香气,四散溅溢。它的花蕊是金黄色的,沾满了细密的颗粒,每一粒花粉都在传递着温馨呢喃的低语。那橄榄形的花苞渐渐变得蓬松而圆融,原先紧紧裹挟着花瓣的丝丝淡黄色的针状须茎,如同刺猬的毛发一根根耸立起来,然后慢慢向后仰去。在昙花整个开启的过程中,它们就像一把白色小伞的一根根精巧刚劲的伞骨,用尽了千百个日夜积蓄的气力,牵引着、支撑着那把小伞渐渐地舒张开来……
现在它终于完完全全绽开了。像一朵硕大的舌匙状白菊,又像一朵冰清玉洁的雪莲;不,应该说它更像一位美妙绝伦的白衣少女,赤着脚从云中翩然而至。从音乐奏响的那一刻起,“她”便欣喜地抖开了素洁的衣裙,开始那一场舒缓而优雅的舞蹈。“她”知道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演出,自然之神给予“她”的时间实在太少,“她”的公演必须在严格的时限中一次完成,“她”没有机会失误,更不允许失败。于是“她”虽初次登台,却是每一个动作都娴熟完美,昙花于千年岁月中修炼的道行,已给“她”注入了一个优秀舞者的遗传基因。然而由于生命之短促,使得“她”婀娜轻柔的舞姿带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凄美。花瓣背后那金色的须毛,像华丽的流苏一般,从“她”白色的裙边四周纷纷垂落下来……
那时是晚九点多钟,这一场动人心弦的舞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她”一边舞着,一边将自己身体内多年存储的精华,慷慨地挥洒、耗散殆尽,就像是一位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的侠女。那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但辉煌仅有一瞬,死亡即将接踵而至;“她”的辉煌亦即死亡,“她”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到达辉煌的。那是一种壮烈而凄婉之美,令观者触目惊心又怅然若失。“昙花一现”几乎改变了时间惯常的节律——等待开花的焦虑,使得时间在那一刻曾变得无限漫长;目睹生命凋敝的无奈,时间又忽而变得如此短暂;唯其因为昙花没有果实,花落花谢,身后是无尽的寂寞与孤独,“她”的死亡便成为一种不可延续的生命,成为无从寄托的、真正濒临绝望的死亡形式……
盛开的昙花就那么静静地悬在枝头,像一帧被定格的胶片。
但昙花的舞蹈并未就此结束。
那个奇妙的夏夜,白衣少女以“她”那骄傲而忧伤的姿态,默默等待着死亡的临近。在我见过的奇花异草之中,似乎没有一种鲜花,是以这样的方式告别的。那个瞬间,我比亲眼见到它开花的那一刻,更是惊讶得无言以对——
“她”忽然又颤动了一下,张开的手臂,渐渐向心口合抱;“她”用修长的指尖梳理着金发般的须毛,又将白色的裙衫一片片收拢;然后垂下“她”白皙的脖颈,向泥土缓缓地匍匐下去。“她”平静而庄严地做完这全套动作,大约用了三个小时——那是舞蹈的尾声中最后复位的表演。昙花的开放是舞蹈,闭合自然也是舞蹈。片片花瓣根根须毛,从张开到闭合,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她”用轻盈舒缓的舞姿最后一次阐释艺术和生命的真谛。如果死亡不可抗拒,为什么不能让死亡变得美丽?如果死亡必不可免,为什么不能让死亡变得神圣?“她”定是为自己选择了安乐死那种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所以在最后的极限到来之前,“她”来得及为自己更衣梳洗,用端庄而整洁的仪态,微笑着迎接死亡;“她”由于珍惜生命而加倍地珍惜死亡,赋予永别以再生的意味。“她”不会像那些落英缤纷的花树,将花瓣的残骸凄凉地抛洒一地;“她”要在入殓前将自己的容颜复归原状,一如生前的娇媚和高贵……
世上也许唯有花期最短的昙花,具有此等视死如归的气度。
至夜半时分,昙花盛开时舒展的花瓣已完整地收拢,重新闭合成一枝橄榄形的花苞,只是略略显得有些疲倦,细长的花茎软软地低垂下来,在玻璃台板下衬出一个白色的影子,像浮游在湖上的天鹅倒影。那花苞的白色,比先前要浅淡些,残留在空气中的香味,已将它乳白色的浆汁吸尽。因而花苞更像是一枝不死的果实,将花的魂留在了里头;而支撑着昙花花瓣那伞骨似的一根根须毛,此刻却已奇迹般地空翻转身,一百八十度大回环,把那个沉甸甸的花苞:重新牢牢地裹在了掌心。犹如开屏后的孔雀,丝丝入扣地将锦缎似的羽毛一并收好。
它看上去像睡着了,宁静而安详,没有凋敝没有萎谢、没有痛苦没有哀愁;它是一个不死的灵魂,昨夜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很多天以后我拿到了那天晚上留下的摄影照片,它在开花前和开花后的模样,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不生不灭,不开不谢——就好像这一个活生生的花苞,从来都没有开放过,或许很快就会再开一次。它始终含苞待放,始终无悔无怨;只等那个属于它的时辰一到,它睁眼就会醒来。
我很久很久地陪伴着它,陪伴着昙花走完了从生到死,生命流逝的全部旅程。“昙花一现”那个带有贬义的古老词语,在这个夏夜里变成一种正在逝去的遥远回声。我们总是渴望长久和永生,我们恐惧死亡和消解;但那也许是对生命的一种误读——许多时候,生命的价值并不以时间为计。
我明白那个傍晚的阳台,昙花为什么一次次固执地呼唤我了。那最后的舞蹈中,我是唯一一位幸运的伴舞者。它离去以后,我将用清水和阳光守候那绿色的舞台,等待它明年再度巡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