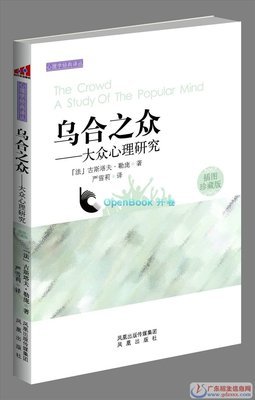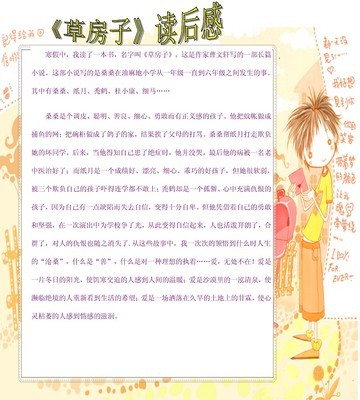梦中每走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对故乡的思念是一个身处异地的老者,晚年最为重要的事,也是最美好的情感。不能实现的事,说一说,想一想,总也能慰籍那颗寂寞的心。在他的概念里,老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一个埋葬亲人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故土。于是,我理解了为何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守着一片贫瘠的土地不肯离开的原因了。这是他的家,他的根。这里埋葬着他的亲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块土地的土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代诗人崔灏一千年前发出的那一声感叹,被远走的人们反复咀嚼着,越咂越有味。这是一个离开故土的人,一生都解不开的情结。
人对故乡的感情是难以割断的。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小城,在那一段时间里,故土情结常常在我脑海中萦绕。那浓浓的乡情乡音,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那一双双亲人期盼的眼神,就是一句俏骂,也是一种享受,那是在别处听不到的声音。还有故乡的山水,那两旁长满野草的田间小路,那踏上去咯咯作响的青石桥,那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哥儿们,那些编织着许多童年梦想的故事,萦绕在意识深处,闪烁于梦境之中,让我久久的思念。这时我理解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为饥荒而离开故土的乡亲们,在离家的时候,都随身带了袋从家里院子的墙根挖的块故乡的黄土。那不仅仅是水土不服时,用开水冲一点喝了能治病。它已成为对故乡思念的精神寄托物。
故乡对于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那里有我的父母、姐妹,有我的童年、少年,有母亲在日落黄昏时,站在家门口呼儿回家吃饭的声音,有我站在石崖上大声呼叫萦绕不息的回声……离开它,是因为我想走出那块黄土地;想念它,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我的一段生命。这一段生命,是以十余年的汗水为代价养育的。无冬无夏,无春无秋,拼死扒活地劳动,就是为了能走出这片土地。是故乡的土地让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时至今天,我一直都认为在中国,最敬业的人应该就是像我的父母一样,在黄土地上刨食的农民。他们用那百十斤的躯体里蕴藏的力量,靠一方黄土,一生辛勤地养育儿女,他们对土地既恨又爱。恨它消耗尽了他们的生命,爱它给予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一生是和土地联在一起的,他们知道啥土质适合种啥庄稼,啥庄稼啥时种,啥庄稼啥时浇灌、拔草、间苗、施肥、收获。土地养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最终也把生命返归给脚下的那片土地。
我看到过一些老人,一生都在一块土地上耕种的八十多岁的老农,在离开那片土地时寂寞的心理。他们离开故土后,在城市的水泥、汽车、格子房中,迅速老去时的情景。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眼神,注释了他们对故土的无限思念。所谓的人挪活,这都是对年轻生命而言的。当一个人从幼年到暮年都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根叶枝脉就全都长在了这块土地上,离开了这块土地,他咋能再幸福。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故土的思念之情,被中华文化数千年来酿制成一杯浓烈的美酒,再有酒量的人喝了它都会沉醉其中。今春回故乡,突然发现我所熟悉的那些老人们都不在了,而记忆中的那些健壮的叔叔婶婶们也都显出了老态。见了我,他们都很惊讶。有的说,我过来时你妈妈还没生你呢。有的说,我回门那天你还穿着开裆裤呢。而和我同龄的人已是胡子花白,儿女成家了。故乡已没有在世的亲人,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一个都不认识。实实在在的只有脚下的那片黄土地。踉踉跄跄地走在上面,东瞅瞅西看看,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情,似乎还能感觉到脚下土地上儿时赤脚留下的余温;还能从几棵老树上,看到当年掏鸟窝时留下的身影。一群放学的孩子突然围住我,问:老爷爷你找谁啊?这时,我的泪水瞬间顺着满脸皱纹唰唰流下,才知道一千年前那个叫贺知章的诗人,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归”的诗,现在是多么地确切。这泪水是对故土至深的爱恋,是对过去一段生命的最后回顾,是我一生解也解不开的情结。
故土,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灵魂扎根的地方,肉体可以消失,而灵魂是不能无根的啊,故土,我与生俱有的根,一辈子也拔不出来!
感想:
没有经历过离乡,便不会知道故乡的意义,故乡的土地里所埋藏的记忆,是一个人烙印在灵魂中的痕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