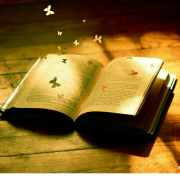女兽医
朱建平
温小雅是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也是全县唯一一个会阉鸡阉猪的女兽医。
温小雅的爷爷是兽医,温小雅爷爷的爷爷也是兽医。因此,到了温小雅父亲阿寿手里,兽医已经成了祖传。
那时候,虽然农民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但还是想方设法挤着养鸡养猪,毕竟平时的零用和过年的丰歉都要靠鸡猪来体现。所以阿寿整天背着个阉鸡用的网兜,走村串户喊着,阉鸡,阉猪,牲畜看病。因此,阿寿的手艺始终没有生疏。
村里人一直说阉鸡阉猪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外人难以掌握的暗行。
阉鸡阉猪一直有着传男不传女的行规。所以,当初中毕业读了一年高中就回家种田的温小雅提出要跟着阿寿学阉猪阉鸡,阿寿有点答应不下来。确实,一个女孩子干这种下九流的活,不但掉价,就连以后找个婆家都有难度。可温小雅说我上没有哥哥,下没有弟弟,你不让我学,你的手艺不就丢掉了?再说,现在公社都在要求大队建牧场,大队又要求生产队建牧场。牧场多了,集体养的猪多了,个人养猪就少了,想挣个人的钱越来越难,以后发展下去,会阉鸡阉猪的只能挣工分了。据说那天阿寿被温小雅说得一愣一愣的,他始终想不明白,才刚刚二十出头,比同龄人多读了半年高中,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思来想去,也想通了,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不传她传给谁?以后找个女婿入赘,再传给女婿也不迟。况且看着温小雅似乎特别喜欢学阉鸡阉猪,因此,阿寿也就依了女儿,
后来听人说,大队的八个生产队办了九个牧场后,大队部考虑到养猪的需要,想多发展几个会阉猪的兽医。可当支书让阿寿在全队范围内挑选一两个徒弟时,阿寿扳着手指数了一圈,竟然找不到一个比年轻,有文化,肯钻研的温小雅来得更合适的人。村支书挠挠头皮,喝了半勺子井水后,只能同意阿寿只带温小雅一个人做徒弟。阿寿这样做,村里人都说他有着一箭双雕的成分在里面,既随了女儿的心愿,也了了自己的心事,没有让阉鸡阉猪的技艺失传在自己手里。
有了大队支书的点头,阿寿趁着生产队办牧场买进一大批小猪急需要阉割的机会,让温小雅把学习、实习一口气完成,本来一窍不通的温小雅通过对上百头小猪的阉割,很快阉割技术练得相当的精湛。特别是阿寿引以为豪的小母猪小挑阉割术,温小雅更是青出于蓝。
温小雅最终没有在大队牧场做兽医,而是做了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温小雅进兽医站,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抓住了机遇。后来说起这事,温小雅总是很自豪,确实,这对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来说,要有多大的勇气。
当时公社农技站按照县里的部署,结合当时畜牧业的发展成立兽医站,兽医站兽医的职能除了阉鸡阉猪,还要防疫治病。公社农技站把在村头村尾流荡的那帮阉鸡阉猪兽医一摸排,才发觉要想收编几个技术比较好的阉鸡阉猪的做兽医,还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员。原本走村串户的老兽医以他们的年龄、一直只会阉割、只会用三棱针给猪放血原始的听天由命治病手段,根本无法胜任现代防疫治病的重任。阿寿就是其中一个。
兽医站的成立,意味着原来走村串户的兽医已经无法从事原来的行业,只能和其他的农民一样,上山砍柴,下地割稻种田。这样的活计让一直习惯阉鸡阉猪挣点活络钱的阿寿如何能接受,可是,规定在那里,不服从也得服从。从牧场阉猪回来的温小雅看到坐在灶下一口一口咬着烟管抽烟的阿寿,奇怪地问,怎么了?阿寿把前因后果一说,温小雅在脑子里快速一番盘算,赶紧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蹬蹬蹬直往公社农技站跑。
农技站站长听了温小雅一阵慷慨激昂的演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了句,会骑自行车吗?温小雅摇摇头,不会。站长站起身,走到边上办公室,喊了声,小杨,你带着这位姑娘和我一起去牧场。
公社的牧场,在离公社五六里地的远的棋盘山脚下,被一大片梨树包围着。这里本来是一块乱葬岗坟地,在前几年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农业学大寨大运动中,公社在山腰上种满了梨树,在山脚下修了一个大坝,把从棋盘山上下来的水全部收了起来。满起来的水库水慢慢把乱葬岗淹没,那块不知道是什么年代被山洪冲刷成的堆堆卵石,就显得突兀。据说县委书记下乡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乱石岗,说了句,这石头用来建牧场真是太好了。县委书记一句话,公社立马行动,充分利用修水库时候建的一条机耕路和那些种不了庄家的卵石,切成墙头,盖上草苫,养上公猪母猪,成了牧场。
牧场养着十多头母猪,五十多头肉猪。站长一进牧场,就问场长,要阉割和打防疫针的猪多吗?场长指着三四窝叼着母猪奶头在哼哼唧唧的小猪说,就这些。站长点点头,顺手指着眼前的一窝十来头小猪对着温小雅说,你把这小猪都阉了。
温小雅看了下猪圈里那群拱在母猪肚子里吱吱乱叫吸奶的小猪问,全部阉掉?场长“嗯”了一声。温小雅又说,不从里面挑几只小母猪留种?场长看了眼站长,站长笑了下,场长豪气地说,这窝不留。温小雅笑笑,那我动手了。边说边从背着的书包里掏出一个腰子形的酒精棉花盒,两把五寸来长锃亮逼人,刀把比挖耳勺粗不了多少,刀刃和小指甲盖差不多宽的阉割专用刀。这两刀初看是一样的,但细看就觉察出不一样了,一把的刀刃是斜斜的三角形,一把的刀刃中间是尖尖的棱形,和微型宝剑差不多。
温小雅先用酒精棉球把三角形的刀刃擦拭了一遍,对着场长说,你把公的给我抓出来。场长看看站长,又看看温小雅,没有动手。站长说,你就依着她。场长跳进猪圈,抓了一只小公猪从猪圈里递了出来。温小雅一伸手,把刚刚拿在手上的阉割刀往嘴巴里一塞,锃亮的阉割刀即刻被她牢牢地咬住,仿佛漂亮的嘴巴里穿了根银簪。站长看了眼阉割刀,眼睛亮了下,但很快把目光转到了温小雅的动作上。
温小雅扯住小公猪的后腿顺势往地上一放,左脚踩住颈部,右脚踏住尾根,像两枚钉子,把拼命挣扎的小公猪牢牢地钉在了地上,无法动弹。紧接着温小雅左手一把捏住小公猪的阴囊,右手先拿了颗酒精棉球在阴囊上擦了几下,然后从嘴巴上拿下阉割刀。就在温小雅拿阉割刀的时候,小公猪适时挣扎了一下,那寒气逼人的刀锋差点划到了嘴角,把站长吓了一跳。但温小雅似乎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刚才的危险,执着刀把,一用力,只听到“嘶”的一声,小公猪刚刚还躲在阴囊里的睾丸像一只还没长毛刚刚学会跑跳的小老鼠,“噗”地一下跳了出来。温小雅快速扯住睾丸,用刀小心地把连着睾丸的那些筋筋条条割断。接着,又是一刀,另一个睾丸也刷地一下跳了出来。温小雅同样小心地把睾丸和小公猪分离。做完这一切,她熟练地用手在已经没有了睾丸的阴囊上撸了几下,把存在里面的血水撸出后才放开脚。受了痛的小公猪惨叫着飞奔到角落的草堆里,把头死死地塞进草堆,再也没有勇气看一眼让它成了公不公母不母的温小雅一眼,只顾着痛苦而无助地呻吟。
站长看了看刚刚直起身的温小雅,冲着场长一努嘴,场长心领神会地抓出一只小母猪递给温小雅。温小雅看看站长,再看看笑嘻嘻的场长,没有多说,在接小猪的时候,把手上的月牙形阉割刀换成了那把棱形手术刀,依旧牢牢地咬在嘴巴上。
温小雅在接过小猪的时候,顺手用手背擦了下额头,把额头上冒出的让人感觉痒痒的汗珠一把擦去,也把挂落下来的几缕发丝撩到耳朵背后。看着这个动作,站长心一动,似乎刚刚才发觉风风火火的温小雅也有着娇柔的一面。
温小雅根本没理会站长的眼神,只是借着小母猪从猪栏里拎出来的惯性,顺势把小母猪撂倒牢牢地用脚钉在地,只是头尾的方向和刚才的小公猪换了一下,因为紧张,刚刚横着咬在嘴里的手术刀,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
温小雅不由得脸一红,赶紧捡起手术刀,拿酒精棉球擦拭了一下,然后抓住小母猪的髋骨向后一扯,伸出的大拇指自然而然成了下刀的标尺。因为有站长和场长在边上,温小雅似乎没有了平时的自信,没有凭着感觉确定下刀的位置,而是和刚刚开始学艺一样,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小母猪的腹部,然后用手术刀把刚才手指比划过的腹部像村口的剃头匠刮头发似得,嗖嗖几下,在小母猪的肚子上刮出一个粉嘟嘟,比五分钱硬币大不了多少的圆斑。温小雅从边上的那个腰子形盒子里拿个酒精棉球擦了擦这个裸露的皮肤,又擦了下刀刃,还没等站长看清,只听得“噗”地一声脆响,温小雅按着刀口的拇指指尖已经冒出了一个布纽扣样的东西,上面全是米粒大小的葡萄仔。温小雅扯住这葡萄仔,像拉渡船一样,慢慢地扯着。扯了一会,按在刀口的拇指指尖又跳出了一串葡萄仔。温小雅把这两串葡萄仔捏在一起,用刀小心割下,把跟着葡萄仔出来的那些弯弯曲曲、盘旋缠绕的枝枝蔓蔓重新小心翼翼地塞入刀口,然后拎住小母猪的左后腿,任由小母猪喊叫、挣扎了一会,才放下。死里逃生的小母猪嚎叫着狂奔到草堆前,紧紧地挨着小公猪,无助地呻吟着。温小雅搓搓手,让沾在手上的鲜血能均衡地涂抹在手上,使得双手不再黏黏糊糊的难受。
如果说刚才小公猪的惨叫,给了正在喂奶的老母猪发怒预热,那么小母猪凄厉的惨叫,就成了老母猪发怒的促成。还没等站长、场长和还在搓手的温小雅回过神来,在猪圈里愤怒转圈的老母猪,似乎知道温小雅就是伤害小猪的凶手,突然一声嚎叫径直向温小雅扑来,吓得温小雅返身就往猪舍外面跑。
没等温小雅跑远,场长在后面叫了,喂喂,赶紧回来。温小雅停下脚步,转身一看,老母猪没有追出来,站长和场长却都蹲在猪圈旁边,刚才还勇猛无比的老母猪,现在躺在他们中间,痛苦地嚎着。
母猪因为救子心切,根本不知道喂猪的人为了防止它的出逃,特意在猪栏上钉了几块削尖了的木头。刚才老母猪奋不顾身的一跳,这尖利的木头正好划在肚皮上,红红的肚子上一半尺来长的伤口,翘嘴巴一样白乎乎的张开着。伤口里面的血没有像泉水般地往外涌,而是一丝一丝的慢慢往外洇,洇多了,也就把母猪的肚皮底下的烂泥地给弄糊了。温小雅的脚竟然有些抖,她虽然阉割过不少猪,但从没碰到过这种事,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温小雅还在发愣,场长早急得不行了,他朝温小雅吼道,你赶紧救治啊。温小雅颤着声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场长生气地说,不知道做什么兽医,逞什么能?温小雅还想辩解,给躺在地上痛苦哼叫的母猪轻轻挠着肚皮的站长对场长发话了,你去找针线过来。
场长赶紧从猪圈隔壁的床铺上找来针线递给站长。站长顺手递给温小雅,别慌,按照我说的做。站长平静的语气,让温小雅慌乱不堪的心慢慢的静了下来,虽然手还有些发抖,但穿针的线还是顺顺当当的从针眼里过去了。站长说,把伤口消毒一下,然后缝衣服一样把伤口缝住。大半个小时后,老母猪刚刚还豁着的两块肉已经像一块补丁一样平整地被缝合了。
站长等温小雅满头大汗做完这一切,笑了下说,做兽医就是要胆大心细,有事不可胆小,无事不可胆大,明天就来农技站报到。我要创公社先河,全县先河,招收一名女兽医。
温小雅进兽医站的第一件是就是去参加省农业学校的学习。原本只懂阉割的温小雅慢慢学会了家畜家禽的养殖、看病、用药、防疫,成了公社兽医站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经过正规培训,除了会阉割,还懂得养殖和治疗的兽医。
学习回来后的温小雅,刚好碰上一件大事。这事如果放在学校的课堂上,不是大事,但放在农村,放在一个村,一个公社,就是大事了。这大事就是公社有几个大队的牧场突然爆发猪瘟。不到十天时间,整个公社有好几百头猪都成了奄奄一息的病猪。牧场养的,家庭养的生猪每天都有死亡。因为不懂预防和扑灭,使得整个疫情有向周边区域扩散的趋向。这把农技站站长急得嘴上全是燎泡。温小雅去牧场走了一圈,明白以自己和其他三四个只懂得阉鸡阉猪兽医的力量,已经无法控制这个疫情了。于是,她立马赶回学校,好说歹说说动了学校老师,然后在他们的支持下,制定了详细的扑灭方案,购买了一批猪瘟疫苗,没日没夜的给猪打防疫针。
果然,猪瘟疫情很快被控制。整个事件完成后,温小雅很快被任命为公社兽医站站长,同时也成了公社,县里,直至省里和农业部的先进。因此,温小雅成了大名人,成了模范。那段时间,温小雅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病、阉猪,而是出席各种各样的表彰会、经验交流会,接受各种各样的奖项,演讲着一成不变的发言稿。
温小雅出名后,烦心事也多了起来。最大的烦心事就是婚事搁浅。原本她没出名的时候,追求她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有人牵线,做媒。追求的人一多,温小雅就有东挑西拣的机会了。后来出名了,成先进了,追求的人反而没有了。
没人追求,温小雅并不着急,她有着自己的打算。其实说打算,也算不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人眼中优秀的男孩,在她眼里已经不再优秀,是自己的眼光高了,还是心大了,她不明白,直到有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熟悉飞名字,才突然发觉自己之所以挑不中那些优秀或不优秀,英俊或不英俊的人,是因为自己心里住着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她在相亲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的按照这个人的条件去套对方。人又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偶尔也会有瑕疵出现,同样两个看似一模一样的产品,其实有着区别,而且不是一般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这个人就是刘晓辉。
刘晓辉是温小雅的高中同学。读了一年的高中,温小雅最大的收获不是学到了知识,而是学会了写情书。当时,刘晓辉是班长,温小雅什么都不是,但温小雅就在那个多看几眼都是流氓行为的年代,给刘晓辉写了好几封情书,尽管没有收到刘晓辉的回信,但这记忆,一直铭刻心中,慢慢尘封。而现在,她突然看到了刘晓辉,那记忆的灰尘立马被掸得干干净净。此时的记忆,就像无意中踩上的一坨狗屎,虽然擦掉了,洗干净了,但只要偶尔想起,脚底下依然会有似有似无的臭气出现。这刘晓辉就是温小雅曾经踩到过的那坨狗屎,就在她以为早就过去了的时候,竟然在她春心萌动的时候又散发出了那恼人的气息。
当然,温小雅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找不好对象是踩了刘晓辉这坨狗屎的缘故,那次去区卫生院,想找个医生给自己生在屁股沟里的一个疔疮开上一刀。到了外科碰上刘晓辉才猛然醒悟。刘晓辉高中毕业后,被公社推荐上了医科大学,读了两年大专后回区卫生院成了外科大夫。
刘晓辉给温小雅割了屁股沟里的疔疮,温小雅忍着痛拉起裤子强笑着说,我这地方可是连我爹娘都没见过,你得负责任。刘晓辉傻乎乎的回答道,在我眼里只有疮,没有屁股。温小雅说,你让我脱了裤子就得负责。刘晓辉疙瘩了一下后笑着说,不脱裤子我没法手术。温小雅说,反正你有点耍流氓。刘晓辉急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要是像你这样说的,我们医生怎么给病人动手术。温小雅撅着屁股,小心从手术台上下来,说,反正我要你负责到底了。刘晓辉还想分辩,可看着温小雅撅着屁股的样子,那滑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温小雅觉察到了,趁机咬牙切齿地说,让你笑,我还不走了。
刚好,这段时间上刘晓辉这里看病的病人不多,温小雅就坐在刘晓辉对面的椅子上,惦着半个屁股坐着看刘晓辉,原来都是对面这个冤家挡了自己婚姻的道。明白了这点,温小雅就七套八套地把刘晓辉的一切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次事情后,温小雅有意无意地向刘晓辉抛出了红线。好在一直让温小雅觉得木讷,不懂风情的刘晓辉,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也向温小雅展开了追求攻势。刘晓辉发动的攻势,在当时看来那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每天下班去兽医站接温小雅,还时不时的去医院边上的小山上折上几支映山红、迎春花、串串红,再不济,也会折几条柳枝编个帽子逗温小雅玩。刘晓辉上班有休息天,温小雅上班和休息都一样,所以,她索性不再休息,天天上班。于是,刘晓辉只要休息,就去兽医站陪温小雅,偶尔还相互探讨一下人病和猪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给温小雅提点意见和建议。有一次,公社牧场的一头刚生了小猪的母猪病了,温小雅看了下,认为母猪患了产后热,于是就按照产后热进行治疗。谁知,连续治了三天,根本就没有起色。眼看着母猪奄奄一息,十来头刚出生的小猪饿得皮包骨头吱吱叫,牧场的饲养员急了,因为养猪的好坏和他挣的工分挂着勾。温小雅也急,她也想把母猪治好,这样不但可以帮饲养员,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积累经验。就在这个时候,刘晓辉出马了,他拎着两瓶已经加了青霉素的葡糖糖生理盐水,跟着温小雅来到牧场,把母猪当成了人,让两瓶葡萄糖生理盐水通过静脉挂针,全部进了母猪的身体。说来也怪,就挂了这一次,本来奄奄一息不吃不喝的母猪竟然开始进食了。
母猪的起死回生,让温小雅成了医治猪病的华佗。虽然外人心里清清楚楚,这一切其实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歪打正着,可是,不管怎么说,让大家都明白了人医兽医是可以互补的,温小雅和刘晓辉这样的组合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黄金搭档。
刘晓辉的主动,让心中本来就有着他的温小雅如何能抵挡得了。很快,在刘晓辉那个逼仄的单身宿舍里,一个兽医,一个人医,殊途同归做成了千古不变的风流韵事。
刘晓辉婚后的表现,让温小雅越来越骄傲自己的眼光。结婚后,温小雅发觉刘晓辉身上的优点也越来越多,不说别的,就说每天给自己做饭,洗衣服,把自己的话当圣旨一样,在农村不是少见,简直就是稀有。还有刘晓辉虽然是大专生,但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多的在农村看来必须去县里大医院的手术像割阑尾这样的手术,他都能做。农村医院虽然要值班,但病人少,所以刘晓辉上班下班还是相当的规律。而温小雅的上下班基本没有规律,不管在家还是在兽医站,只要有人来叫,温小雅都得背上药箱出诊。无论她多迟回家,刘晓辉永远会等着她回家吃饭。
可这个最佳组合不到一年很快出现问题了。因为温小雅的敬业以及说一不二的强势,让刘晓辉越来越难以忍受。小时候因为家穷,一直被人看不起。虽然在高中毕业刚刚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的时候,被推荐上了大学,但小时候的自卑依旧像三九寒冬突然融化渗入沙土的冰水一样,看着没了影子,但只要天一冰冻,这些冰水依旧会在沙子底部牢牢的冰冻,无法融化。所以,自卑,让他在大学时候只能羡慕别人谈恋爱,自己却不敢恋爱。参加工作后,向他抛绣球的女孩不少,可这些女孩在上过大学的刘晓辉眼里看来,都是些无法入眼的粗俗女子。
沁入骨子的自卑,让他在无法强势却又不甘落俗的痛苦中挣扎。就在这个时候,温小雅出现了。温小雅的强势侵人,让刘晓辉一夜之间忘记了自卑,忘记了粗俗,他很努力的经营爱情,很快乐的享受爱情。但时间一长,他才明白,爱情是浪漫,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婚姻是现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强势的女人永远是强势,虽然刘晓辉占了温小雅倒追的优势,可这个优势对刘晓辉而言,等于没有优势。
在家里基本没有话语权的刘晓辉突然后悔结婚,这个心念一出,他再也没有心思去经营婚姻,经营生活,连工作也变得混日子一般。日子,在刘晓辉眼里已经没有了阳光,整天的灰暗让他开始变得不修边幅,邋里邋遢。
刘晓辉的颓废,温小雅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越是这样想,越是堵心。于是,两人开始有了吵闹。很多事情都是有一必有二,有二就成了常态,很快,本来平平和和的两个人,变得大吵不断,小吵不绝。
当然,矛盾的爆发往往是很多小矛盾积累到了极点,在急需一个出口爆发的时候,哪怕一点点小事,都有可能让小小的矛盾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把人、把感情、把婚姻爱情炸得千疮百孔。刘晓辉和温小雅的矛盾慢慢的积累着,但还没到爆发点。可就在这个时候,温小雅竟然出手提前找到了这个爆发点,而且还毫不犹豫的引爆了。
温小雅引爆矛盾的爆发点是肚子里的孩子。孩子对刘晓辉而言,其实就是和温小雅两人生活中娱乐的副产品。尽管是个副产品,可却是必不可少。很多人因为无法生产出这个副产品,天南地北的奔波。而刘晓辉在娱乐的同时,无意中把这个副产品给搞了出来,这让刘晓辉高兴得像老鼠掉进了油瓶,兴奋得不知道如何下手。温小雅知道这个消息后也是如此,当她从卫生院的产科医生那里得到这个信息后,激动得恨不得孩子马上就出来。可是,这个兴奋没持续多久,温小雅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

那段时间,刚好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机构开始改革,公社改成了乡,大队改成了村。牧场开始慢慢关闭,农民单家独户养猪养鸡的越来越多。特别是养猪,政府还有补贴。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了起来。兽医站里的兽医,也由以前的记工分年底拿分红,变成拿国家工资的政府机关部门干部了。因为有了干部身份,本来就是热门部门兽医站更成了抢手货,好多有技术,没技术,懂阉割,不懂阉割的人都想着法子进兽医站这个蜜罐子。
在这样的关键时候,温小雅怎么能生孩子呢。她一怀孕生孩子休产假,无疑是给人腾位置,这种事可不是她的风格,她也不想这样做,更不能这样做。她要把兽医事业坚持下去,直到退休。于是,她瞒着刘晓辉到乡计生办打了个证明,跑到县医院把孩子打了。刘晓辉一直要到一个多月后才知道。
从不发火的刘晓辉彻底发飙,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刘晓辉的举动,让温小雅心里存着的一丝愧疚彻底消失,激怒之下,竟然说了句离婚。这话一出,把刘晓辉吓了一大跳,他虽然不满温小雅的霸道,自私,可是他从没想过离婚两字。再说,他家中六个兄弟姐妹,就他一个是挣工资吃商品粮的,要是离婚,让家里人怎么在村里人面前抬起头来。于是,他只能忍。忍着,忍着,学会抽烟了,学会喝酒了,学会颓废了。
原本话多的刘晓辉话少了,单位里的同事并没有觉察到不正常,因为他经常这样。可有一个人看了,觉得不正常,这个人就是护士张红梅。张红梅和刘晓辉是同一个村的,虽然不能说是青梅竹马,但也能算是知根知底。以前张红梅对刘晓辉没有多少感觉,可是,当她卫校毕业,分配进区卫生院看到穿着白大褂、寡着脸坐在外科诊室给人看病的刘晓辉,仿佛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立马毫无来由就喜欢上了刘晓辉。可惜,当时的刘晓辉却看不上相貌平平的她。暗恋,让张红梅时时处处的关注。这样的关注,终于在刘晓辉颓废的时候起作用了。很快,刘晓辉在卫生院的单身宿舍成了他和张红梅的快乐地。
温小雅一直以为刘晓辉不敢出轨,也不会出轨,因为家里的一切都被她死死的掌控着,他有什么资本出轨呢?可现实让她不得不接受。于是,她软硬兼施,开始跟踪,盯梢,吵闹,打骂。这样的方式果然有效,刘晓辉似乎已经和张红梅断绝了来往。可是,成果没保持一个月,温小雅还没有放松警惕的时候,刘晓辉又旧病复发,只是把浪漫地换了个地方,从单身宿舍换到了张红梅家。温小雅又拿出农村的泼妇相,把刘晓辉和张红梅的脸挖成了大花脸。
面对这样的结果,刘晓辉说,我们离婚吧。温小雅咬着牙齿说,不离,就是不离。刘晓辉小心地擦着脸上的血迹说,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不离婚就这样拖着有什么好处呢。温小雅歇斯底里地说,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刘晓辉说,我都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名声可以败的。说完就顾自走了。确实,温小雅知道刘晓辉出轨,她在找刘晓辉、张红梅发作前,先去找了卫生院的领导。在生活作风问题大如天的时代,刘晓辉就是有起死回生华佗般高超的医术,也得接受处分,因此,他从一名医生被贬成一名普通的勤杂工。所以,当温小雅说要让刘晓辉他身败名裂,刘晓辉听了反而笑了,他觉得这实在是太可笑了,自己已经从王子到乞丐了,还有什么名声可裂,这样一想,他反而坦荡了。
刘晓辉决定豁出去了,张红梅当然紧跟这也准备豁出去了,她决定,就是被医院开除,也要跟着刘晓辉了。但温小雅却退缩了,她不能因为离婚成了别人口中的话把。
温小雅和刘晓辉不死不活地拖了两年,这两年间,谁都没有理谁。温小雅继续做她的兽医,做她的先进。刘晓辉毕竟一技在身,做了几天勤杂工后,又回到了医生岗位。
忽然有一天,温小雅托人带了个口信给刘晓辉,让他晚上有空的话回家一趟,有话和他说。刘晓辉不知道温小雅会怎么对他,哪敢回去,就躲在医院的宿舍。温小雅回家后,天黑都没见刘晓辉回来,就骑着自行车找到医院,倚在刘晓辉的宿舍门口轻声细语地说,这么两年下来,大家都身心疲惫,我有些事和你谈,跟我回去吧。
男人就见不得女人温柔,见温小雅这样一说,刘晓辉心里一阵涟漪,毕竟曾经爱过,好过,毕竟自己出轨在先,毕竟没有交恶到水火难容的地步。于是,刘晓辉破天荒地坐在温小雅的自行车后座上,乖乖地跟着温小雅回了家。
温小雅烧好的几个菜,放在桌上,已经有点冷了。温小雅一改以往刘晓辉在从不下厨的习惯,系上围裙,下厨把冷了的菜重新热了一下。又拿出一瓶酒,两个杯子。于是,已经吃过饭的刘晓辉在温小雅温软的劝说下,喝下了大半瓶酒。酒乱人性。暖暖的酒意,让刘晓辉看着温小雅依旧娇艳的脸,能掐出水来的身子,心也跟着动了起来。很快,长久不做的运动又重新启程。
激情汹涌的潮水退去,温小雅和刘晓辉仿佛是躺在沙滩上两条筋疲力尽的鱼,睁着眼睛,却无力跳动。温小雅像以往那样,用手轻柔地抚摸着刘晓辉的下身。刘晓辉慢慢地闭上眼睛,舒服地享受这个过程。
温小雅忽然支起身,边轻柔地揉着刘晓辉的两个蛋蛋,边贴着刘晓辉的耳际说,舒服吗?沉沉睡去的刘晓辉迷迷糊糊的“嗯嗯”着。揉着,揉着,温小雅突然起身从边上的梳妆桌上拿过那把阉过无数公猪的手术刀,手起刀落。刘晓辉的两个蛋蛋就和普通公猪的蛋蛋一样,热乎乎跳进了温小雅的手心。
迷迷糊糊的刘晓辉被一阵剧痛痛醒,睁开眼睛,只见温小雅捧着两个圆圆的东西跪在身边,而自己的下身鲜血淋漓,顿时明白过来。伸手就抢温小雅手上的蛋蛋。温小雅冷冷一笑,手一挥,两个掌握男人命根的蛋蛋就准确无误地飞进了床边的马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