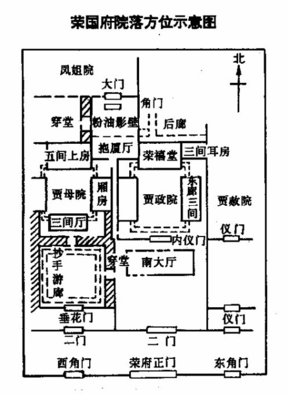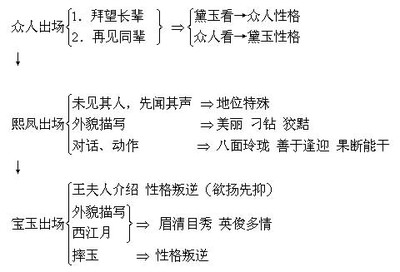我很喜欢这个叫林和生的人,手头有他的不少著作,包括诗集、学术作品、还有其他研究成果的集结,质量都堪称上乘,尤其是他的译作《拒斥死亡》,让我不忍释卷,每日睡前看一会就索性抱着睡觉,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在我的心中堪与《百年孤独》比肩,甚至比后者还要深刻的多。林和生漂亮而富有激情的译笔让我对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奥托.兰克诸人深邃思想的阅读有了可能。不需要隐喻和暗示,《拒斥死亡》以字句的锋芒直刺血肉模糊的人生,我每每阅读之际,心中的激动久久难平。
然而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昨天在社科院的时候,无意中说起他,我们的总编笑道:你这么喜欢他啊?想不想见嘛?我还真吃了一惊,马上问道:见得着?哪儿见?原来林和生是社科院的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这可不是天上掉馅饼么?总编帮我约定了时间,恰好林老师今天有课,讲的是“艺术创造心理学”,他邀请我今晚去旁听,我正中下怀,忙不迭答应了。
钱钟书爷爷说:“你既吃了鸡蛋觉得好,又何必非要看那下蛋的母鸡呢?”可是没办法,我就是那种吃了鸡蛋还想看母鸡的人,在成都这些年来,我已经陆陆续续地见了不少还能下蛋的母鸡,有优秀的鸡也有很糟糕的鸡···
当我推开教室的门时,林老师已经在授课了,我其实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想象他应该是一个很孱弱的人,然而,他的眼神是坦然的,他的容貌几乎可以说是端严的,他的身体居然看上去也很壮健,是一个极有艺术家气质的中年人。林老师问了我的名字,非常欢喜,向在场的大约七八位同学介绍了一下我,我粗略看了一下,各位的年纪虽然也都不小,但看上去都一脸学生气,而我黑西装的装扮,确实扎眼了些,便有点不自在起来,向大家欠了欠身,找了个空位入座了。
我的心又开始剧烈的跳动。
林老师这节课的导论是“向死而生”,讲到他最推崇的两位天才,卡夫卡和梵高,他称他们为“创造型艺术家典型中的典型”,还以韩寒方舟子之战为大家讲解了“日常形式的死亡”和最高形式的死亡之别。
他语速很慢,然而这慢并不是那种约定俗成的官方腔调,而是为了措辞精确,有所斟酌之故,但偏偏他的措辞又并不配合他的语速,他清明而光洁,我再不能比在这节课堂上还更能明了他的爱憎。由于人类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因此而困囿种种欲望,他自责地向我们坦陈了自己的“贪得无厌”——有两套住房:成都一套,老家一套便于自己回去养老。也许,占据了超过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即是罪状。但是为什么即便我只是一个庸常的倾听者,倾听一位长者的忏悔,也感觉自己是在跪受着神典?
我想我无法述说自己的感觉,一切只因为林老师的那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里有我没有没有见过神光,几乎是一种泪光莹莹的悲悯,我相信我会在这一双眼睛的凝视中得到救赎。
在场的同学似乎都比较木讷,吝于言词。我憋了一肚子的问题,为了避免别人的厌恶,也只敢蜻蜓点水的问上几句,即便如此我和林老师互动也相对较多。林老师的态度始终谦和而循循善诱,我喜欢他专注的目光和顿挫的语感。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久违的少女时代,懵懂无知,怀着巨大的憧憬聆听老师的教诲,心中是满溢的喜悦。

我享受这一刻的错觉,而现在,只有林老师可以给我这种错觉。
林老师对诗歌推崇备至,他说,自己的所有著作也抵不过一首好诗。而他的诗歌也是那种风骨端净的作品,一字一句都是辛苦锤炼得来,少了灵秀却多了几分纯美。这份与大众消费时代无缘的爱直接注解了他清贫孤苦的生活。然而林老师不以为意,他说“总会有人倾听。”《岸》。
我愿意就这样坐在台下,安静的倾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