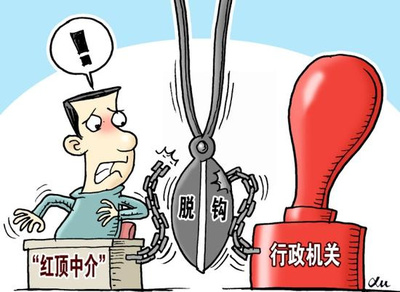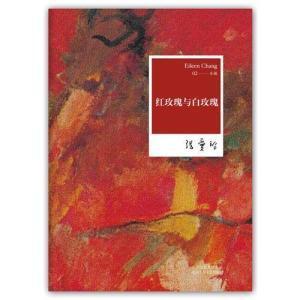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上海这样传统:古老的家族、神秘的大宅、浓重的吴音,弥漫着永远抹不去的怀旧心绪;然而,那时的中国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上海这样现代:洋场的灯火、风云的变幻、各国的来客,夹杂着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的人心。时代与地点造就了张爱玲传奇的矛盾,因而她小说中的人物永远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构筑了一片永恒的苍凉风景,《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是这样一篇佳作。
一个人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一个女人的一生是最美丽的传奇,张爱玲小说中女人的美丽却永远带着苍凉。女性是张爱玲写作的中心,女人最了解女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中国的女性所受传统压迫最为严重,因而现代一旦来临,要求解放的呼声也最为强烈,然而由于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尚未协调的夹缝中,这时的女性既保持不了传统也完成不了现代,无所适从感一直笼罩着她们。娜娜究竟该不该出走?出走的结果是堕落还是回头?张爱玲对这些思考的深刻决不亚于鲁迅。
《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女性是传统与现代的两个典型化身,文章开始就表示:“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然而,无论是白玫瑰烟鹂还是红玫瑰娇蕊,尽管她们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极端,等待她们的都是悲剧。如果说白玫瑰的悲剧是由于传统,那么红玫瑰的悲剧则缘于现代。
烟鹂是男性眼中理想的妻子形象:文静、温顺、内敛,是“圣洁的妻”。自从结婚以后,她传统中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受了西方文明熏染下的男性眼中,都变成了不足,现代之中的传统女人是令人乏味的。振保对烟鹂传统的回报是在外面公开的玩女人,当着她的面砸东西。面对男性的放荡与无情,烟鹂最终也突破了传统所需要的淑女形象,作出了越轨行为,和一个远不如振保的裁缝偷情,张爱玲把一个欲守传统而不得的女性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
与烟鹂不同,娇蕊是新文明熏染下的女性。她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对于爱有着执着的追求,为了和振保在一起,她抛弃了一切,坚决提出和丈夫离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却是男人的无情,最终得不到所爱得人。时代新女性为残留的传统所不容,追求现代而不得的女性经历过伤痛后随即开始渴望回归传统。当娇蕊再次和振保在电车中相遇后已不再留恋,她嫁了人做了母亲,并安于这样俗艳的平庸,尽管话语间充满了对往事的伤怀与哀悼。
传统对女性的要求永远是贤妻良母,处于被控制被奴役的地位,没有一丝的生机和活力,这样的传统女性已落伍于时代。她们的平庸、自我压抑、顾影自怜、婢妾似的怨愤远远不合当时男权社会的要求,只是作为男性购置的花瓶,或当作旧时的屏风,摆设而已。所有的这一切使白玫瑰们对传统产生了怀疑,有了一丝摆脱的渴望。对于红玫瑰们来说,她们的热烈、自由、奔放、西化的生活方式、不顾一切大胆的追求很能满足沉湎于物欲与情欲之中的男权社会,不过,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男权世界大多表面维持着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通常把这类西化的女性当作生活的调剂,闲暇时的玩物,构筑一番天长地久的爱情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现实,这类女性或堕落、或毁灭,或者再回到传统之中,就象一只苍蝇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
女人在传统与现代冲突面前无能为力,男人同样也是如此。只是与女性不同,男性多了一些自由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主人公振保从表面看来似乎能在传统和现代女性之间游刃有余,文本这样描写:“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的,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不过无论如何潇洒,张爱玲传奇中的男性依旧是享受着现代文明但却摆脱不了传统的人:一方面,现代生活的侵入让他们感受到了婚姻与爱情的自由;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依旧像巨蟒一样箍紧他们,他们同样要面对现代和传统的不可两全的局面。
振保出生微寒,如果不自己争取自己,便“一辈子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圈子里”。后来他出洋得了学位并赤手空拳的打了天下,因而有了体面的工作、古典的妻子、众多的亲戚朋友,表面热热闹闹地周旋于现代于传统之间,其实内心深处永远潜藏着深深的贫乏与无奈。后来他在娇蕊面前痛哭一场,完全暴露其内心的苍白。在处理与女人的关系上,振保也保持着现代与传统的中庸: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对于娇蕊,尽管他十分留恋,但却不愿对抗传统,这点可从他对娇蕊的话中看出:“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同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个人,社会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士洪到底是我的朋友。”(《红玫瑰与白玫瑰》)对伦理与社会传统的顾忌,不得不使他离开娇蕊,他选择了烟鹂,又无法忍受传统的死板与琐屑,于是变得比以往更放荡,他最终成为了自己得奴隶。
象振保这样的男性在张爱玲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如娄先生(《鸿鸾禧》)、范柳原(《倾城之恋》)、乔琪(《沉香屑:第一炉香》)等等。范柳原出身于现代文明中的非正常结合,是出洋的父亲和伦敦一个交际花的私生子,他为此吃了好多苦,才获得了继承权。本来象他这样无意于家庭幸福的男子是不想承担责任的,由于战争他还是回到了传统之路,结局却十分令人惆怅。爆发户的娄先生、只会玩的乔琪都是在这样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尽管尽力去弥合传统与现代的裂痕,却只能使得自己的生命变的无可奈何。
男女的不幸看似彼此双方造成的,却隐藏着深层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与文明间的错位使得人与人之间美好纯真之情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心灵建造一个牢笼。费勇在评论《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人物时说过:“三个人都是失败的:佟振保没有创造出一个‘对’的世界,也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红玫瑰没有成就自己的‘热烈’;白玫瑰更没有实现自己的‘圣洁’。三个人的五官最后都是灰色的一片,点缀在这个灰色的人世。”这些悲剧性的结局使得张爱玲的传奇永远笼罩着一种苍凉的氛围,这种苍凉来源于面对现代与传统交杂的矛盾世界的无奈与迷茫。
传统与现代的不能两全性给张爱玲的传奇染上了悲伤的色彩,苍凉成为她小说的主要基调。川嫦(《花凋》)面对病魔无法留住自己的爱人,在怅惘与失意中凄然离世;许太太(《心经》)自知女儿与丈夫之间有着违反伦理的依恋,只是在默默忍受中看着丈夫的离去;娄太太(《鸿鸾禧》)表面似乎维持着平和的家庭,其实却忍受着最大的寂寞与不幸,至于葛薇龙、白流苏、顾蔓露等更是不由自主的从传统向现代中堕落,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玫瑰的悲剧。同样,“红玫瑰们”也面对现代和传统不能两全的悲剧,现代女性如同娇蕊一样在找回自由的同时,一样的失去了自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提出离婚,这当然极具现代意识,然而随即她便陷入了大家庭的攻击中,四面楚歌,最后不得不从找归属,回到原有的圈子中去;曹七巧用了半辈子的青春,获取了金钱,却给自己套上了黄金的枷锁,人性极端扭曲变形;对爱充满追求的霓喜却陷入了欲的海洋中,一无所有的为自己凭吊。所有的这一切便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中处于现代与传统文明夹缝中女人悲凉艳丽的伤感传奇。
红玫瑰娇艳风流,白玫瑰清纯圣洁。但是在现代的转型时期,女性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既无法保持自己的圣洁,也无法永远热烈,幸福总是和她们擦肩而过,因此留在她们深色的背影后面的只能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永恒的苍凉风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