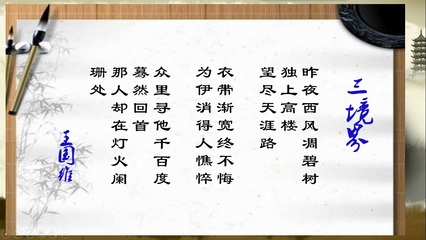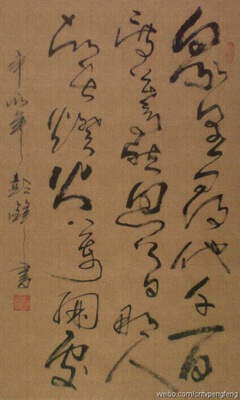迦南;迦南人(CANAAN, CANAANITES)
一个说闪族语言的民族;他们的地域,主要在腓尼基。他们的种族渊源,现今已不能确定。
Ⅰ 名称
迦南这个名称(来:k#na`an),用在民族或地方上,都是从他们的祖先迦南或迦拿(Kna`)而来的(见上一个条目)。这是根据创十15-18和迦南-腓尼基本土的传统而得到的观念。这些传统,由桑丘尼亚托(Sanchu-niathon)传下来,又由比布罗斯的非罗(Philoof Byblos)保存了。希腊文一些资料和腓尼基人自己,都采用迦拿(Kna`[an])作迦南腓尼基人在本土的名称(如:钱币:见 W. F. Albright,于 'The Ro%le of theCanaanites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一文,页1,注1,文章刊于 The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Essays for W. F. Albright,1961,页328-62;以下简称 BANE Vol.)。Kn` (n)这个字的意思不得而知,在圣经以外,这字也有出现过,有时有最后的 n 有时没有。这个 n字可能是闪族文字常见的末尾的n,或许是户利文(Hurrian)所用的词尾(Albright,上引书,页25,注50)。昔日,有学者把“紫色染料”所用的字〔尤其是在户利文中〕和Kn` [n] 连系起来(如 Speiser, Language12, 1936,页124),但这个建议被兰斯伯杰(Landsberger)所推翻(JCS 21,1967,页106-7)。
Ⅱ 迦南的版图
无论在圣经或外界的资料中,“迦南”有三重意思。
1.基本上,迦南是指叙罗─巴勒斯坦(Syro-Palestine)沿岸的地方和居民,尤其是指腓尼基。创十15-19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这段经文详细的列出了迦南的子孙,包括“长子”西顿、*亚基人、西尼人、洗玛利人和在俄隆提斯河的哈马。民十三29;书五1,十一3;士一27起更特别指出迦南人是在沿海一带,在山谷及平原,和在约但河谷的,而亚摩利和其他人则在山上。值得注意的是,主前十五世纪的亚拉拿王(Kingof Alalah)伊德米(Idrimi),在碑文中提及他逃亡到迦南沿岸的阿美亚(Ammia)(S. Smith, TheStatue of Idrimi,1949、页72-3;ANET 3,页557-8)。
2.广义来说,“迦南〔人〕”也包括了内地,即泛指叙利亚巴勒斯坦(Syria-Palestine)。例如,创十15-19也包括了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希未人及革迦撒人,作为“迦南的诸族分散了”的解释(18节);这较为辽阔的土地,从西顿沿岸一直伸展到迦撒,然后直达内陆死海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而似乎再向北,直到*拉沙(位置不详)。另见:创十二5,十三12或民十三17-21,卅四1-2,及下文对巴勒斯坦西边疆界的厘定;士四2、23-24称夏琐王耶宾二世为“迦南王”。这广泛的用法,在早期圣经以外的资料也出现过。在他们的亚玛拿信件(主前十四世纪),巴比伦和别处的众王有时采用“迦南”这个名词来泛指埃及的叙罗巴勒斯坦属土。而主前十三世纪的埃及阿纳斯塔斯蒲纸(PapyrusAnastasi) IIIA,(第15-6行)和IV(16:第4行),提及一些“从赫鲁(Huru)来的迦南奴隶”(赫鲁 =广义的叙利亚巴勒斯坦)(R. A. Caminos, Late-Egyptian Miscellanies,1954,页117、200)。
3.“迦南人”这个称号,狭义来说是指“商人,做买卖者”,贸易是迦南人最典型的职业。这个意思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伯四十一6;赛廿三8;结十七4;番一11。耶十17甚至用kn`t 这个字来指“货物,商品”。法老王亚门诺菲斯二世(AmenophisII)的一个石碑(约主前1440),列举了他的叙利亚俘虏,其中有“550个 maryannu〔相等于贵胄的马车战士〕,他们的妻子共240人,640个Kn`nw,232位王子的儿子,323位王子的女儿”(ANET,页246)。梅斯利尔(Maisler,BASOR 102, 1946,页9)从这份记录推断,Kn`nw(迦南与权贵并列的640人)乃是商人,是“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沿岸和贸易中心的豪”;不过,这是不能肯定的。
Ⅲ 迦南人和亚摩利人
以上提到“迦南〔人〕”这名称,具有特殊、广义及狭义二种含义。同样的*“亚摩利人”这名称也有它特殊以及广义两方面的含义。狭义上圣经里的亚摩利人是指巴勒斯坦山区民族之一(民十三29;书五1,十一3)。但广义来说,“亚摩利人”倾向与“迦南人”的用法重叠。首先,根据创十15-16的记载,“亚摩利人”乃是从“迦南”而出的。之后,根据民十三17-21等等,以色列要征服迦南(=巴勒斯坦),而日后他们果然定居在亚摩利人之地,征服“所有在那地的居民”,就是亚摩利人(书廿四15、18)。神应许赐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在此之前他已来到这地(创十二5、7,十五7、18),但却要延迟占领那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十五16)。示剑是迦南一个主要的城镇,由一个希末人的领袖管治(创十二5-6,卅四2、30),这个人也可被称为“亚摩利人”(创四十八22)。
文学批判学的底本论(documentarytheory),经常以迦南人和亚摩利人这些名称(和其“他成对”的名称)重叠或重复的出现,来作为不同作者的标记(见 S. R.Driver,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OldTestament9, 1913,页119,或 O. Eissfeldt, The Old Testament, andIntroduction,1965,页183)。不过,这种理论是应受质疑的,因为圣经以外的资料,有时用“迦南人”,有时用“亚摩利人”,而这并不是因为背后有不同作者之故。
亚拉拿泥版(Alalahtablets)显示,在主前十八世纪,阿木如(Amurru)是叙利亚的一部分,而在与巴勒斯坦本土的夏琐有关的一份马里文献中,则提及亚摩利的众王子(参J.-R. Kupper, Les Nomades en Me*sopotamie au tempsdes Rois de Mari,1957,页179-80)。夏琐既是巴勒斯坦北边最卓越的迦南城镇,因此,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就证实有混杂的人种和用语。在主前十四或十三世纪,位于阿迪─亚述塔(Abdi-as%irta)的阿木如的王国、阿西努(Aziru)和他们在利巴嫩山区的承继者,藉着侵略和结盟,紧紧的制了腓尼基海岸的一段和它的迦南港,“从比布罗斯一直到乌加列”(AmarnaLetter No. 98)。有关*亚摩利人在迦南沿岸的控制,在兰塞二世(Rameses II)论到迦底斯之役(Battle ofQadesh)的碑文中进一步的被证实(主前十三世纪)。碑文提到从“阿木如地的一个港口”合时来到内地的一般战争的势力(有关这事,见Gardiner, 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 I, 1947,页188*-9*,和Gardiner, The Kadesh Inscriptions of Ramesses II,1960)。这是一个独立的证据,证明在摩西时代亚摩利(人)的含意,与迦南(人)的含意相近。因此,将这些名称视为出于不同的文学手笔的标记,乃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五经和约书亚记交替使用“亚摩利”和“迦南”这两个名称所反映的情况,在主前十三世纪末期已经因着海上居民定居巴勒斯坦的影响,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这日期以后,这种用法的出现是无法解释的。
Ⅳ 语言
“迦南文”的定义,极具争论性。在一般西北闪族的语言和方言中,圣经的希伯来文(参:赛十九18),在亚玛拿信件中的西闪族文的注解及用语,与摩押文和腓尼基文,都可以正确的被称为“南迦南文”。不同但相关的语言,有亚兰文和雅尤迪文(Ya~udic)。而乌加列文就在这两者之间。有人认为乌加列文乃是独立的一种西北闪族语言,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乌加列文是迦南文的一种,与希伯来文等同类。乌加列文本身显示这种语文随着历史的演变,有所发展,因此,主前十四或十三世纪的乌加列文,比起伟大史诗的古乌加列文,更接近希伯来文(Albright,BASOR 150,1958,页36-8)。因此,我们是可以暂时将西北闪族语文视为包括南迦南文(希伯来文等),北迦南文(乌加列文)和亚兰文。有关这方面,参:莫斯卡特(S.Moscati), The Semites in Ancient History,1959,页97-100。(他相当激进的)要取消“迦南文”这个名称;另参:弗德奇(J. Friedrich,Scientia 84,1949,页220-3)。“迦南文”和“亚摩利文”差不多是没有分别的,顶多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方言。西北闪族语文的 a{音与迦南语文的 o{ 音的异同,参:吉布 Gelb. JCS 15,1961,页42-3,两个音只有齿擦音方面的分别。从北叙利亚城*押巴拿得到的文稿,据辨字的皮提纳图(G.Pettinato)认为,是以一种似乎是西方闪族的文字写成的,与迦南文关系密切,皮氏称它为“古迦南文”(Orientalia新丛书44,1975,页361-74,尤其是页376起)。(*旧约的语言)
Ⅴ 迦南人的历史
巴勒斯坦在主前三千年期已经有说闪族语的民族在其中居住这一点,目前只有一份那个时期的文稿,可作证明。这份文稿中有两个地方名,是用闪语写的:Ndi~这个字其中的一部分是 ~il(u),有“神祇”的意思。另外一个字是 n.k.,是以ain(即:“水泉、井”)作为字首的。这两个字,出现于一个埃及墓窟的图画上,这个坟墓,是属第五或第六个朝代的,年份大约是主前2400年。
问题是,这是否能够证明迦南人曾住在巴勒斯坦,而迦南人又是什么时候在巴勒斯坦出现的呢?这是具争论性的。迦南人和亚摩利人肯定在主前2000年已经安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而约在主前2300年,北叙利亚的押巴拿已经有说西北闪族语的居民在其中居住。
在主前二千年期整个时期里,叙利亚巴勒斯坦划分为许多迦南或亚摩利的城邦,至于数目则时有变动。在主前十九或十八世纪,埃及人的咒诅祷文(ExecrationTexts)记载了许多地方和领袖的名字。有关这段时期,即族长时期,部分在巴勒斯坦的独立州郡的组织,另见:范塞尔(A. vanSelms),Oudtestamentische Studie/n 12, 1958 (Studies onthe Book of Genesis),页192-7。
大约在主前1500至1380年,这些小城邦,是属于埃及在亚洲的帝国的一部分。在主前十四世纪,北面的城邦转而受赫人管辖,而南面的则名义上仍然属于埃及人。主前十三世纪的早期,埃及再次有效地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岸(赫人仍守着叙利亚的北面和内陆),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埃及人就失去了对上述地方的控制(参H. Klengel, Geschichte Syriens, 1- 3,1965-70)。因此,在主前十三世纪后期,以色列人遇到迦南或亚摩利人的对抗,却没有特别与埃及人对抗(米聂他 [Merenptah]失败的突击是个例外)。约主前1180年,兰塞三世的“入侵”,是一次扫荡式的袭击,主要是在沿岸及主要路线上侵袭,而且很表面化。
主前十三世纪末期,迦南人或亚摩利人城邦的势力衰落,因而被政治上的激变所粉碎。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下,由约但河进入巴勒斯坦的西边,首先控制了山区和打败了一系列的迦南君王。对希伯来人来说,征服迦南乃是要成就神在古时对列祖的应许(创十七8,廿八4、13-14;出六2-8)。他们要撵走那地的人,因为神要把那些人驱逐,又要把余下的人消灭(参:申七1、2起)。这样做是因为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持续的犯罪,现在受到神的审判(申九5;参:创十五16),而不是因为以色列本身有什么的功德可言。
当时,埃及文献中记载的海上居民(包括非利士人),已将赫人的帝国打败,又横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直至在埃及边境被兰塞三世所制止;有些人,特别是*非利士人,就在巴勒斯坦沿岸定居。最后,在跟着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渗入叙利亚内陆的亚兰人亦迅速增加。结果,迦南人那时统治的,就只有腓尼基本土和它的港口,另外,也统治一些位于别处的零星藩国。从主前十二世纪开始,以前铜器时代的迦南人,在新的,受限制的环境下发展成为主前一千年期以航海著称的*腓尼基人,以著名的*推罗和*西顿王国为中心。有关迦南人的历史,尤其是日后发展为腓尼基人的历史,见:奥伯莱(Albright),BANEVol.,页328-62。
Ⅵ 迦南人的文化
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主要来自两个资料来源:第一是文学方面,在*乌加列(叙利亚海岸上的沙呣拉角)所发现的北迦南和巴比伦文稿,以及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零星文稿;第二是考古方面的,指那些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城镇和墓地出土的物件和遗迹。
a. 迦南人的社会
大部分迦南城邦是君主专政的。君王拥有军事方面的委任及征兵的广泛权力,又有权力征收土地和将土地出租,换取服务;更有权立税,税项包括什一税、关税、地产税等等,又有权强迫劳役,在庶民中征召劳工为国家服务。撒母耳所斥责的君王制,也就是直接指以色列邻国的这种君主制度(撒上八,约主前1050)。另外,在亚拉拿(Alalah,主前十八-十五世纪)和乌加列(主前十四-十三世纪)的泥版,也清楚提过这种政制(见I. Mendelsohn, BASOR 143, 1956,页17-22)。君王直接控制了军事、宗教及经济,王后是个重要人物,有时高级官员会向她求助。在较大的城邦,像乌加列,宫庭有精密的组织(有关乌加列的宫庭,参A. F. Rainey,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Ugarit,1962)。
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主前十九至十五世纪期间,来自乌加列的北迦南人的伟大史诗(见:下列的文学一栏),展示了家庭生活的主要特征(见A. van Selms,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in UgariticLiterature,1954)。至于主前十四或十三世纪的情况,法律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比较大的社会组织,包括城镇和有关村落的这些明显的大组织(在乌加列的这些城镇和村落,见Virolleaud, Syria 21, 1940,页123-51,另参 C. H. Gordon,UgariticLiterature,页124的简述)。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料,与约书亚记十三章起提到的城镇和村落作比较。除了以上这些大组织以外,也有一些分布很广的同行业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基本的生产者(牧人、猎禽者、屠夫和面包师传)、技工(铁匠、铜〔或青铜〕匠)、银匠、陶匠、雕刻家和建筑(房屋、船只及战车的)工匠,和在本地或来往外地的贸易商人。祭司和其他宗教上的人员(参下),还有乐师,也成立了工会或组织;另外,又有几种特别阶级的战士。在巴勒斯坦发现一些雕有文字的标枪或矛头,大概属于主前十二或十一世纪后期的迦南雇佣兵,像西西拉或耶宾所领导的那一种人(士四等等);这些雕有文字的戟、矛也显示,在士师时期的巴勒斯坦,人们经常运用早期西闪族的字母式文字。有人认为在主前十三世纪的巴勒斯坦,迦南人的社会明显有上流贵族与低下阶层的半自由农奴的划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成为对比。考古学发掘了的地点似乎显示以色列人的物质水平较低,而且阶级平等。
b. 文学
这方面主要的代表来自*乌加列的北迦南文献,包括:冗长却零乱和零碎的巴力史诗的片段(巴力或哈达的事迹和命运),这里面的文字大概可追溯到约主前2000年;亚奎赫(Aqhat)传奇(好王但理,[Dan~el]的独生子的盛衰),大约是属于主前1800年;克瑞王的故事(Keret;他痛失家园后,他的新妻子差不多是俘掳回来的,他也招致众神祇的忿怒),大约属于主前十六世纪;还有其他文稿的残片。所有现存的文稿,都是属于主前十四或十三世纪的。早期史诗那些辞藻夸张的诗歌,在用字及遣词造句上清楚的说明了旧约许多的希伯来诗歌带有古旧的风味。史诗的完整翻译(内容对早期迦南人的宗教很重要),见C. H. Gordon, Ugaritic Literature, 1949; G. R. Driver,Canaanite Myths and Legends, 1956; A. Caquot, M. Sznycer, A.Herdner, Textes Ougaritiques I, 1974。H. L. Ginsberg 的ANET,页129-55和 J. Gray 的 DOTT 提供了其中部分的选集。
c. 宗教
迦南人信奉的神祇很多,以伊勒(El)为首。但在实际的敬拜上,主要的神祇乃是*巴力(主),即暴风神哈达(Hadad)和*大衮,在乌加列和其他地方都有其庙宇。女神*亚舍拉、*亚斯他录和亚拿特(Anath),像巴力一样,具有多重个性和残暴的性格,她们是性和战争的女神。科撒尔-哈西斯(Kothar-and-Hasis)是技工的神祇(参Vulcan),而其他较不著名的神祇亦大量存在。

巴勒斯坦昔日的庙宇,今日留下遗迹的,见于伯珊(Beth-shan)、米吉多、拉吉、示剑,尤其是夏琐(最少有三间),除此以外,有些是在叙利亚的夸特那(Qatna)、亚拉拿和乌加列。乌加列文献提及将多种不同的动物献给神祇为祭:牛、羊(山羊及绵羊)和雀鸟(包括白鸽)。当然,亦包括奠酒。在巴勒斯坦地几个地点发掘出来的动物残骸,给我们看见同样的一幅图画。
大祭司的称号(rb khnm),已被证实用于乌加列的迦南人的宗教上。乌加列文献中的 qhs%m字,很可能是指庙妓。无论如何,qds%m是构成迦南宗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也是神绝对禁止以色列拥有的(申廿三17-18等等)。在主前二千年期,迦南人的宗教用人来献祭的事,虽然考古学上未能肯定,但有迹象显示这是当时的一种习俗。乌加列文献及源自闪族或灵感来自闪族的埃及文献,清楚证实迦南人的宗教诉诸人类的兽性和唯物的特性;参:奥伯莱(Albright),Archaeologyand Religion of Israel3,1953,页75-7、158-9、197,注39;另见*金牛犊。我们若完全了解这方面,就更清楚知道,无论在物质上和灵性上,这种复杂鄙劣、衰败的迦南文化,绝对不能与新建立且有独特使命的以色列并存不悖。
图/迦南与邻近的地区
书目:A. R. Millard, in POTT 'TheCanaanites',页29-52。至于在乌加列的发现,见:从1929年开始,薛华(Schaeffer) inSyria 的报告,and Schaeffer, Virolleaud and Nougayrol所著一系列例证详尽书册,Mission de Ras Shamra。
K.A.K.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