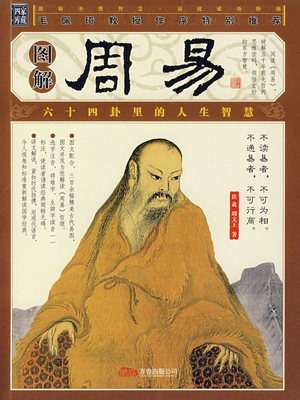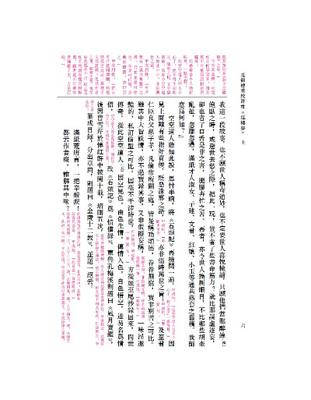下边文章均发表于天津日报
风物长冝放眼量
周伦玲
1968年9月5日,父亲周汝昌照常去上班,中午却没有回家,在全家人焦虑地等待中,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人了,让立即去送被褥。等我们赶到出版社时却没能见到父亲,看到的只是遍地贴着父亲名字和上面划着大红叉的革命标语。
父亲被扣压,开了“斗争大会”,关进“牛棚”,打成“反革命”。
这一切,直至父亲离去,他也从未和我们讲起过,自然我们也不愿去触及,只能从他的一篇《关起来的滋味》的文内,略知一二。虽然他的文字看似轻松、一带而过,但其中的苦涩、忍辱、煎熬,赫然在目。“天天逼供、拍桌瞪眼,声色动人”,十二字囊括了一切。
日后,家中发现了一页破旧之纸,那是父亲关押时写的一份“申请”,我抄录于此,聊作想象:
革命群众:
我从八月下旬起,未能理发,至今已两个多月,头发太长,时犯头晕目眩。我曾以书面和口头多次向您们和值班的同志们申请,都因故未能安排好。我又不应以琐事每日絮请。但日期已久,迫切希望照顾,准予安排,不胜感激之至。特此再次申请,并致敬礼!
后面还缀了几句:
附恳者:十月十日家属给我送东西时,有九、十日两天的人民日报二份,我因需要学习,请求寻找一下,至感。……那次是我的女儿周月苓送来的。
关押期间,我们与父亲无法见面,更无法联络,隔一段时间去送一些生活必用品和学习材料。母亲有时会偷偷往背心裤衩里塞进几块水果糖或一包白糖,自以为不会被发现,有次甚至还在裤裆里绣上“保重身体”四个字。不知父亲是否看到,能感受到家人对他的挂念与担忧。
父亲关了一年多,最后落实政策记得是在一个周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以释放回家。没过数日却在中秋佳节当天随集体离京,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办的这个“五七”干校,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文化名人,我知道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冯雪峰、韦君宜、萧乾、杨霁云、孙用、许觉民、严文井、牛汉、陈早春等等,其他文化单位的还有臧克家、王世襄、周巍峙、郭小川、罗哲文……,他们离开书斋,体验生产劳动,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父亲此去的心情更加复杂与沉重,不但自己要自觉“改造”,还要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干校里分很多小队,“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彼此难得往来相见。有一次父亲与冯雪峰几位“老弱残兵”要清除一处地面,去打扫破砖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冯雪峰勤勤恳恳地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们彼此竟没交一语。
在“干校”,父亲著一条破旧蓝色长裤,不像强壮的人那样赤裸着上身,而总是一件背心,手里常携件极薄的的确良衬衫,狠毒的太阳把他干瘪的身体晒得红中透黑。
父亲掏粪,种菜,守夜——每天半夜三点多须起,四点到湖,满天星斗,蹚着过膝的水,破裤子卷到大腿根,到那“围湖造田”的菜地,只他一个人,拄着一支竹竿,像个鬼魂。因这时无人“管制”,他就吟唱自娱,唱的总是《女起解》那大段八句“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连带着徐兰沅、王少卿二师的美妙的“小肩膀儿”与“大过门儿”,一字不落。这样,由湿闷的呼吸,巨蚊的包围,夜幕的黑暗,迎来了东方的曙霞,朝曦,晓雾,晨晴……不觉悠然自得,忘了一切。父亲对这段唱工的感情和“关系”,可想而知。
父亲最大的支撑与乐趣就是读到家人的书信,那母亲的叮嘱、儿女的关心,带给他无限生机与愉悦。父亲重亲情、重感情,他天天盼望等待来信,并一一给我们写信、写诗:
我天天盼信,无有,是怎么回事?!十分惦念。这信本想等着信再发,可是再不想等了……
书至此十二点半已過,一点往回走去吃饭。早午二餐皆须吃半凉或凉饭菜,亦已无所谓。来书琐琐叙动态及感想,阅之宽慰,能如此最好……。
1968年年底,我响应主席号召赴延安插队,临走未能见父亲一面。后来父亲给我写信时附了一首“赠伦苓”,至今难以忘怀。诗曰:
插队离家意志坚,未能一面两年间。
已与农民感情厚,心怀圣地话延安。
那时,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弟弟建临不久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他给父亲寄了一首小诗:
转眼离家已三月,而今分外思故乡。
不知何日返故土,再来探望亲爹娘。
父亲极疼爱建临,怜他16岁即离家,不久得知被评为五好战士,将要登台“讲用”后,父亲满怀喜悦写下“口号”诗一首:
劳动归来午饭时,阳光普照暖熙熙。
今朝欢幸缘何事:喜见吾儿第一诗!
父亲看到弟弟的诗很高兴,以后书信往来就常附以诗作相互鼓舞。一次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今天是建走的周年纪念日。
今天仍在下雨,时下时止。早晨只我一个在湖里,黑夜泥中摸来的很不易。我作了一首词寄你与建:
西江月
北望云天一线,南居感受千端。宵宵独自守湖田,待得朝阳来伴。祖国花开灿烂,家园竹报平安。音书少处卜忙闲,话语心头何限。
父亲很得意大姐能继承他的语言天赋,也学的英语专业。那时大姐正在部队农场锻炼等待分配,一首“赠月苓”十分有意思:
苦攻外语为人民,锻炼期终待配分。
愿遇新知情意合,速将佳讯报双亲。
一天,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二姐丽苓兴匆匆地告诉他说:我入党了!醒后历历如绘,即作诗一首:
梦中欣报已入党,历历当时欢喜情。
祝女科研多创造,再团圆是在神京。
父亲有一则日记这样写道:
农历十一月初一,收见家中捎来衣包,中有临儿为我买的新版主席诗词一册,有多幅未见的主席宝象,及两帧买不到的未见手迹,这都是我久所梦寐以求的!

临儿,即是我的大哥喜临,他虽然是残疾聋哑人,却也时时为父亲奔波、助力。
我的母亲虽然只有高小文化,却非常有主见,她的坚强勇敢常常感染着我们。那时出版社常常来人动员母亲到“干校”去,有时还以威胁相逼,母亲却以智慧与他们周旋,终得以躲过“一劫”,照顾保全了我们的家。母亲有次给父亲去信引用了主席的诗句“风物长冝放眼量”以为勉励,这让父亲佩服感动的不得了:“一语凭君同记取,白头长久不分离。”父亲时时告诫自己,并时时诵之、牢记之。
“风物长冝放眼量”,让父亲、也让我们全家迎来了另一种生活。
【附注】
常有朋友希望我写写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事情,于是酷暑之下斗胆写下“父亲小记”一组六篇文字,以示回馈。
载天津日报2014-11-14
好好题诗上北楼
周伦玲
1970年8月6日,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父亲周汝昌给母亲寄去一信:
后日就立秋大节了,又是七夕,又是三伏,阳历是“8.8”阴历是“7.7”,可太巧极了。祝你立秋百吉!
我每日下湖,身体很好,勿念。只辛苦点,重劳动反而因此免了。这种安排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希望别到水太冷的时候……
父亲心情不错,还特意作诗一首:
嫋嫋今晨汗稍收,最怜风露玉金秋。
女牛巧七欢无尽,瓜李伏三暑到头。
偷换流年词最警,纵观大化气方遒。
从来庚节关人事,好好题诗上北楼。
“从来庚节关人事,好好题诗上北楼”,就在距这首诗作不过二十几天,接下来就发生了一桩大事,大到惊动了整个“干校”!
父亲在“干校”的生活维持了十一个月即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的如此之大,令父亲几于不敢相信为真,飘飘然若梦境焉。
那是1970年8月的最末一日,父亲照例拄了竹竿淌水上堤,照例哼唱反二簧,直熬到东方既白,朝暾露熹。等到上午到此劳动的人马到来,交了班,悠悠荡荡,打道回程。他本想以一个鸭蛋和一个馒头大饱饥腹,迎面却来了一位同志拦住他,画手掌为字,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
“画掌为字”“画纸作谈”是当时人们与父亲交流的一种方式,因为父亲双耳重听,聋的可不一般,别人和他说话还须大声喊叫,也许人们就索性为了省点力气,干脆以字代谈。
父亲听说队部里找自己,而且要快,大吃一惊,不知这倒霉的被关押过的自己,又出了什么麻烦——犯了何项罪款?无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前往。
“周汝昌同志,因工作的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收拾东西。”队部领导盯着父亲说道,并嘱咐今天要到政工组去办手续。政工组即是中央文化部咸宁垦区五七干校筹建领导小组。
“调回北京”?这是真的吗?父亲简直不敢相信,他还像在梦里,若信若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北京需要我去作什么?
父亲持了公文,走湖堤赴“五七区”,当时天降零细雨星,想起这十一个月所走过的那些路径、竹丛、田畦、旷地,遥望每日来守之湖田,即将分别,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父亲东摸西绕找到五七区时已下班。下午三点,有一女同志出面持一介绍信交给他。介绍信大意是接省军区政治部转达国务院通知,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北京工作……。
怀揣介绍信都没敢再多看一眼即赶至邮局,他给母亲打了一个电报,文字极其简单,他并没有以实情相告,他想在北京车站相见时带去意外惊喜,故只写道:
我准于九月五日下午到京,盼能在车站相见。我将在京度国庆。
才归屋,不料好友杨霁云先生消息极灵通,紧紧跟踪而至。杨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老辈人,他与父亲曾一起给菜园子挑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杨先生也极兴奋,好像比父亲还高兴的样子,即“画纸作谈”,断定父亲回京是搞红楼工作;又提五三年主席对新证“评价很高”的事,说“两月前已有消息”。
傍晚杨先生再至,这回是他预先在日历背面写好的两张纸。一张说可能与吴(世昌)、李(希凡)同事;一张云这次“跳出臭知识分子圈子”,很为父亲高兴。杨先生再次叮嘱父亲到京两三星期后务必通信以情况相告,至有“‘贵人’勿相忘”之语,这让父亲感念不已,故有小句云:
桶粪同君共一抬,树阴小憩亦开怀。
人生奇境原荣幸,几世三生修得来!
此刻全连已传开尽知矣,遇者纷纷见问,人情物态为之一变。当初见了父亲趾高气扬不屑一理的,变为拍肩谄笑。从未笑过的现在见了也呲牙……如此不一。而父亲自己不敢一丝洋洋得意,唯有警惕,谦虚如常以处之。
这天的晚上,安排看“红灯记”。父亲早早即去坐在前面,为的是得以看得真切。此际星斗满天,明河耿耿,仰望北斗星,父亲胸中不胜依恋之忱!
父亲联想起自己8月6日的那首《立秋节兼七夕并三伏凌晨湖田作》的诗,确是为回京早早埋下伏笔,真是句句合先兆,岂非异事!
遥忆1954年5月,是中宣部电调父亲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消息传开,不几天他便接到老师顾随一信,内云“无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亦风流。”特寄来的一首《鹧鸪天》:“玉言梁孟携其五鶵凤自川抵京,舍馆初定即来函告,三復诵读喜心翻倒,走笔为小词当洗尘也”,词云:
三载西川可有情,风舲鼓浪下巴陵。遊鲲振鬐离南海,彩鳯将鶵入上京。挥笔阵,破书城,万人海里见人英。西山山色年年好,长照君家四髩青。
往事历历,回想感慨万千。当父亲再次踏上北京之途,想起老师顾随已作古离去,不胜悲从中来。
而转念又思:余何人?两度北旋,皆出中央电召,倘更不能竭尽微力,于祖国人民,无所贡劳,其心安乎!
1970年9月5日下午二时一刻,父亲周汝昌回到了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
载天津日报2014-11-21
思想“开差”到雪芹
周伦玲
1970年9月5日,父亲周汝昌怀揣着中央特调指示,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首都北京。除了心情异常激动振奋之外,他更多的是惊疑,因为那时正在大力加紧催办继续下干校,不许逃避,而怎麽一个区区的周汝昌,却会专电调回北京呢?
略歇息了一天,第二天7号一早,父亲即在母亲的陪伴下持公函赴文化部留守处去报到。当时的文化部座落于朝阳门内大街的路北,一栋外表庄严朴实厚重的大楼,在那片区域内很显著。踏上高高的台阶步入,楼内鸦雀无声,了无人迹。
传话入内后,出来一位“留守”同志,他看了看公函,见是国务院调来的,很注意,但一点也不摸头,立刻拨打电话。放下电话后,即介绍父亲去“文化小组”。“文化小组”位于人民出版社的四楼,在文化部斜对面不远处。人民出版社与父亲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处一棟楼,而位其东半,父亲很熟悉。这“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虽仅二字之异,功能却大不相同。最妙的是,父亲怀揣的那份调令上却明明白白写作“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而误漏掉“文学”二字,你说巧也不巧?
赶到“文化小组”,那里有几位同志,有一位郭队长负责接洽,但也不知应把父亲“安插”在何处,只是嘱咐回去先休息,有了信息再通知。
过了几日来通知了,父亲乃前往会见郭队长。郭指示要父亲谈谈工作想法,父亲一时没有思想准备,不过说说译述与古典二事。郭队长聆罢将题归到古典遗产上,并提及“红楼梦”三字,嘱写一书面报告,一二日交来以备向上级反映。父亲用了两三天工夫,极认真地把自己的专业、特长、希望等等详详细细一并都写在报告里递上。然这份报告自交给郭队长之后就再没有了下文,是否上交了?抑或根本就没交而压置下来?都成了疑问。
后来,让父亲暂在原单位“挂着”等候。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人员基本都下到湖北“五七”干校,只有几位“留职”人员专司印制“样板戏”。“样板戏”在当时很“火”,家喻户晓,人人会唱。
谈到京戏,应该说是父亲的最爱,这源于周家辈辈酷嗜音乐,父亲称之为“顾曲家风”,“顾曲余家”,更有诗句为“笙管曾如天上乐”,他也曾粉墨登过场,拉二胡、弹月琴,还为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操过琴……。
父亲在“干校”时给他的四兄周祜昌写信就透露:“智取威虎山剧本我最喜……常宝所歌是取鑒于娃娃小生腔而出新者,故尤注意之……”“三个新样板戏脚本,我皆在反复细读……”。他还偷偷把毛主席对普及样板戏的內部指示抄录给四哥,如:“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凡是发表了的剧本,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組织业余演出队演,专靠几个样板团不行……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
人文社这个专司印制“样板戏”的部门设在底楼,其三楼皆空,打开328室,里面已尘积寸许——这就是父亲日后的办公室。
父亲独在三楼,極清静,几乎与其他同志不发生关系,每天即在328办公,却无“公”可“办”。这时的父亲太“自由”了,没有人管,也不敢来“管”,连军宣队的长官见了,也客气地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
那时候到班就是学毛选、听报告、学习主席公開著作及内部講话。有一段时间集中学习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父亲带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古典遗产,还要講用,那时人人都得講。
每日首要第一件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日久不免“思想开小差”。联想到有可能还会从事自己的老专业,父亲脑中忽然闪过有意试试写写怎样向工农兵群众介绍《红楼梦》,努力扫荡原有的那一派知识分子的“语言”和“八股氣”!但是,感觉這个难度可大呀!
有一天,“小差”竟开到曹雪芹身上。
父亲一直认为:“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篇什的散亡,和《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遗稿的迷失或毁坏,同为我们文学史上的极其巨大的损失和恨事。这种无可比拟的损失和憾恨,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弥补和消解的了。”
父亲突发了奇想,忽然“异想天开”:雪芹的诗,就只剩他为敦诚题《琵琶行传奇》末二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十四个字可见,我们无福得见全豹,——我不妨揣摩一下,看能否把它“补”成“全”篇?一种跃跃欲试的想法立即出现在眼前,父亲兴奋地吸了一口手里的烟,他真的想试试自己到底能补成什么样子。
但是,谈何容易!但父亲想到十年前不是也曾不止一次地步过张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诗里“吟、深、阴、寻、林”的韵脚吗!想到此,一种“续补”的欲望与兴奋达到了极致!
父亲就真地试起来了,而且前后一共试补为三首“全篇”,现录如下: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
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
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相濡久识辙中鲂,每接西园酒座香。
岐宅风流柯竹细,善才家数凤槽良。
断无脂粉卑词品,渐有衫袍动泪行。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不想,日后竟由此引出一桩红坛“大案”。
载天津日报2014-11-28
情缘久在不须疑
周伦玲
1970年秋天,父亲周汝昌由国务院特调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到年底都没有任何批示消息。他自己也怀疑难道要待七一年乎!可又觉得调动既然如此之急,又不是立時投入具体工作,上级必有统筹規划,非枝枝节节之事,故亦非個人揣测所可妄断的。于是就静心地等待上级的安排吧!
父亲在“天天读”时开起了小差,而且这个“小差”竟然开到了曹雪芹身上——想把曹雪芹遗留下来的那仅有的两句十四个字“补”“全”。他决心要作一种“试验”,试试自己的才能如何,能模仿到什么地步。
曹雪芹的诗是有家学承受的。他祖父曹寅是康熙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诗、词、曲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曹雪芹虽然没有赶上他爷爷的晚年,但那部丰富多彩的楝亭遗集他却下工夫读过,对祖父的诗篇十分熟悉。这就间接说明了曹雪芹的诗格也受祖父影响势必趋近宋人,势必具备熔铸矜奇的特色。曹雪芹的诗自然又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第一是他的诗绝不轻作;第二是他的诗,格意新奇,特有奇气。
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悯念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别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长安名妓的身世命运,进而联系到自身的贬官九江司马的遭遇,写出了“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而清代诗人敦诚亦取此题材演为传奇脚本,无疑也是有感于自己的沦落不自得,叹老嗟卑、自伤不遇而已。
可惜曹雪芹的那首诗的全文,敦诚没有整篇具引,但有一点,曹雪芹并没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来大发一顿牢骚,而是说:白香山这位大诗人,躯壳虽亡,精灵长在,仍旧活在“地下”,听见敦诚把他得意的诗篇编写为剧曲,十分高兴,必然就叫他那两位擅长歌舞的侍女小蛮、樊素二个赶紧照本搬演起来——那种快乐就像任何一个作家亲眼看到自己写的故事被搬上舞台,人物都如自己所设计地那样活动起来一样!这是多么美妙的想象!
最妙的是在他想象之中不但诗人白香山还活着,而且连他的生前的侍女也还活着,而且他们还像生前一样地生活在一起,还照样享受他们那种诗人和艺术家的共同歌舞风流的“韵事”,这实在是奇想妙想。
敦诚《琵琶行传奇》是以长安名妓沦落天涯为主题,曹雪芹就在题咏中仍以蛮、素二人为结穴,着落到此,气类相从,一丝不走。曹雪芹的这种想法,这样写法,自辟蹊径,绝不落人窠臼,一点陈旧、迂腐的气味也嗅不着。他的才性的潇洒跌宕、风流倜傥,令人闭目如见。
父亲几乎没有太多思索,因为他早就动过脑筋、做过研究,已成竹在胸了。他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烟盒,拆开铺平,反过来,就在上面落字了。
自父亲回京后,他依旧吸烟,我常常见他伏在案前手夹一支烟,边写边吸、边吸边写。有时看见他笔挥不停,任手中的烟白白燃掉,还感觉奇怪:不抽,为什么不掐掉呢!
父亲当时常吸的一种烟名“光荣牌”,是上海卷烟厂生产,价格不贵,也就两三毛钱,他常常令我们到外面的小铺替他买烟。烟盒一面是一朵大红花,一面是一个光明四射的五角星。这种烟很大众,销售流通很快,点上不易熄灭,这也是父亲喜欢的原因之一。当然,以家里拮据的条件,能天天抽上这种烟也就很不错了。
父亲把烟盒拆开铺平,提笔写道: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能传栩栩,渌尊那靳感茫茫。
西轩笙管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这首诗,笔底流畅,一气呵成。“补续”既成,父亲欣喜无限。
1970年元旦那天,父亲写给四哥祜昌一封信,信的末页,附上了这首诗。经仔细与烟盒上原诗稿相比较,第三句的“能”改作“堪”,第五句的“笙管”改作“鼓板”。
父亲很搞怪,他竟然没有将自己“补续”的实情告知四哥,他在诗后缀了两行字,曰:
右雪老题敦敬亭传奇诗全篇也
鑑老试看如何
鑑老,即父亲的四哥,我的四伯父周祜昌是也。当其时,父亲刚从干校回来,四伯父也得以旧业重操,正埋头于“大汇校”,并命名为《红楼梦鑑》(即后来出版的《石头记会真》)。鑑有审查、鉴别、鉴定之义,父亲称“鑑老”,真可谓一手二牍,一箭双雕,既含“鑑真”大业,又有试探四哥之鉴别能力。
没过两天,四伯父回信了:
雪老诗全篇乍看一惊,真有余叔岩阴阳怪气之风致。但不注出处。首句“慨而慷”改“慨当慷”,令人疑。末句“鑑老试看如何”,口吻含混,乃知是老弟笔墨,以试老兄眼力者也……
接着又写道:
诗腹联转得极自如,月荻句最佳,全篇开朗,声出金石,读之令人意远。茫茫句使我想到“剑横破匣影鋩鋩”。它句便想不出。又想起“苑召难忘立本羞”,想来是两首吧?
看来,鑑老还真有眼力。父亲过录此诗时肯定受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诗句的影响,这首主席《七律》,那时人人都倒背如流,脱口而出,父亲一落笔即作“慨而慷”则不足为怪,后划去“而”改“慨当慷”,却引起四伯父的怀疑,他识出是“老弟笔墨”,是为“以试老兄眼力者也”。
其后,父亲为四哥寄去一首诗:
小年解授白家诗,笺注文心那易知。
更有神来补芹句,情缘久在不须疑。
这诗是父亲讲自己的经历。首句说的是少年時曾為小学生讲过白傅《琵琶行》;次句讲1962年,父亲奉古典部指派,与顾学颉先生同为注释《白居易诗选》。对于《琵琶行》的注释,自谓颇得作者意处,尤其对于琵琶弹奏、曲调神情尤多体會。
“芹老断句,独涉琵琶,何人敢補?余实為之。此亦唯祜老知之耳。”
这首诗,足以作为历史见证。
载天津日报2014-12-5
往事斑斑感不胜
周伦玲
父亲周汝昌所敬重的同代同辈份的红学同行,当属吴恩裕先生。
父亲与吴恩裕六十年代即已相识。父亲著有《曹雪芹传》,吴先生著有《有关曹雪芹八种》,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大部主题都离不开曹雪芹。文革中,父亲下放至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吴恩裕则下放至皖北宿县西五铺政法“五七”干校。
1970年秋,父亲奉命调京时,吴恩裕尚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
1971年5月,吴恩裕告诉父亲发现了曹雪芹的著作,引起父亲极大关注:
《考工志》有别人看到,我已晤及。但还弄不十分清楚,在深一步追索。
题者不止董邦达,董邦达也不止题一个。据说在首图卷内也有董题云云。
吴恩裕不肯录示,父亲则疑其不真。12月7日,父亲寄去一函,戏言:我这里有曹雪芹题敦诚《琵琶行传奇》全诗,咱们交换吧。
听说有曹雪芹的诗,吴恩裕迫不多待,马上抄寄董序,却不示雪芹自序,并透露身边还有雪芹的“双燕歌诀”,对这些消息他嘱咐父亲不要外传:
关于曹著《南鹞北鸢考工志》董序,是这样:我在文化大革命即有一孔君以书之见示……均因其离婚爱人持去销毁,而无从觅得……文化大革命中孔君见访,以董序及曹之自序残篇见示,且有一些雪芹自撰之札、画风筝的歌诀……至于雪芹那篇自序却是残稿,因下来时什么都没带来……据云原稿是雪芹自书,字体是草书……此函不足与外人(包括世昌兄)道也。(12月13日)
吴恩裕这次回信之快,让人明白即欲探明父亲手握之诗,他承诺“亦必不外传”:
知兄得曹题《传奇》全诗,望得此函后,能为抄示,弟亦必不外传也。并请将得自何人?是见于某手稿抑书籍?一并见示为感。
吴恩裕只抄来董序,父亲当然希望能看到那篇所谓雪芹自序和其它一些资料。看了董序,父亲断定为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想考验一下他的识力,并叮嘱切勿外传。
于是吴恩裕就再来询问,父亲就再次作答,这样来来往往有几个回合。
12月26日父亲回复:“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
1972年1月14日又复函:
……至其来源,系人所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
1972年3月,吴恩裕由干校回到北京。与父亲数见過,其每日奔波不辍,让父亲佩服不已。
那时节,中央下达了对“四大小说”重印的指示,《红楼梦》也主張另出新本。毛泽东的“《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影响极大;有关《红楼梦》与曹雪芹的文物也陆续有所发现。《红楼梦》在当时确实很“热”。
有天早上父亲刚起床不久,同仁周绍良先生忽至,他是从咸宁干校回京探亲,满腦子還是《八旗通志》、曹寅与程伟元,坐谈至十一点半才离去,时光虽然全交代了,却十分有趣。
彼时,父亲正忙于撰写“碎叶考”,吴恩裕则致力于搜集曹雪芹佚著,几近痴迷,他不仅提出与父亲“合作”意愿,还要修改自著《十种》,忙得不亦乐乎。
10月14日,吴恩裕到人民文学社去拜访父亲,兴致勃勃,说《文物》月刊同意接受谈芹文章,并代杂志社向父亲约稿,说他自己写“风筝”等,非要父亲写“笔山”“脂砚”等,还特意指明要把雪芹题敬亭剧本的“七律全文”也写进去。父亲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
吴恩裕为父亲“制定”的内容,在以后事态发展中被一笔抹去。
吴恩裕催得很紧,11月8日再递一函:
弟文颇有改动……爱此一拳石一诗当略涉及……题传奇折诗大可一谈,何似兄终不愿多谈耶?……
这是吴恩裕第二次“明示”父亲写题传奇一折诗的例证。
1973年元月,中央下达重印《红楼梦新证》的指示,父亲把这一大好消息告诉四哥,那四哥接信后下班不即归家,袋内揣信却迳向“大弯”而绕去,父亲觉得祜老之意度神情至可念也,可惜没人照相留影,忽然又覺得此時的四哥与馬祥唱梆子站起來走一园场,有异曲同工之妙,亦可发一大笑也。
父亲只能“相机应对”了。他把拟好的题目和提纲初稿寄给吴恩裕这位代约稿人,初步分为六小节,其中把题传奇诗与据传的一首“雪芹自题画石诗”合并作为“附录”,因为父亲根本不相信那样的“画石诗”会是雪芹所作,认为如果这种诗会是雪芹手笔,那么我自拟的七律也可冒充得过了。他在词气上表明了存疑。
吴恩裕文章题目定为“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父亲文章则为“《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
1月23日,父亲决定撤下自拟七律。他写信告诉吴恩裕。27日,又给《文物》寄了挂号函,再给吴恩裕寄出一简函。
2月5日父亲开始修改文章,他删去附录中的二文,加入程伟元“画扇”。
7日《文物》取走修改后的校样。
3月9日,《文物》送来校样十份,父亲分寄李希凡、启功、何其芳、瑶四处听取意见,并亲自送校样至干面胡同吴世昌先生家中。孰料他阅后连夜作书,凌晨即发出一信,说要在父亲文后加一“跋语”。
14日,启功回信了,他建议将“新本(靖本)”移前,将各件文物移后,不但与题目相合,且分量也压得住。
同日,李希凡回信告诉父亲,说王冶秋同志前两天为此到报社去了一趟,先已送去了一份校样。李希凡建议“把版本一节放在最前面,这样可以突出重点,其他部分可稍加压缩,把想像性的解说,不必说得太死太实,以免被别人抓小辫。”并且“倒是赞成收入《新证》中”。
后来何其芳也回信了,他托刘世德、陈毓罴二同志代处理。
父亲虚心听取,认真对待。他改后的顺序为:一、板本;二、笔山;三、图章;四、砚石;五、画像;附录一项:画扇。一切完毕,此文即将付型。
过了几天,父亲接到吴恩裕一信:
前函敬悉。前日世昌兄来访,畅谈数小时……。
玆有一事,甚为抱歉,特奉告。兄寄弟之雪芹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一折诗,弟原抄于保存雪芹其他佚著之本子上,并写明“×年×月承周汝昌兄见寄……”等字句。某次,研红同志来访,偶因检查该抄本上之雪芹《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持该抄本以示之。不意他们翻到抄兄所寄诗之一页,弟当时绝不便阻搁,遂只有听其翻看。故前嘱:不能定其真伪,暂勿示人云云,无意中失约,万乞吾兄鉴谅为幸。
弟意兄能加入为《文物》所撰之文中,即补为附录,亦未为不可也。若能插入正文则更好矣。(3月20日)
似曾题月荻江枫
周伦玲
父亲老辈份红学同行中,还有一位社科院的老专家吴世昌先生,字子臧。
1973年3月21日,父亲接到吴恩裕寄来的失约道歉信,说补诗被“研红同志”抄录,后得知“研红同志”即社科院文研所的同志,随即消息迅速传开。
后来,吴世昌来信称:“弟细读后敢决其为雪芹所作,虽悬万金亦无人能作伪到如此高度也”。
月刊《文物》1973年第二期迟至5月份出版,父亲与吴恩裕文章赫然在目。
再后来,吴恩裕来信说:
今日下午世昌兄来访坐谈两小时,对曹敦等作彼亦与弟等之意见相同,认为作伪不得也。必要时彼亦参加讨论……弟曾有只讨论不公开‘论战’之意,闻蓝翎同志亦有此意,认为他们又要把我们引入“考据”之争云云。弟以为此实有远见之言,未知兄意云何?……
看来,一场“论战”在所难免。
父亲没有参战,他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一则为《新证》再版忙得不亦乐乎,要增添的资料太多,先是借调四哥来帮忙,二是眼睛出了大问题,又把二姐丽苓借来相助。
父亲与吴世昌、吴恩裕三人昔日戏言:“二吴二昌五个耳朵、五只眼睛”;1972年吴恩裕眼睛出了问题,变成“四个眼睛”,此次父亲眼底出事故,就剩下“三只眼”了,难怪吴世昌说“《红楼梦》搞不得,搞《红楼梦》都成独眼龙了。”
再后来,吴世昌给父亲来信,闹得极不愉快,现把父亲的回信引录于此,以结束本文。
子臧阁下:“1977.8.16小汤山疗养院”来信收阅,答复如下:
一、阁下说的我曾“函约”你所古代组“陈、刘诸同志恳谈”等情,不符事实。拙著《新证》分赠后,有少数未来回信的,不知其书是否寄达(出版社代寄的),故至今年又曾分发信函询问。因顺便与陈刘两同志提及已有“勘误”一份,因目坏,付邮也困难……如所内有外出收发取件同志,希便路枉过一取。蒙陈、刘两同志的好意,接信后便主动见访,才获晤谈的。……阁下所说,未知何据?此等细事有何重要,阁下亦致如此重视之?盼你以坦荡的胸怀、目光,看待人家的正常的自然的事情。
一、阁下所谓“憾词”,当也是过听传言所致。我提到阁下那年不理睬我的事,不过当做友朋间趣事,善意地话及的,充其量也只是座间晤话的谈助。我亦并非真把这些细节引为“憾”事。(阁下为此辩解,诿过于耳目的不灵,“交臂失之”,那末,在陈凡同志珠市口设宴招邀“红学家”时,阁下后至,我热情起迎阁下,而阁下略一执手,正眼不瞧,急趋别座,与他人谈笑欢甚,终席不与我交一语,又是何故?最后还是我觉得不好意思,临散时与阁下攀话,方蒙勉强地匆匆赐答一二语。我若真“憾”阁下,何不举此?)
一、张次溪的问题,我确实无所了解,他原名江裁,来示中尚予注明,可证阁下亦认为我并不一定对他的事早都清楚(现在也不清楚)。约在六三年秋间,他通过别人向我表示有研红资料愿意提供,我当然要表示欢迎感谢。他对我讲过的只是他的编制关系属于广东文史馆——我当然认为这是事实。至于他的历史问题,我无从了解,也不可能为此而去详细调查。阁下与他是旧交同事,对他还曾有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慨叹,我想这应是阁下当时也尚不知其详之故,所以我并不想执此以为词,说成是阁下同情汉奸。
一、所谓“雪芹全诗”,我从来也没有说它是“真”的,告知恩裕兄时,特别说明,可靠与否尚不可知,嘱咐他切勿外传。他是依约的。后来告诉我说是文研所同志在他家里自己翻阅书册时看见了,才传抄出去,他对此还向我表示歉意,说明并非有意违约。此诗后来非正式发表,亦非由我。再后来听说阁下在一学报上正式发表了,并“悬赏万金”,力主为“真”雪芹诗。这些事阁下并不见告,而且也不蒙向我问一问原委如何。请阁下想:我如何能对你的观点、发表权利获有发言权呢?我对此事有何过错呢?
一、阁下并因此而评及拙句,但阁下似尚不知,唐人已不尽守“官韵”,到宋人二韵通押,已成常例,至有“进退格”“辘轤体”等等名目,阁下岂不闻耶?至于诗中“变读”,更为人人皆知之事,如“绝胜烟柳满皇都”,胜字在此,义为“超过”,本去声,而变读平声(与禁、堪义之读音同)。阁下自诩诗学,又不知诗中上句如係仄起,有时故意将末三字“平仄仄”变为“仄平仄”(如小杜“刻意伤春復伤别”,太白“解道澄江净如练”,例不可胜举),皆小拗以取声调之美,况“石头记”三字乃专名,本不能改动乎?阁下自称“自弱冠弄柔翰,至今垂五十年”,而观其论用韵,论格律,不离试帖识见,而竟以此等识见主观“判断”芹诗之真否,毋乃太孟浪乎?
一、阁下责我未见真芹诗,何能判断“去真”之“远近”,谨答:我确实见过真芹诗的末二句十四字,又有何疑?前六句与后二句,风格不一致,此即续补之证,阁下的责难全无力量。
一、拙词“似曾题、月荻江枫”,一“似”字正为说明我的看法,清楚明白;如我认为此诗句真是芹语,又何“似”之云云?(“似”,亦非“相似”义,不过意谓想像雪芹也可能写、用过这类词语字面而已)。
一、阁下责我“未见”芹诗即下断语云云,但阁下也未见“幽篁图”原件(相片也只极小一部分),而你竟敢下断语说它真伪如何,岂不可异?我未见原件,故表示是真是否,不同看法,各有可肯定点,又各有可疑点;因此,在未见原件前,只能存疑。胡适毫无论证,主观武断,我也指出、批过了,阁下宁无覩乎?我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立论,又有何罪过?阁下竟说什么“为胡适翻案,诚何心乎?”请问:这是否政治诬陷与恫嚇?
一、阁下自己“定”的什么“脂残本”(哪本不残?)“脂京本”等名目,我觉这正是从胡适的不通的“程甲本”“程乙本”而产生并发展而来的,全无可取。我不采用,就触犯了阁下的权威,又说出什么“不惜牜义〔原字如此〕……牲自己良知,媚此买办文人‘在天之灵’的恶毒话”,请你自忖:你攻击别人的逻辑大抵似此,其实崇拜胡适的正好是阁下。你的学风是一派霸气,作风是骇人的恶劣。我奉劝你,自己尊重一些,不要这样恶性发展下去。难听的话,别人未必不会讲几句,只是还要考虑同志关系,有个肯与不肯的分寸在,你不要因为对你客气,反而气焰越发高涨。你在人前背后,口头文字,对别人谩骂攻击,以此自鸣得意,自己的任何论点都“碰不得”,谁要敢以任何委婉方式表示一下不同意见,就是无可饶恕,不惜以政治罪名肆行威嚇——您的这一些作风和表现,大家是很有印象的(外地读者亦有此感)。希望你收敛一点为好。
专复,顺颂
研绥!
周汝昌手启 七七、八、十九.
又,阁下在海外时,素不相知,因写书而引及拙著,主要属于资料性东西,注明出处,你是取资;至于我的论点,你受益之外你很少正面肯定,而多加评议,所评正确与否暂可不论(实际多不公允),我从未计较。今日这也成了你问罪条款之一,你的思想方法实在奇特。我过去撰文,处处表扬你的可取之处,你并非不知。但你毫不记省,却怪我在《新证》重刊本不引及阁下之论著……我现在既然要被你问及“朋友之道”了,我才提一下:当年你从国外投函于我,通过我才刊出你的“自我介绍”的大文,你应还记得,还夸奖我的“雅量”,不想今天变成你可以写出这种恶信的来由了,你的“朋友之道”又是什么?
你自称不拘细节,不重礼数,可是你又斤斤计数你来我处共多少次,而我去只有几次……。怕你记忆、计算法也未必皆臻精确……我自愧条件与阁下不同,我是上班工作制,日又常程,不宜外出作私人交谊活动,到了晚间,我什么也看不见,寸步难行,不可谅乎?去的次数,包括阁下适不在府而空返的,必不至如来示所言,况且枉过的次数中(还有来当面骂“胡适尸居馀气”的呢!)不也包有阁下有事找我的吗?(如借书,如问事,如执一信件来、瞠目不发一语——为“靖本”资料初次来到我手而“质问”,如为看“南京本”,我须恭敬奉陪三四个小时让你阅看满意而去……这些,也要我“回拜”吗?)说这些,实在显得太可笑,因阁下要算细账,故从命答复。
周汝昌又启
载2014-12-19天津日报(报刊略有删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