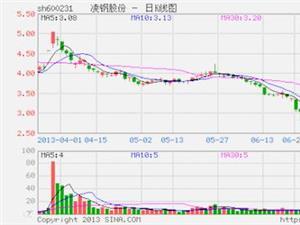“尽一切努力让自己变得坚定”
——记池凌云
邹汉明
一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给诗下过一个半真半假的定义:“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揆诸常理,西方人素以精确的量分为整个世界所称道。不过,一旦关涉到诗——不论古典或现代——都不免认同于中国人的模糊思维。柯尔律治这两个斩钉截铁的“最佳”,看似言之凿凿,铁板钉钉,实则一头雾水。若非不得已认同这位英国大诗人的诗定义,依我看,还得另加一个“最佳”——诗人痴迷于创造时刻的那个“最佳状态”,或曰,“决定性的时刻”(此处引王家新语)。
每个诗人都在祈求这样一个神赐的瞬间。事实上,柏拉图早就说过,诗是凭神力写出的东西。优秀的诗人一旦步入创造的巅峰状态,任你怎么写,都会“发明”出一首接一首佳作来。
二〇〇四年,诗人池凌云终于等来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一年的春天,她在写下了《风在吹》、《风还在吹》之后,带着无声的渴望,突然发力,女诗人悄悄地捧给了我们一个组诗——《布的舞蹈》:
她的渴望无声
她的渴望覆盖了渴望的眼睛
让所有下降的人感到惊奇
——池凌云《布的舞蹈》
在此,读者“渴望的眼睛”且慢惊奇。让我们回到二〇〇四年前后。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派拉蒙(沈方)和米高梅(笔者)等几个IP每天在早班火车论坛上灌水,有时嘻哈打趣,有时兼谈或乱弹诗歌。不得不说,那几年,实在是中国诗歌论坛交流的一个黄金时期。论坛上,无论谁,什么身份,都可以匿名发表高见。正反双方的参与度因此显得前所未有地活跃。而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及时性和互动性的论坛,成为那几年交流诗歌、磨砺诗艺的最佳场所。
终于有一天,一个网名叫无名的人出现了。无名每天都有新作贴上来谦虚地请大家批阅。无名的低调和持续的创造力让大家眼前一亮。后来知道,这个无名其实有名。她就是身处物质温州的诗人池凌云。没过多久,池凌云将她的新作《布的舞蹈》贴了出来。此诗一经亮相,点击率随即猛增,引来一片喝彩。可以说,从二〇〇四年的这个组诗开始,池凌云猛然把自己提上了一个高度——这是写作了多年诗歌的许多诗人梦寐以求却常常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
《布的舞蹈》的创作,诗人池凌云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惊奇了。此后,她以全新的书写方式出现在诗歌的前台。她紧接着写出了组诗《偶然之城》的绝大部分。她开始动用保存在记忆中的那些直接而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坚定地把诗歌的触须伸向了故乡和童年。回忆是以干涸的血迹为代价的,她的这些诗歌,诗思充沛,常带有个人的创痛记忆——在经过多年的诗歌操练后,她现在有这个能力可以揭开伤疤并勇敢地写下它们。诗人此时关于诗的形式感完全具备了这个时代对于诗歌现代性的要求。年底,在写出了《一个人的对话》之后,她更以一首《安息日——兼悼林昭》收尾,给创造力蓬勃的她的二〇〇四年圈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借此短文,在此我仍需着重提示:诗人在二〇〇四年最后一天奋力写下的这一首《安息日》,如今仍值得尊敬。这首诗,正如王家新所言:“这是从锁链、从地下白骨和草根的搅拌声中发出的声音,这也几乎是从天上发出的声音……”或许,单就这首作品,我仍可以移用王氏在评述池凌云另一首诗《寂静制造了风》中说过的话:“……需要怎样的爱、怎样的哀戚和阅历,或者问,需要怎样的高度,才能写出这样的诗篇?”
写下《安息日》的池凌云有一条高贵的诗歌血脉可以追寻。她从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大诗人中盗火。在诗歌的阅读和创作中,“盗火者”和“被盗火者”从来都是互利互惠的。优秀的盗火者最后必定会以自己的诗歌烈焰吐哺给那一个伟大的传统。诗人池凌云经由此火,开始煮沸自己的血液——这是复活的圣火,也是洗涤之火。正是在此火的引领和照耀下,诗的担当非常可贵地出现了。我个人非常看重诗人指认现实的那部分诗作和她背靠的那个传统。这无疑给二〇〇四年以来的池凌云诗歌加上了一个沉甸甸的砝码。发生在十年前的女诗人诗风的转变,特别是《池凌云诗选》在二〇一〇年元旦的出版,池凌云终于有了一个开阔的磁场可以吸纳更多的目光了。
二
笔者与池凌云的相识源于一次本省的诗会。
新千年刚刚降临的那会儿,诗人江一郎在黄岩搞了一个诗会,邀请了省内好多位诗人与会。我也受邀从嘉兴赶去参加。会上,我还书生气十足地发了一个言。也就是那个诗会,我失去了一位朋友。意外地,我认识了一位新的诗友——很高兴,我是在一个生活和诗的晦暗时刻认识池凌云的。
诗会间隙,大家一道去石塘游历。其时,这个浙东的小渔村据说因为最早迎来了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而为世人所知晓。转过石塘的一个弯,在一个平缓的陡坡上,我与池凌云走到一起并接上了诗歌的话题。我与凌云这是第一次相见。不过,她的诗名我早已知悉。那时,我刚收读她与荣荣、千叶和汪怡冰的诗合集《光线》。我注意到,《光线》的序言是邹静之所写。静之先生引奈莉·萨克斯的一封信串联着为浙江省的四位女诗人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此文我连读两遍,余犹未尽。我记得话题就是从这篇序言开始的。静之先生对于池凌云的诗歌,当时有“直接和灵动”、“很快很猛的激情”等等评述。这是早期池凌云诗歌的一个印象。静之先生的这些话,对当年的池凌云得以持续地写作下去,应该是一次珍贵的鼓励。
我对邹静之先生总心存感激。先生曾给我的第一部诗集写序。因我当时身处偏僻乡村,他担心我买不到书而亲自打包给我邮寄来里尔克、瓦雷拉、穆旦等人的新版诗全集。而池凌云对邹静之先生也特多美好记忆。就这样,我们的话题渐次深入,并多有心灵的契合。转过这一年的这个小小的弯道,我们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开始向着同一个方向移行了。这种同行,既有诗人之间的友谊、彼此对诗歌的理解以及创作观念的基本认同……等等在里头。
因为同处浙省,我与凌云在不同的诗会上常有见面的机会。比如,在宁波鄞州的东钱湖边,在杭城,也在诗人安身立命的温州。好多地方都留有我们交流诗歌的美好记忆。我还记得,我们较早交往的一次是我还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那次我到温州附近的永嘉开会。会后,我摆渡过江。凌云来瓯江码头接我。我随她的团队去了一次苍南——那个晚上,作为嘉宾的我聆听了一场美妙的诗歌朗诵会。这是我第一次越过苍茫的瓯江并踏上温州的土地,也第一次听到整场的现代诗朗诵。后来,由于种种因缘,温州这个浙南城市我没少来。而每次到临,我的朋友老陶总会叫上池凌云。我因此总有机会与她同桌吃酒,话旧和聊诗。凌云工作在温州晚报社,早年在广告部,近年忙活在副刊。她又担任着单位的职务,工作自然是相当忙碌。但凌云对于诗的执着,依我看,在这个时代是不多见的。身处物质的年代和物欲横流的温州,她的精神生活之孤峰卓立由此可见。十多年来,她以勤奋而勇敢的书写维护了汉语的尊严。但我看得出也分明感觉到,她在温州始终是寂寞的。有时候和我通长话,老友之间,她会坦白自己的焦虑,告诉我整夜整夜的失眠,这折磨着她的失眠,甚至连中西医都对她不起作用。一个诗人内心的寂寞和孤苦,何足为外人道。在一个太过于物质化的城市里,很明显,浅薄的读者不会认同这样一位诗人的书写。同为服务于一种语言,我知道,这是精神的命运注定要遭受的困境。诗,因反抗媚俗而对于普通读者的推拒,使得它在这个时代陷于更其孤立无援的境地。诗连带着书写它的诗人,永远少之又少,如一粒未被发见的钻石,很可能将承受淹没或不被理解。池凌云当然不例外。但池凌云又是一个例外。
三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四日,我突然接到孤独的诗人自拉萨打来的电话。她显然被奇迹叠出的西藏所震惊。她先是讲她的同伴如何在西藏缺氧的可怕经历。谈着谈着,她忽然问我,为什么不谈谈浙江诗歌?很显然,池凌云对浙江诗歌有她自己的判断,也或者这种判断需要同行的印证。但大部分批评家或诗人,比如我,公开场合一般不会谈论浙江诗歌,尤其是它的短处,说穿了,其实无非不想得罪同行而已。池凌云严肃的问话让我沉思——也就在搁下电话的那一刻,我以四十四分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和池凌云聊西藏,兼谈浙江诗歌》。我终于不揣冒昧,坦白了那些年憋在心里的“有突出的浙江诗歌吗”这个疑问。这本来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谈论浙江诗歌。这种批评式的反问也是无情地在拷问每一个浙江诗人包括我自己。老实说,就我自己而言,这种质疑里实质上更多地含有我对自己创作的不满。正所谓诗非诗同者不能道也,此问果然起了波澜。但凌云不以为意。就在我的诗贴上早班火车论坛后不多久,她也贴上了一首和诗:《与邹汉明说起西藏》(收入诗集时改题为《与Z谈西藏》)。诗中,她告诉我:好东西都在天上。看得出,她的疑问和探索很清醒——这有她的诗句为证:“我站在彩色的经幡下,异常清醒/却无语。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再看看她对于诗的高度的表述:“上升到一个高度,/就要担心自己的呼吸和干裂流血的嘴唇。”这后一句诗,正是对于我的诗行的呼应。
温州与嘉兴,相距不下五百公里,现代科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让这千里之遥的空间感随时消失。那些年,我常接到凌云的电话。有一次,我在轰响的23路公交车上听到她略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汉明,那些孩子的诗歌写得真好,真好哎!成年人写不出……”我将小灵通更密实地贴向右耳朵,另一只手将左耳朵掩住,将公交车的杂音挡在外面。听清楚了。原来她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孩子们写的诗歌了。孩子们的这些诗,出现在埃利·威塞尔的文章中,很少有中文读者关注。那些年,我的阅读量不算小。我碰巧读过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一个犹太人在今天》。经她的提醒,我回家取出书来重读。我深深震撼。池凌云诗歌知识谱系中的俄罗斯背景,很容易被玛莎、莫泰尔、阿莱娜、巴维尔·弗雷德、莫泰利等犹太小孩在进入焚尸炉前写下的这些诗歌所震撼。这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相反,我被她异样的眼光打动——她关注的当然不是这些孩子们的诗歌技艺,而是“他们在死去之前的一刻还在歌唱着生活”(威塞尔)的那一种勇气。不独在诗人创作的作品中,在一个诗人的读物中,尽可以看出一名诗人广阔的怜悯。
长久以来,固执己见已经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我对于今日诗坛许多戴着人工光环的人物,常有所不屑。而且,这种不屑,常要凸显在脸上。这很让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议论诗歌,月旦人物,我会与很多人小有争论,而唯独与池凌云从不相争。我们谈诗论文,每有会心的时刻。而且也唯独池凌云,曾当着某个人的面为我抱不平。这是私谊,至今想起,仍足以让我动容。
我们曾抱怨诗歌和诗人所处的当代环境,也曾在电话中数次谈论诗歌的理想读者。曾记得池凌云在《一个人的对话》中写下过这样自信而坚定的句子:“我已被选中,清理我自己的遗物”。但归根结底,我认为诗在这个时代的选择始终是艰难的。诗人在这个时代除了创造诗歌,还有一个额外的任务——他(她)必须创造读者。“唯其存在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方有存在的可能”。惠特曼的这一句名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这儿,迄今仍管用。中国当代优秀的诗歌需要有极强鉴赏力的、有思想的以及能够体贴心灵的读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具备这样的读者,诗人如池凌云就不会发出“我不知道我发出的声音会落向何处”之类的感慨。诗歌的声音始于诗人微微颤抖的嘴唇,但终于读者的心。诗人杜鹃啼血的声音需要有知音读者的心灵回应。
面对真正的诗以及滚滚而来的“时间将来”(借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意象),杂乱无章的“时间现在”(同上)其实算不得什么。当一个诗人说出“我依然惧怕孤独,依然不可遏制地懦弱”的时候,你以为她真的孤独和懦弱吗?目睹池凌云由“悲伤之诗”、“苦难之诗”转向“存在之诗”(引语出自王家新《篝火已经冷却——读池凌云的诗》一文)的途中,我始终相信,身为诗人的她仍会“尽一切努力让自己变得坚定”。
诗和诗人要担当得起这一份坚定。

2013年10月1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