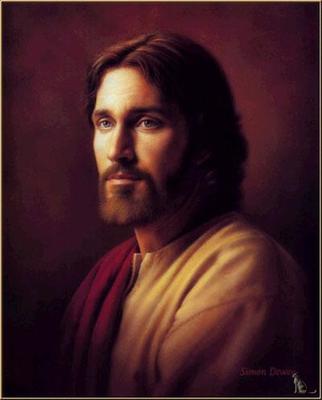这其实是个老话题了,自古至今,对于文化名人“户口”的争议,一直是中外古今文化史上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由于这些文化名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所在区域的文明程度和履历,因此,每次的争议,总是相当白热化的。远的不说,就说发生在前些年的诸暨与萧山的西施之争、绍兴与淮阴的周恩来之争,哪一次都不是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在这些纷纷扬扬断断续续、甚至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议中,上虞祝英台的“户口”之争,也不时地被一些好事者旧事重提。
或许因为她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众女儿;或许因为她是一位敢于向封建婚姻直面挑战的斗士,每当有人对祝英台的“户口”重新提出质疑时,总会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其历时之长,关注的人之多,要远远超过其他文化名人的“户口”之争。
祝英台究竟是否是上虞人,这在中国许多权威的历史文献中,是早有定论的,特别是在唐以后江浙一带的地方志当中,记述尤为明确。其中较为详细记叙梁祝爱情故事的当数晚唐张读撰的《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同肆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乃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鄞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可见,对于祝英台这个江南女子的出生之地,没有人想在这方面动更多的脑筋,而事实是,随意地更动一个文化名人的“户口”或别的什么,自古以来,成功的概率极少。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全国解放之初,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专门派员数度来上虞考察祝家庄遗址,最后认定祝英台乃上虞人无疑,而此后不久推出的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第一句唱词,也确定了这个基本的文化事实:“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
优美的唱词和动人的乐曲伴随着这个凄楚委婉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海内海外。地处浙东一隅的上虞百姓,因为有了祝英台这么一个可敬可爱的女儿,而倍受荣耀。
这就是祝英台的份量。一千多年前,当这个纤弱而极具反叛精神的美丽女子在向强大的封建婚姻发起挑战的时候,她不会想到她这个名字会被这么多人如此长久地议论,更不会想到日后会从她身上生发出如此众多的纷争和纠葛。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究竟是谁率先揭开了祝英台之争的序幕了。一九八九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我汗流浃背地在丁界寺寓所那间小书房里昏天黑地地赶写《梁山伯与祝英台》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曾从报上读到过一条关于对祝英台“户口”之疑的消息,这篇不足300字、火药味也不甚太浓的短文却使我加倍地引起了警觉。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篇短文的发表,可能预示着一场祝英台“户口”之争的风波即将出现。基于这个原因,我才毅然把手头正在写的《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嵇康传》放下了,而把原打算放在第三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提了上来。我必须在这场风波未引起高潮之前把书写出来,我当然不认为这部书能使一些窥视已久,并早想改变祝英台“户口”的人心服口服、改弦易辙,但我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祝英台生长生活的土地只能在上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动笔到出版,总共花了三年时间,不过原先的书名不是这样的,而是叫《祝英台与梁山伯》。这样取名的原因有二:一是祝英台是上虞人;二是“梁祝”故事中真正的主人是祝英台,而不是梁山伯。把祝英台名列梁山伯之前,理所当然。但谨慎有余的编辑们认为这样取名有悖中国读者的传统习惯,建议还是取《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好,我拗不过他们,只好作罢。
书出版后,产生了一些影响,我甚至把书寄给了曾对祝英台的“户口”提出质疑的作者,甚至他们那儿的图书馆,以此向他们表明:别再打改变祝英台“户口”的主意了,看看吧,你们的这篇短文,引来的却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下次再提出这样的质疑,上虞人是不会罢休的。这不,谢晋导演也加入到为祝英台的“户口”以正视听的行列中来了,不仅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书的扉页上写上这样一段话:“将家乡优美的民间传说、美好的人性传播到全世界。”还在全国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发布消息,他已决定把“梁祝”影材搬上银幕,准备花重金征集剧本。虽然这部电影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搬上银幕,但它所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大。作为祝英台的同乡人,谢导此举无非向世人证明:祝英台是我们上虞人,你们想把她的“户口”迁到别处去,没门。
曾经因一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而震动世界乐坛的何占豪先生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祝英台“户口”的捍卫者。作为一个诸暨人,他自然知道他家乡的美女西施差点被别人抢走的那场风波,虽然那场风波以诸暨人得胜而渐告平息,但它却向文化名人的所在地敲响了警钟:别睡安稳觉,有人可能正在打你们那儿文化名人“户口”的主意呢。
何占豪先生正是在别人打祝英台“户口”主意的时候,与上海芭蕾舞团的一些编导、舞美和演员来到了祝英台故乡的,站在祝家庄满是废墟的遗址上,这位音乐家对眼前的情景唏嘘不已。不错,他心目中祝家庄的亭、台、楼、阁已不复存在,想象中那充满灵气的玉水河变得狭窄不堪,有些河段已被乱石堵塞,他只能从脚下随处可见的断砖残瓦中,去感受祝家庄当时的繁华气势和玉水河的清澈幽深。而当他把深长的思绪从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拉回到现实的时候,这位注定一生与梁祝文化有缘的音乐家却掩饰不住对祝家庄现状的不满。
何占豪走了,走的时候带着遗憾,当然也带着希望。希望在哪儿呢?光靠命名一个“祝家庄”有什么用?人家那里已为祝英台立了塑像,造了房子,建了坟墓,而我们呢,什么也没有给祝英台,她太穷了,简直是空有其名。
任何区域性的文化都是一种渗透着浓浓乡情的文化。很难想象,当我们在向外界眉飞色舞地推介故乡的女儿祝英台的时候,竟然对她没有丝毫的感情。由此笔者想起了80年前一个名叫王佐的人,他为了要办一所春晖中学,竟向上虞籍的皮货商陈春澜先生跪了下去,这一跪感动了陈春澜,陈春澜拿出了银洋20万,于是才有了今天繁荣的春晖中学,才有了许多遍布世界各地的英才。王佐为人一世,尽管他做过许多事情,但都如过眼云烟,记不得了,惟这一跪,才跪出了他对故乡的情意,才使人记得上虞还有他王佐此人。
不能再等了,等待和沉默是对别人挑战的一种默许。不能等到玉水河干枯了,等到祝英台“户口”真的被人家迁走了,甚至等到连谢安、王充、嵇康,甚至谢晋、何振梁的“户口”也被人家迁走了。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了,那么你、我、还有所有的上虞人,将怎样面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责问,或许这种责问并非来自我们活着的时候,但即便是在一千年之后,我们也能问心无愧吗?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那段开宗明义的唱词吧:“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
这委婉动人的旋律,这优美缠绵的唱词,这回荡在人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但愿从此以后,不要再动祝英台“户口”的脑筋了,让她安居吧,在故乡温柔的怀抱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