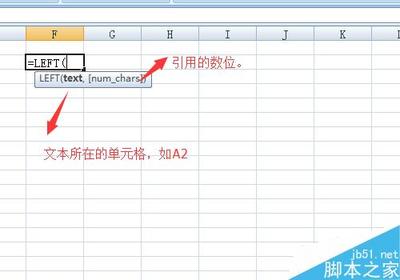(二十四)
我和阿木喝酒时突然看见麦子和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走进来,那个男人满脸横肉,应该是那种有钱的当地人,估计是一个工程包工头,看来深圳就是一个大染缸,竟然把麦子这个我曾经有过幻想的女人也变成这样一个女人。记得以前我是她短期男朋友时,我还带她来过这里一次的。现在居然带别的男人来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毫无办法。在她一去外边打电话时,我故意在她身边跟她打了一个照面,表示我的存在。其实,她好像早就知道我在这里,也许进来的时候发现我来了。
我问她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她说这个男人以前是她的老板,而现在就是男朋友。同居的男朋友。她早就不干活了,住在高档洋房里,进出都是开的高档车。我靠,这个女人如今怎么变得如此龌龊无比,当初跟她初恋男朋友多好的一对啊。后来跟我也没有发生什么故事呀,也就在一个办公室睡了一晚上,还没有做那坏事呀。我和她之间还保持着距离和美呢。真是,我当初对她有过的好感都变成牛粪垃圾了?简直是对我灵魂的亵渎啊。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看她现在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是彻底破罐子破摔了,我是无法阻止她的了。我目送她扬长而去。这次我算是把麦子这类型的女人彻底看透了,决心把她从内心深处彻底地清除,连一丝印记也不要留下,以后跟女人打交道可要多留心眼,要注意成本,这个成本不是多少钱,而是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不好的女人,甚至比路边的妓女还要差劲,因为妓女是公平交易,一分钱一分货,而这种虽然不是妓女的女人,她比妓女更可怕,她要的是男人的金钱,必要的时候可能要男人的性命,如果一开始能够鉴别该多好啊,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浪费那么好的心情,去找寻别的好女人多好呀,哪怕是向菲菲都要好一些。我呸,向菲菲也好不到哪里去。别提这些女人了,还有吴美丽,把我好好地身子都玷污了,今后我颗没有干净的身子献给柏雅了。从这一点上,我已经配不上柏雅了。不光我的身子,我的心都被她们毁了,当然也有我自己好色冲动的原因。哎!气死我也。已经被她污染了,想清除彻底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在外面伫立良久,阿木来叫我,说是看见一个超级靓女在舞池中跳舞。回去一看,是上次见过的一个四川女人,是个香港人承包的二奶。香港人给她在黄贝岭租了一间单房。他们好像有什么鬼约定来着,香港人每周过来深圳两次,跟她寻欢作乐,不准关手机,不准带人进这个房间,每个月给她8000元。真是一个典型的二奶呀。浪费了。
“你要不怕麻烦,就去跟这个女人联系下,反正她也寂寞。”我今天遇见了麦子,心情不大好。
“真是二奶吗?就怕有病啊。”“你要是得病了,我就不跟你来往了。”
从麦子,我担心的想到柏雅。柏雅真的那么高雅?是不是也会变得跟麦子一样龌龊无比呢?如果真是这样,我早就应该听从阿木的劝说,不应该对准这个如花似玉的柏雅进攻,那彻底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还不如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长相并不是特别漂亮的女人身上,这种女人找回家,男人觉得很保险,也很干净,不用天天提心吊胆这个女人到底会不会红杏出墙。
晚上,我梦见柏雅也一样沦落为小三,住在高级洋房。我在梦中喃喃呓语:“我对深圳女人的所有疑惑都已经解开了。我已经不需要女人,我对女人已经开始排斥,我觉得她们只会使我颓废,使我冲动,使我做梦,使我不得开欢颜,我唯一要求她们替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通过她们给我生一个儿子,而且这种欲望显得并不那么强烈。”好在只是一场梦,从梦中惊醒的我在黑暗中发呆。恍惚之中,突然我发现自己幻化为一粒光子,从窗户缝里钻出去,没有惊动房间的一切,包括父亲母亲的照片。我怎么经常会出现这种幻觉啊,晚上经常出现。白天有时候看见地王大厦也会偶尔有这样的幻觉。我想是不是我中什么邪气了。也许是我研究太多东西的缘故吧,本来就是学物理的,在深圳研究彩票,研究股票,又研究女人,研究二奶,研究向菲菲,研究柏雅。压力太大吧。
在黑暗中,我看见父亲母亲的照片在那里,照片中的他们在注视着我。
第二天阳光灿烂。我心情很好,心想好天气预示着一天会有好运气。向菲菲的妈妈接听我的电话,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我是向菲菲的老朋友,问她在家吗?她说不在家,带小孩子去医院看病了。
我关切地问小孩子什么病,向菲菲母亲说因为小孩子早产,一直就生病,医药费也花了不少。我问是在哪家医院,她说是在妇儿医院。于是我匆匆来到医院,我远远看见向菲菲抱着儿子打开车门,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呼叫着她的名字。她回头看见我的一刹那也很是吃惊,但是马上钻进车里,猛地关上车门,启动马达就冲出了医院。我打的士跟着她的车子,我在她家楼下下车,她看见我了。我叫着她的名字,想跟她了解这个儿子的事情。她知道我的用意,于是跑步走进大厦门卫,说不认识我,让门卫阻止我。于是我真的被门卫阻挡住了。
我感到无可奈何,我不可能私闯民宅,否则向菲菲会起诉我的,我也将被判私闯民宅罪名。
我打电话给她家,接听电话的是向菲菲,但是她马上挂断电话,我又打进去,又马上被挂断。
后来她家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估计是她彻底拒绝我,憎恨我的缘故。
我晚上打进去时,她母亲接电话,告诉我向菲菲对我已经死心,绝对不愿意见我,以后不要再打扰她了,我说我只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她问到底是什么事情,我说跟你说不清楚,只有向菲菲自己才能告诉我,我要亲自问她真实情况。
我估计,向菲菲也许也跟自己最亲密的母亲讲述过我与她之间的恩怨瓜葛关系,只是迫于女儿的要求才没有告诉我实际情况。要不然这个老母亲怎么会对我的态度有一些奇怪,令我感到她的口气的确有些欲言又止的余味。但是,无论我怎样表白,她就是拒绝我,还是要求我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不要再麻烦菲菲了。
我没有别的欲望,我只是希望搞清楚这个小孩子的来龙去脉,我必须弄清楚。如果是我和向菲菲的遗传基因产生的后代,那么我还要认这个儿子。
如果这是我的儿子,我也不用发愁自己没有继承人了,当然我要负养育他的责任。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哪怕是一件坏事或者丑事。
可是,我该怎么证明或者排除这一点呢?如果不是我的遗传基因产生的结果,那么我会立即轻松,不至于把这件事情老是牵挂在心上。
我好久没有洗桑拿了,于是我邀请阿木一道去享受一下深圳的桑拿,小姐们给我挖耳朵真令我舒服极了,在蒸汽房里更是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释放感觉,那种快感,那种透彻骨髓的刺激,既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洗礼。
记得阿基米德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想到王冠的秘密的,而化学家也是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状态下梦见苯酚的分子结构的,而牛顿想到万有引力就更神奇——在苹果树下看见苹果掉落地上的顿悟。
而我这次来洗桑拿也有顿悟。正当我在蒸汽房奇热难奈时,我突然脑子里显现一丝灵光,那就是我在妇儿医院的女性朋友,她原本就是我在英语俱乐部的好朋友,她曾经老是邀请我去参加美国安利化妆品演示会,她试图吸收我作为她的下线,虽然我一直很忙而没能作成她的下线,但是我也帮她介绍过不少人去参加活动,我的人品她是肯定的,
回到家里,我翻出电话名录,可是联系方式已经变化,手机停止使用,只有办公电话有效。第二天我打过去,可是她已经辞职下海,专职做安利销售。她的同事告诉我她的新电话,于是我终于找到这个曾经令我心动的美丽女医生。
她听了我的故事,赞成我的主张,主要是要查出小孩子的DNA,这样做虽然有些过分,但是不查清楚对我是不公平的。于是,她同意请同事通过电脑查出以向菲菲登记的挂号单,进而查出小孩的病历情况。
后来得知小孩子的病情并不是特别严重,只是经常需要打针,还需要抽血化验,以检验其免疫系统是否正常。
这样更合乎我的意思,也刚好让医生利用抽血化验之机进行DNA测试,而我的B型血早就是这个朋友测试过的,我这次专门提前将我的血液进行了DNA检验,只要小孩子的血液DNA检验结果出来进行比较,就立即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我的儿子。
反正我又不害怕别人说我的闲话,我只想弄清楚向菲菲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向菲菲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来医院了,难道是我的计划泄密了?或者是上次在医院找她,她害怕我骚扰就去别的医院了?
医生说,不会的,可能是小孩子最近情况好转,医院也只是要求向菲菲在必要的时候过来做检查。
于是,我非常焦急地等待,等待向菲菲过来给儿子做例行健康检查。我也决定不再给她打电话,不在医院附近出没。

皇天不负有心人,向菲菲第三个星期带着儿子来到医院做例行检查,医生乘机对血样进行DNA检查。
令人兴奋的结果传来时,我的一颗心终于放松了,但变成了一颗激动的心。
这样,我就可以实施我的下一步计划了,既然确定那是我的儿子,那么我就要采取行动了,尽管向菲菲可能会完全拒绝我,但是我必须告诉她,她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为了保护我的朋友们,包括医生们,我会首先通过私下和解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向菲菲肯定不会接受;那么我就采取另外一套方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对这个儿子的认领权诉求问题,这样法律程序一定会走到DNA检验这个环节,到那个时候向菲菲一定会无法阻止我的。
我和这个曾经与我有过几年不明不白暧昧关系的向菲菲居然共同拥有一个儿子,我的遗传基因居然也起作用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向菲菲是一个个子不矮的女人,也不愚蠢,而我的智商也会遗传给这个儿子,那么今后一定是一个英俊、高大的小伙子。这样,他绝对不会走我的冤枉路——因为个子矮小而找不到漂亮老婆。如果我能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乃至护权,我一定好好教他读书,教他如何从小抠女——补偿我这辈子找不到漂亮女人的苦楚。我估计法院顶多判我认领和抚养儿子的权利,而绝对不会让我来监护他,除非向菲菲主动放弃。
反正向菲菲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知道真相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向菲菲还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知道我对她儿子的真相绝对起了疑心,所以她对我防范有加,后来我在她家楼下,她远远地就看见我了,不等我打招呼就转身抱着儿子上楼了。
她是真的如此记恨我吗?
于是,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决心采取更加曲折柔和的方式来进攻向菲菲,既然当初我能把她从腐败男人手中诱惑过来,那么这一次我就能通过“真情”打动她,即使没有真情,我还不会演戏吗?
我写了一封二十页的长信来表达我的忏悔之情,我认为那个儿子也有我的份,我不希望通过打官司这种无情的方式来逼迫她承认儿子也有我的份,我不要求她对我承诺什么,我也不要求儿子跟着我,甚至不要求儿子跟我姓,我只想去看看我的儿子,如果她愿意,我可以尽做父亲的责任。
我的脾气,向菲菲那几年是领教过的。如果我认准的事情,或者下决心要做的事情,我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即使最后局面不可收拾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二十页的长信已经足够诚意的,而且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我以特快专递方式把信寄给向菲菲,第二天就会到达她手上。
我绝对相信我的煽情的本领和这封二十页长信的巨大杀伤效果,向菲菲这种女人在灵魂深处一定是愿意原谅我的。但是说实在的,我真的目的只想认领这个儿子,而决不想和向菲菲结婚,如果就这样与她结婚,我是不是有一点窝囊,我竟然从腐败男人那里捡过来的一个破烂货色。
但是,我的儿子没有错,我的遗传基因没有错。
我又和阿木来到地王大厦顶层。我们一起眺望激光发射的方向,那是浩瀚的宇宙苍穹,那是虚无缥缈的宇宙时空的永恒不灭的存在。
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面上讲,我们既是虚无缥缈的,也是永恒的。我和阿木幻化为自由光子,在随着激光发射,向着太空前进。那里,在星球之间,在黑洞之间,上帝在微笑,玉皇大帝在主持七仙女和猪八戒的婚事。
恍惚之间,在豪华的天国的圣殿之上,我仿佛看见阿基米德在澡堂里测量真假皇冠,牛顿在苹果树下面研究神学,佛洛伊德正用催眠术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尼采为了俄罗斯将军的女儿悔恨,梵高与贝多芬同病相怜。
我和阿木,在太空中寻找自己的第三个女人。我的目标是柏雅。
“柏雅,我真的爱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