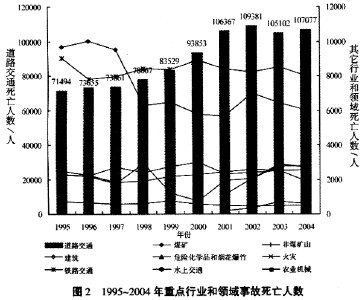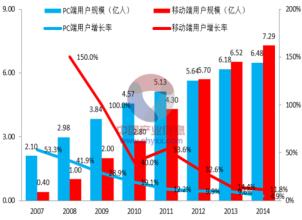中国“艺术电影”:命名、由来、现状与趋势
陈旭光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从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艺术电影”的流变,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指称与境况,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文化流变。艺术电影的艺术创新,为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艺术借鉴和艺术养分。艺术电影对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渗透,在现实主义深化和类型电影的艺术探索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艺术电影 新时期 新世纪 商业电影 主流电影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中国的艺术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而言的,
相对的,“剩余”下来的某一部分电影。但就世界范围而言,艺术电影可谓渊源有自。
一、“艺术电影”:术语的辨析
“艺术电影”(ArtCinema)无疑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术语,并无严格统一的标准。在国外就是如此,进入中国,由于语境的差异更其复杂。
克里斯丁 汤普逊与大卫波德威尔曾论述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法国印象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出现,使得影评家越来越倾向于在主流的商业电影之外和支流的‘艺术电影’之间进行清晰的划分。无论这种划分是否有效合适,这种划分方法从那时开始被广为运用。”而且艺术电影与相应的体制密切相关。“由于艺术电影特定的、较受限制的的受众对象,导致了1920年代出现一种新的,被一名历史学家界定为‘另类电影的网络’体制的形成”。这一体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影院”或“艺术院线”。“艺术影院、电影俱乐部、展览和出版等,都殊途同归促进了‘另类电影’的发展。”[1]
但现在西方学界一般说的艺术电影的概念,“是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持续到现在)制作的叙事电影,它们展现了全新的形式观念和内容蕴含,并以知识文化阶层的观众为主要对象。”[2]
公认的艺术电影包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等,后又扩大到也包括美国电影中的一些好莱坞片厂制度之外的独立电影,最后成为了一个含义宽泛的指称,泛指片厂制度以外,在艺术影院放映,面向小众,常受国际电影节肯定的,有一定的风格化特征和艺术探索性和人文深度意义追求的电影。
一般地说,欧洲电影素有表达作者个人理想,追求影像之思想深度的艺术电影传统,此传统也常常与现代主义电影美学传统相重叠。好莱坞电影之外的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也可归为广义的艺术电影。不少被称为“新好莱坞”的电影,就融合了欧洲艺术电影和美国电影的传统(商业电影、类型电影)而欧洲电影人如吕克贝松、阿尔莫多瓦等也吸收了大量好莱坞电影的表现方法,形成了“一种强调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的“看的电影”趋势[3]。所以,融合是大趋势,复杂难辨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此术语的存在以及从此角度研究电影的有效性。
归纳起来,西方“艺术电影”的限定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相应的体制上的支持;第二是风格上的,有一定的艺术追求和人文性深度,具有“作者”电影特征;第三是融资渠道与发行渠道上的独立性,区别于好莱坞大片厂制度。
在大致梳理了西方电影中艺术电影的所指之后,我们再来看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艺术电影(有时也称艺术片、文艺片等)随也无法下严格的定义但却是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国内评论界一般都把电影进行主旋律电影、娱乐片(商业片)、艺术电影(艺术片)的区分。
若是对照西方艺术电影的这三个限定,中国的艺术电影呈现出其复杂性。比如,中国没有艺术院线的体制,但七十年代末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电影生产和发行体制客观上却是支持艺术电影的。由于当时电影的生产放映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内,几乎没有商业电影或娱乐电影,所以电影不可能逃脱与政治的关系,但只要是在艺术上有新意,在政治主题的表达上不像以前电影那么直接,第四代导演的很多影片就可以纳入艺术电影的行列;九十年代以后,统购统销的计划体制不支持艺术电影的创作了。这带来第五代的分化和新时期艺术电影高潮的衰落以及第六代导演特定阶段体制外的“独立制作”。而新世纪以来,随着环境的进一步宽松,第六代导演从“地下”走到“地上”,与其他导演一道接受市场的洗礼。此时市场经济的体制已经不再允许某些导演做纯粹的艺术电影探索。艺术电影着面临分化与分流的境遇。进入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的界限愈益模糊。在今天,艺术电影也得考虑票房,也可以做得时尚化、商业性,也可以向主旋律题材进军。艺术电影与其他电影的界限逐渐模糊化。
所以,我们只能大致地界定中国近年的“艺术电影”,它一直是一个变量,“永远不会被完全固定下来,然而它总会在标准化和多样化的张力之间、结合特定的历史情景被提炼出来。”[4]
二:一个粗略的轮廓: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电影的流变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的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艺术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
1、艺术的“苏醒”:诗意与纪实(1979——)
1977年,人们从一个压抑和贬斥“美”的时代中“苏醒”过来,迎来了一个呼唤美的回归和艺术自觉的新时期。
在电影界,则是一个艺术感觉苏醒的时代,一场致力于艺术创新和技巧实验的“静悄悄的绿色革命”开始了。理论界关于“电影与戏剧离婚”、“丢掉戏剧的拐棍”、“电影语言现代化”等的探讨引领或配合了这一电影创新潮流。1979年《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春雨潇潇》》等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拉开了中国新时期艺术电影的序幕。随后从1980年到1984年,《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邻居》、《沙鸥》、《小街》、《都市里的村庄》、《逆光》、《乡音》、《青春祭》等,迅速把从“文革遗风“和“样板戏”模式中突围而出的艺术电影潮流推到一个高潮。
这一自觉追求艺术创新的潮流,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他们的艺术追求与新时期文化理想、艺术精神高度契合一致,是新时期艺术创新潮流中的有机一元。
与新时期美学热、形式热,文艺创作的“向内转”等趋向相应,此间的艺术电影,都重视电影表现的诗意风格,走向人文气息浓郁、追求“美”的形式主义取向,有着较为浓郁的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气息。在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调上,此间的艺术电影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征性影像系统,偏重于表现美好的东西被毁灭的,带有感伤与忧郁的悲剧美,常常表现出一种淡淡的“美丽的忧伤”风格,中和而有节制,哀而不伤,在哀婉感伤中透出脉脉温情和理想光芒。
《小花》对战争的影像表现(在表现严酷的战争场面时在镜头前加红滤色镜,从而使战争“虚化”或“写意化”,并退居后台),使得影片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都带有一定的叛逆性质。
《城南旧事》致力于传达“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韵味,追求如“缓缓的小溪”一样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绪氛围;[5]音乐旋律的周而复始,场景的重复,以及“节奏的重复”和“叙述上的重复”。[6]渲染了人生的离情别绪,在艺术境界上营造出别有况味的生活流逝感和浓浓的诗意。
《青春祭》,以诗化的风格、重人物内心世界之表现的散文化结构方式表达了对美好的青春记忆之失落的喟叹和惋惜。影片行云流水般地洋溢着动人的诗情画意,清新的抒情与深沉的哲理思索在影像中融为一体,营造出了一种阴柔、含蓄、抑制而冲和的美。
此间艺术电影对电影语言、形式、美学风格进行了多向度的积极探索,这种艺术探求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也与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相应。
滕文骥的《苏醒》通过对极左政治造成的个人精神和情感的摧残的思考,隐喻了自我意识的觉醒。那种“拍得比较朦胧”[7]的风格调子,也非常符合自我意识“苏醒”的主题诉求,而且“苏醒”无疑是具有全社会性的文化主题。
《如意》、《青春祭》、《逆光》等影片还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由此表达“我”对现实世界的主观感觉和感性思考。
《青春祭》、《小街》以画外音的方式开始回忆性的叙述。叙述者“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自由出入,其清醒的主体反思意识和对话精神,把凝固的历史激活为鲜活的视听影像世界。
《苦恼人的笑》堪称心理电影或意识流电影,以主人公心理活动为主线,把梦境、幻觉、潜意识和现实剪辑交融在一起,其荒诞风格更为鲜见。
总之,此间艺术电影普遍的感伤情调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影像风格表征,奠定了影片诗化追求的倾向,如优美的,色彩流丽、温柔敦厚的影像语言,对已逝青春和美好理想的喟叹,记忆的诗化,美化过去的怀旧情结,温馨浪漫的抒情写意,心理时空的表现、内向型的心理独白,对大自然的心仪和移情------
第四代导演艺术电影探索的另一重要路向是纪实风格追求及相应的电影语言的长镜头实验。
在当时,“当时反矫情、反虚假是我们最大的艺术目标”(郑洞天),他们转向了对主张纪实性追求,提倡用长镜头,反对蒙太奇,反对戏剧化结构的巴赞美学的倾心借鉴。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新时期电影初出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过于戏剧化、矫饰和虚假。于是,纪实风格和长镜头手法成为当时第四代影人艺术突破与创新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沙鸥》虽如张暖昕所说,是试图使影片“成为一种创作者个人气质的流露和感情的抒发。”但影片“追求自然、质朴、真实”,表现的内容“都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以极为自然逼真的面貌出现”,“我们努力尝试用长镜头和移动摄影来处理每一场戏”( 《我们怎样拍<沙鸥>》)[8]
《见习律师》大量运用全景镜头、长镜头和跟移镜头,增强了银幕空间的真实感。据统计,《见习律师》的总镜头数为320个,这与当时一般电影月500-600个镜头比,长镜头无疑占有很大的比重。
总之,新时期艺术电影第一个浪潮的艺术探索,相较与文革结束之时的艺术荒芜,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成就是巨大的。纪实美学与心理化的诗化风格追求,堪称此间艺术电影对整个三十年艺术电影的影响深远的两大艺术遗产。
2、视觉造型美学:崛起与分化(1984——)
1984年,《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出场宣告了一场更为大胆猛烈的电影艺术革命的到来,也宣告了一代新导演——第五代导演的出场,他们在前人开启的艺术探求的基础上,把艺术电影推进到一个高潮。
第五代导演富有主体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气质,致力于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和民族精神重建。在艺术上,他们致力于对银幕视觉造型和象征写意功能的强化,以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进一步强化了影像美学的崛起。他们的成就代表了新时期电影的最高峰,也标志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一个和八个》是第五代导演的亮相之作。在题材超越、人物形象和画面造型诸方面都有相当的突破,影片以非常规的构图,粗砺的人物和画面造型,灰黄的色彩基调,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民族生存的伟力。
《黄土地》以强烈的视觉造型性,以丢掉“戏剧的拐杖”而回到电影之影像本体之后所带来的强劲视觉冲击力,给影坛以强烈的震撼,标志着“影像美学”的崛起——偏于静态造型的视觉美学,而非动态性的视觉奇观展示。空间的大写意风格,缓慢的、几乎停滞不动的镜头运动方式,呆照式的镜头切换,某些意象的循环往复,都具有一种格外沉重的沉思的风格。
此后,《喋血黑谷》、《黑炮事件》、《大阅兵》、《孩子王》、《猎场札撒》、《盗马贼》相继推出,给中国影坛以持续的震动。
隐现在影像造型的背后,是第五代导演强大的主体情绪和理性精神。
《黄土地》具有鲜明的审视批判的立场。影片的主角与其说是几个性格不甚鲜明的人物,不如说是那一片永远沉默着的、仿佛有着灵性的“黄土地”。影片独具匠心地用电影语言渲染、突出并“拟人化”了这一片黄土。
《黑炮事件》有着浓烈的表现主义色彩。画面造型受到新构成派绘画的启发,通过背景的变形来形成画面造型的新颖奇特的现代形式感,“现代化建筑的积木感和高度发达的工业化设备的几何图形感,构成了画面的现代形式美。”[9]
夸张和变形的视觉造型,凸现了导演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主体精神。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主体精神强大充沛,仿佛要溢出画框,色彩是浓烈的,而不是像第四代影片那样是淡雅的诗意,美丽的感伤。当然此间艺术电影也暴露出电影叙事的薄弱。一些电影逐渐歌高和寡,渐渐远离了观众。
进入九十年代,理想深重、抱负远大,实验也不乏大胆激进的艺术电影在艺术理想上更为稳重、含蓄,由于电影生产环境的变化,他们多少考虑到了市场的制约因素,因而更为注重叙事,也进一步走向世俗化。
《红高粱》是新时期电影的高潮,也是一个时代、一个特定含义导演群体终结,一种艺术创新潮流转向的信号。《红高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艺术探索的集大成者,充分发挥了银幕艺术世界的造型和抒情的功能,全面调动了各种视听觉要素。如渲染并强化的红色主调,充分表征了野性的生命力和无羁的热情。狂放不羁的祝酒歌、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气质的唢呐声都在听觉效果上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颠轿”、“野合”等几个具有仪式性功能的场面,给人立体的视听感官冲击。
《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群体转型乃至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中国新时期电影之“娱乐化”的转型和走向也有重要的先导性意义-----从此之后,长期在特殊的计划体制护佑下进行艺术电影探索的第五代导演们也将脱离庇护,独自上路,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飘摇沉浮。
陈凯歌也因为《孩子王》、《边走边唱》等的过于歌高和寡而通过《霸王别姬》等作品实施自己的转型。《霸王别姬》主题宏大,试图把京剧舞台与历史舞台合一,借用了“戏中戏”结构,非常重视戏剧化的视觉形式的建构,在视觉美感上颇具凄艳华美的意象美。影片以中国50年的历史为背景,表现人性的迷恋与背叛的主题。人物命运本身,曲折的情节,明星的组合,华丽的视觉风格,将一个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讲得有声有色。
其他导演如黄建新、何群、何平、李少红、宁瀛等的创作略晚于陈凯歌张艺谋们,又很快就遭遇了市场化的社会转型,故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征,与时代社会有更为密切的关联,但那种知识分子气质、艺术品位的保持则以一贯之。
3、“边缘的求索”:纪实与实验(1993—)
自八十年代后期新时期艺术电影的高潮过后,中国电影业遭遇了一个票房淡季的低潮。第四五代导演继续拍片,有的向主旋律靠拢,有的艰难地实施商业化转型,艺术电影因遭遇市场而生尴尬。
这之中,一个以“第六代导演”为主体,集中呈现“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特点的艺术电影潮流悄悄成型。1993年,电影学院87班发表《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中国电影的一次谈话》[10]。《北京杂种》、《头发乱了》等影片拍摄于此年。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元、管虎、李欣等先后开始拍片。总体而言,这一批艺术电影的导演们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第五代导演的辉煌和九十年代电影市场化转向的现实客观上推动他们坚持小制作、独立制片、边缘另类题材、国际电影节等艺术电影取向。
此间的艺术电影呈现出几种重要的艺术向度。
其一,个体意识觉醒,“作者电影”风格明显。
此间艺术电影在个体影像语言上注重影像本体,具有明显的风格化特色,是现代主义式的,他们对欧洲作者电影或艺术电影着迷,影像语言充满陌生感、节奏也慢。有些影片甚至深入到潜意识、隐意识的层面,探索他们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像日记体,如“自叙传”,有一定的个体人文深度。
《悬恋》中,黑白影调对比鲜明的画面、总是若有所失的年轻美丽的女精神病患者、莫名其妙的梦境,构图上的鲜明的表现主义特色等等,从中不难见出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电影如《红色沙漠》、《奇遇》等的踪迹。
《邮差》通过风格化的影像语言深入到了一个“偷窥者”的内心世界:敏感、焦虑、自闭而又渴求与他人沟通。
《冬春的日子》以风格化的影像描绘了一对画家夫妇的精神生活,带有相当浓郁的“身边性”和个人隐私性,就像一部日记体的“身边小说”,自我意识非常突出,以至于作为主角的画家最后面对镜中自我而陷入精神分裂的困境。
《巫山云雨》的表层是纪实的,但在结构上却是分段叙事,呆照般的画面构图和不太自然的演员表演都颇富“像外之意”。影片正是力图通过影片的结构来把握生活、概括生活。纪实只是假象,是表层,而深层的内涵是关于人的生存、偶然性等重要哲理主题。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意义生成模式。
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是中国电影中真正的现代主义——一种个体性的现代主义,“作为个人艺术家的第一代”。[11]
于是,个体“成长”成为他们普遍表达的主题。《周末情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非常夏日》等都隐含了“长大成人”的主题结构,是关于成长的寓言、青春的呓语或抒情诗。
其二,叙事的实验游戏和形式探索的意向。
此间的艺术电影,颇有电影语言的自觉意识,更不乏电影叙事和影像表达的实验游戏精神。
《北京杂种》在结构上颇具后现代的无序性,并置了五条线索,断断续续插入了六章摇滚乐,颇具拼贴装置性,在叙事上明显受带有后现代风格的新好莱坞电影如《不准掉头》、《低俗小说》等影响。
《谈情说爱》,也是“碎片”式的三段式叙事结构,而且有意“没有让故事的发展进入习惯的思维轨迹”[12]从而以激进的叙述游戏颠覆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非常夏日》既有影像上的别出心裁,又有叙事上的引人入胜,尤其是对悬念气氛的把握相当老成。在叙事结构上留有《滑动门》、《疾走罗拉》的影响痕迹,也是几次回叙性叙述的叠合,在几次叙述的对比之间留下某种“叙事的缝隙”和悬念,最后把真相的“包袱”抖给观众;
《月蚀》同一演员扮演两个女人,表现了人性的丰富复杂性以及生命的多重可能性和偶然性。与《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的现代主义主题相似。《月蚀》在汲取现代主义文化精髓之外,还融进了零散化、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文化。它从一个中国女性的独特视角和感性,表达了当下现实中个体生存的残酷,近乎精神分裂的诡异影像风格,残酷的生存现实的呈现,具有强烈的视听冲击力。
其三,纪实风格的追求即以纪实风格呈现个体生存状态。这一批电影经常使用同期录音,跟镜头、实景拍摄、长镜头等手法,以强化影片的纪实风格。《周末情人》、《头发乱了》、《冬春的日子》、《巫山云雨》、《小武》、《过年回家》等都是叙述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和个体人生的当下都市生活体验,别有一种还原本真生活状态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新生代导演不想寄托宏大主题的凡俗心态以及他们之琐屑、杂乱、日常的现实生活状态,小制作的影片生产方式等决定了影片的纪实性风格:粗糙而富于质感的的影像,破碎的片断化的叙事,日常生活化。
三、新世纪以来:多元流向与新趋势(2000——)
在新时期的每个重要阶段,艺术电影都表现出或主流的辉煌或边缘的寂寞而顽强存在的态势。到新世纪,第五代导演或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以大片弄时代之潮,第六代导演从地下或边缘进入体制拍片,新的年轻导演也不断出现,这一切都使得新世纪以来艺术电影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复杂性。

原为第五代当美工或摄影师的霍建起、吕乐、顾长卫、侯咏等人构成了“后五代电影”现象。《那山 那人那狗》、《暖》、《孔雀》、《美人草》、《立春》等艺术电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普通人,表现他们的悲喜和人生际遇,对青春岁月的回望、对故乡和爱情的追思,以及情感诉求和表达上的抒情性,使这几部影片流露出浓厚的感伤和怀旧意味,是一种浪漫化的中国式乡愁的世俗表达。[13]
第六代导演大多继续走艺术电影的道路,但更为稳健,也开始分化,更加重视叙事、故事和电影的节奏。面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冲击,他们原先抱有的纯艺术理想也在经受着冲击和变异。
有的继续叙述成长主题,回顾成长经历,关注成长记忆、父子关系问题等,如《向日葵》、《青红》、《看上去很美》、《我11》等。有的进一步离弃极端个人化和边缘姿态,积极回归现实,关注他人与社会,如《十七岁的单车》、《世界》、《卡拉是条狗》、《租期》、《三峡好人》、《惊蛰》、《图雅的婚事》等。
更多电影的艺术探索开阔了影响与借鉴的视野范围,不再象早期第六代导演那样仅仅沉浸在欧洲艺术电影的理想中。《走到底》、《寻枪》、《可可西里》、《非常夏日》等,不难发现诸多好莱坞影响的痕迹,不再刻意追求边缘题材和陌生化的艺术表现,呈现为艺术电影与类型电影的综合。
也有艺术电影在艺术探索上不惜走极致。《太阳照常升起》是新世纪以来艺术电影的一个重要个案。影片复杂多层次的主题意蕴与繁复驳杂过于个人化的意象细密交织,增加了影片读解的难度。《太阳》也试图靠拢市场,如明星的出演、市场化的营销策略,但在艺术追求与商业诉求之间形成了分裂。
不少电影在艺术电影要素和商业电影要素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借鉴,达成了平衡与适度,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如《蓝色爱情》、《走到底》、《好奇害死猫》、《夜。上海》、《飞越老人院》、《观音山》。
有些艺术电影则向主旋律题材电影渗透,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纪实性风格(既不同于第六代导演边缘化灰色调的纪实风格,也不同于主旋律现实主义电影)。如《香巴拉信使》、《千钧,一发》、、《钢的琴》、《神探亨特张》、《人山人海》。
还有些电影则颇具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如《走着瞧》、《盲山》、《光荣的愤怒》、《最爱》、《斗牛》、《哈罗,树先生》、《杀生》等。关注农村的现实,在冷峻中透着黑色幽默的风格,实为传统现实题材电影的突破。
新世纪艺术电影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其一,仍有艺术探索但并非小众化和先锋性,如《转山》、《星空》、《秋之白华》、《钢的琴》等。
其二,风格时尚,手法多样,不拒明星和商业,有时往喜剧类型靠拢但不低俗媚俗,且投资不大,控制成本严格,常常呈现出多元文化思考的意向,如《疯狂的石头》、《苹果》、《刀剑笑》、《杀生》等。
其三,关注现实,追求接地气,如《海洋天堂》、《李米的猜想》、《最爱》、《搜索》等。
其四,探索独特的投融资宣发模式。一般是小成本,不追求大投资和刻意追求市场,但也尽量不亏本,并从国内外的获奖中补充收益,如《二十四城记》、《观音山》、《桃姐》等。
总的来说,艺术电影与其他电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世纪以来艺术电影的多元流向体现了艺术电影发展的成果,其艺术探索化入了各种类型的影片,为商业电影、主流电影以及自身的发展都提供了坚实的“艺术的保证”。虽然电影的工业性和商业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有矛盾,但并非不可折中甚至共赢。
艺术电影有强大的衍生性和生命力,现实情怀、本土关注、平民意识、民族精神,乃至产业价值都需要借助于较好的艺术表现而传达。艺术电影更是新生代导演初试身手的必然选择。艺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赢得国际声誉的重要途径,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国际化呈现。新世纪以来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如《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孔雀》、《西干道》、《钢的琴》等都属于艺术电影。
因此,对艺术电影的宽容、扶持和研究总结事关中国电影的现实和未来发展。
[1]克莉丝汀 汤普森、大卫 波德威尔《世界电影史》,第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第23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3]克莉丝汀 汤普森、大卫 波德威尔《世界电影史》,第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第23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5] 吴贻弓:《<城南旧事>导演阐述》,《电影文化》1983年第2期。
[6] 吴贻弓:《<城南旧事>导演总结》,《电影通讯》1983年第2期。
[7]滕文骥曾自述:“《苏醒》当时拍得比较朦胧,谈论的这里有些生硬,而实际上那个时候人人都是处在朦胧之中谈论生命的道理的。”(滕文骥、荣韦菁、李奕明《第十一部》,《电影艺术》1990年3期。)
[8] 《电影导演的探索》(第二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136页。
[9]雪莹《肩负起新一代的使命——黄建新谈<黑炮事件>创作体会》,〈〈西部电影〉〉1986年8期。
[10]此文写于1989年初,后以“北京电影学院85级全体毕业生”的署名方式,发表于《上海艺术家》1993年第4期。
[11] 郑洞天《“第六代”电影的文化意义》,《电影艺术》,2003年第一期。
[12] 李欣《关于<谈情说爱>》,《当代电影》,1996年第4期。
[13]参见陈旭光、苏涛《论新世纪的“后五代”电影现象》,《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