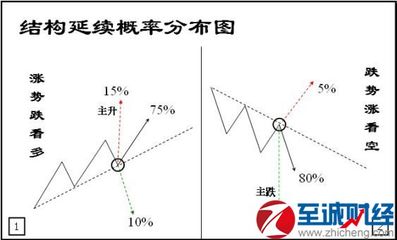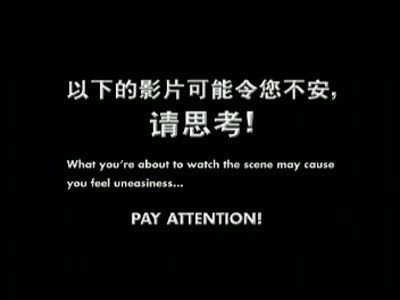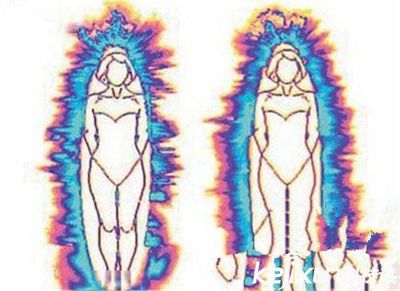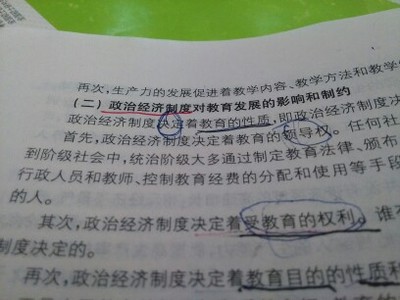前言:前日饭间,一邻桌说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激动不已,论断不停。本人没有详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在重新思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时,我深深的为之折服,可惜关于其更多的论述,百度并没有很好的帮助到我,搜索出来的论述都是对的,但总感觉大同小异,没有我想要的。于是,我决定提笔。
我们首先要明白基本的概念,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经济基础,是指当时社会占统治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制度的总和。
上层建筑,是指在当时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政治、法律、哲学、文艺、道德均属于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指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应,上层建筑须由经济基础来说明。但是经济基础总是在一段时间过后就有所变化,而上层建筑更多的是制度与意识形态,而制度与意识形态一旦形成便会顽固,故上层建筑总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制约于经济基础,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我就以下六个方面,阐述我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如何思考中国。
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
二.中国封建社会决定的上层建筑
三.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四.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
五.新中国经济基础变化决定的上层建筑变化
六.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基础及其决定的上层建筑
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
中华文明大致形成于黄河流域,即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属于典型的土地文明。人们完全附着于土地生存与发展,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下,人是作为最有效的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效率,于是人口的多少就成了整体实力的要素之一,然而不论人口有多少,人的生产力都必须依附土地而发挥效率,人与土地牢牢的捆绑在了一起。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故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掌握了人口,谁掌握了人口,谁就势必要争夺土地。土地作为不能移动的财富,故围绕土地就有继承的产生,特殊生产关系以及人口天然形成的“家”,同样依附于土地,所以家的小权利中心拥有对土地的分配权力,故家中拥有权力的人往往比政治权力的人更能驱动人,这就导致中国的“家”更具有管理制度与管理技巧。

人类的主题是生存与发展。土地经济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生存靠土地生长的农作物即可维系,为了生存的质量,也可以说为了发展,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交换,交换是商业的本质,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交换历来就不被重视,因为农作物的交换仅仅是为更好的生存而已,并不能对生存产生威胁,更何况,土地是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作物、手工制品或牲畜的交换仅仅是生产资料末梢的移动,根本动摇不了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至尊地位。土地本身固然也能交换,然而土地的不可移动属性,让土地的交换仅仅只能在小范围进行。所以封建社会按照对社会的贡献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人们认为商人干的仅是交换的行为,自己并不生产,是依附别人的劳动成果而生存的,干的都是投机倒把的勾当,自然就不承认商人的价值与地位。
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商业发达的时候,例如丝绸之路的闻名,丝绸之路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兴盛于唐汉,这也是因为唐朝经历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达到了新的高峰。李世民仅有四分之一汉人血统,他大力倡导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交往,鼓励外国人同中国人的交流,在国家管理上,大量启用胡人(非汉人),国家政策开明带来的物产丰厚加上开放的心态与空前的东西方交流,势必就形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发展,在长安的胡人,鼎盛时期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丝绸之路更是促进了世界文明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工艺及技术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长安城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自信、最动人的时代。
唐汉的鼎盛并没有永久的延续,中国又经历了非汉人统治的元朝及后来的清朝,清朝的灭亡并非是清朝自身原因,清宫三百年,十帝励精图治,然而在参与世界游戏中,清朝落后了一大步,是世界的发展让清朝难以为继。中国三千年来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海洋国家的一场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资料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变革,清朝这落后的一步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内忧外患的大清宏大又悲壮、可怜又惨烈的倒下了,随之一起崩塌的还有中华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基础及陈旧的上层意识形态,这一切厚重的人文意识、繁杂的文化形态、长达几千年不变的思维模式被列强的炮弹轰得支离破碎,永不可修复了。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围绕土地建立的,土地的自然属性让中国人不重视交换,围绕土地经济基础形成的家与家族,又让中国人始终注意小团队的活动,在家与家族中,左右上下属于共同体,又有各种各样的亲疏关系,家族一旦大起来,里面关系错综复杂,矛盾不断,作为核心权力者,又不可能进行严厉的整顿,因为都是“自己人”,故中国历来的核心权利人都非常看重表面的稳定与团结,上下一团和气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鉴于核心权力者的这一需求,所以中国人又擅长私底下斗争与暗地里较量。回头看整个中国史,总是在极盛与极衰中动荡,经济基础也是一度极好一度极坏,在这种大起大落中,人们看透了人世与争端,望穿了荣华与落魄,沧海桑田变幻眼前,于是中国人在生死观上个个都是思辨家。与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商业发达时候,但是一开始便已形成的天朝上国、重农抑商的上层建筑,始终制约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经商从来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更何况与外国人经商。这种思维模式直到近几十才有彻底的改变,同样是因为世界在变。
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乱,给后来的大一统准备了条件。中华文明中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形成于这一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雅斯贝尔斯著名的“轴心时代”也是这一时期。东方世界诞生了老子、孔子,西方世界迎来了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帕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佛陀也是此时在菩提树下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以及混乱,形成了经济上的彼此独立与军事上的相互征战,而可能正因为这种经济及政治上的不统一,这种“国与国”的概念,才从另一个方面成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诸子思想。
独尊法家,通过商鞅变法改变经济基础的秦国,迅速的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国力的强盛就是战斗力的强盛,就是发动战争的必然,这个道理亘古不变。秦国一统六国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经济基础与文化基础的统一,秦始皇及他的幕僚得出结论:统一仅是军事与政治上的统一,要想真统一,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统一、进行压制。于是焚书坑儒这一反人类文明的行为发生了,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压迫越大,反抗就越大,这个道理同样亘古不变,秦始皇没能长生,死在了路上。杀害兄妹二十余人的秦二世至死估计都没明白明明是鹿,怎么大家都说是马。
饱受战火之痛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大汉帝国,汉高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采用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从经济基础上改善了百姓生活,经济基础的雄厚不仅仅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使得社会精神文明快速发展,东汉桓帝时期,仅太学生就有3万,各家学说在此时又得以生存与发展,并且很多学说又有了新的分支与流派。大汉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立国,大汉是踏着大秦而来,秦皇尊法家统一了六国,汉朝自是不能丢了法治,然而秦王朝的灭亡,让汉朝又不能独尊法家,于是汉朝无为而治之后,在文景时期,以儒法两家为指导思想。在国力强盛,政策开明,日清月朗的社会环境之下,自然是人心所向,虽然各家学说再次兴起,但是儒家思想的地位因为国家的长期倡导及国强民富的社会环境,已经具备独尊的条件了,汉武帝毕竟不是秦始皇,他听取了董仲舒的意见,以较温和的手法罢黜了除尊儒家学说之外的官员,从仕途上扶正了儒家,从建立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稳定来看,统一思想是有必要的,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逢经济基础的盛世进行上层建筑的统一,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福分。
西汉本来就重农抑商,讲究”圣人不言利”的儒家独尊之后,更是上层建筑制约了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文明并不仅以商业作为唯一标准,大汉的强大与广袤的疆域,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此时,在遥远的地中海,还有个罗马。
好论天道的中国人爱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爱说否极泰来,乐极生悲。英雄辈出的三国、五胡乱华十六国的晋、动荡混乱的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三十多个大小王朝交替生灭,混乱又剧烈的动荡势必造成经济基础的薄弱,如此社会状态下的百姓,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当日子过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人往往将生死看得很透亮。恰好此时,佛陀弟子们袒着右肩、披着黄袍、踩着细沙从遥远的西方而来,曾经隐进山林的道家学说,因为对痛不欲生的社会境况有着心灵的抚慰而受到人们的尊捧,被汉朝神化的孔子及其儒学,自然而然的也就在此一时期被拉下神坛回归理性,于是国人思想构架中,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产生了。
依旧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华大地迎来了激动人心的大唐时代,任何伟大的王朝都一定由伟大的帝王造就,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有四分之三的胡人血统,可能由于这一原因,故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认为“四夷可使如一家”,横扫天下的帝王以博大的胸怀看待外族,那么帝王领导下的民众自然也充满了自信与豁达,后来的清王朝同样为“胡人”,但他们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异己,可能与他们夺得天下本就不那么光彩,自身文明在汉文明面前尽显拙劣有关吧。后来人推测,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顶峰时期接近十万,许多边疆大吏也是胡人。汉人重农抑商,胡人可是有着商业头脑的,丝绸之路的通畅配备大唐的自信,中华与世界的文明交往变得空前繁荣,令人神往。同时世界对大唐的强盛与开放、包容与自信更是无限崇拜。可以说,唐朝时期,是中国上层建筑充分推动经济基础的时代,特别是对商业的推动,更为后来宋朝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并不是说上层建筑能决定得了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能有助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例如两千年后的中国,提出“解放思想”的上层建筑工程之后,对经济基础的建设有了巨大的推动与包容。唐朝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是无意而为的自然效应,是制度与心态的开放,是以不为包容有所为的大智慧,同新中国“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有质的区别,后者是有意而为的反科学运动。
屈辱的宋朝披着黄袍被人簇拥着走来,大宋的江山来得轻巧,走得却是令人心寒。
这注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王朝,继承唐朝富庶的大宋,为了避免战事,一边进行虚弱的抵抗,一边是连年进贡北方蛮夷,岳武穆、韩世忠夫妇终究没能抵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连年的进贡只能换来贪得无厌的侵扰。中国封建社会一向重农抑商,唯独宋朝大力发展工商业,熙宁10年(1077年)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到70%。大唐的经济繁荣背后是大唐帝王的坦荡与历代皇帝的文治武功作为基础,北方胡人尊称李世民“天可汗”。而大宋立国之后,一味的发展工商业,杯酒释兵权的心得以致大量重用文官,大宋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如范仲淹、李清照、辛弃疾、苏东坡、柳永、朱熹、王阳明等。宋朝除了军事,在其他任何一方面,应该来说都不比汉唐逊色,甚至超越汉唐。汉唐是犯我天威者,虽远必诛。但是一遇战事就进贡了事的大宋,终养虎为患,二帝被捉,靖康之耻,也是中华民族之耻,宋朝气数尽于崖山,十万士大夫投海自尽,日本举国哀悼大宋的灭亡,倭主从此再不朝贡。后人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陆秀夫那一跳,中华的精气神至今没有浮起。
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构筑到大宋,也就算是停下了,因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结构上一直没有较大改进,行至清朝,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制约,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地步,因为你没有变,而世界一直在变。元明清的思想高度、哲学成就难望前人项背。元朝的残暴杀戮,让人性极度扭曲,一次次屠城,大量汉人被迫南迁。明朝的文化断档,没能建立起自己的性格精神,清朝奴才文化的遗毒更是让今天的中国精神摇摇晃晃,迟迟不得站立。
这里单独提出一点,那就是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在1850年被动摇,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列强侵略清朝的缝隙里迅速壮大,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自己系统理论的农民革命团队,中国共产党是第二个。《天朝田亩制度》及《资政新编》具有很高的思想指导水平,但是从来没有在太平天国的管辖区实施过。天平天国以基督教教义加儒家经典加个人崇拜(洪秀全鼓吹自己是天父附体)作为核心引导精神,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明、驱逐洋人”为口号,主张男女平等(太平天国有10万女兵)。太平天国风风火火了13年之后终于自己把自己给结束了。太平天国后期领导阶层的骄奢淫逸以及用人唯亲应该是让太平天国迅速走向灭亡的根源之一。事实证明,经济基础薄弱的群体在取得政权之后,首先要干的两件事就是彻底打倒之前财富所有者以及取得经济基础的厚实,经济基础薄弱时形成的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厚实之后,随之也发生了改变,一开始的理想与操守、坚持与梦想,全部都被既得利益泡得稀烂。以古观今,我们需要反思的有很多很多。
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
西方人的思维构架在希腊三贤的学说之上。希腊是海洋国家,这个地球表面覆盖着70%的海洋,所以人类历程上,海洋是商业与战争的“发祥地”,靠近海洋的国家,有发展商业的先天优势,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可在全球开辟战场。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一度控制着大半个世界。
以海洋文明为背景的欧洲人,自然而然在航海方面不停的探索,西方人首先发现新大陆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中国一度在造船工艺上领先,但是西方国家最终在海洋行驶上拥有绝对优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海洋城市的商业繁荣,势必会形成与之相关的文明大发展,最突出的就是数学与逻辑,商业贸易促使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缜密与精确,又成就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与严谨的精神品质。对商业的重视,自然也就是对产品的重视,对产品的重视也就形成了创新与不断改良的意识,与此同时,围绕产品的生产力与生产效率自然也将受到重视,这是水到渠成的良性发展,最后,西方爆发了工业革命也就合情合理了。
商业关系不同于家族关系,商业关系是彼此独立与合作的自由关系,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西方人性格里面的独立与个体精神,这种独立就形成了人人都可以说了算的状况,于是很多事情靠投票决定,民主的雏形形成了。雅典10天一次的议事会每次有五百人参加,集体对于他们来说是合作的产物,不是形式主义的关系维持。城邦国家的建立,让人在个体与集体中找到很好的平衡,相比之下,中国的家族群落,让人的思想意识从一开始就要求你忽视个性,收缩自我,有“大家大我“的觉悟,所以中国人喜欢动不动就拿“集体利益”说事。
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
一个王朝的倾覆,势必会带来一段时间的混乱。清朝的主子及他们的奴才们还没明白总统与皇帝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就匆匆的离别了紫禁城,中国的军阀割据及抗日战争又在这片土地上燃烧,孙中山以“民族、民主、民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他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袁世凯竟倒行逆施,来了一场复辟。李大钊、陈独秀以马克思思想为武器,决心要建立中国的共产国际。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均来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反帝制的思想运动,让“民主”这一思想在中国扎下了根。
抗日战争过后的再次内战,确定了新中国的领导人以及领导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思想让中国领导人以苏联为大哥,打败了美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认为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能够难道他们,于是封闭的“三年赶英、五年赶美”、、“亩产三万六”、“全民大炼钢”、“人民公社”的大跃进运动来了,着实热闹,然而全国所有归全民所有、企业盈亏无人担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在一开始的整体调控下表现出了一定的适用性之后,立马就漏洞百出,人民生活质量跌破生存底线,于是三年自然灾害了,此时的经济基础不仅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基础本身都难以支撑,在此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更是机制呆板、思想教条、行为程式。用意识形态决定生产效率,就是违反规律、违反科学。喊口号若能喊得出产品质量,“中国制造”又岂能是今日之境地,违反规律的一定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经济问题,全部都由政府说了算,致使全中国的人都穿统一款式、统一材质、统一颜色的衣服。而政府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对全国所有情况都清清楚楚。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部门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社会文明整体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地步。
伟大的邓小平在1978年终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又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接着高考恢复,知识分子从牛棚中爬出,拍拍身上的尘土,满眼疑惑。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公的这段话,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认识,让听者感觉恍然大悟。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质疑,在抗拒,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丝毫没有放慢。
晚年的邓小平一直在思索未来中国的命运。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成为载入中国史册的时刻,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八个字,让全国人民感觉精神抖擞,那是一个到处都充满机会的年代。国家博物馆至今都在一遍又一遍的播放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老人家再次掷地有声的说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诞生了,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指导思想,让聪明中国人搞起经济来是如虎添翼,改革开放三十年,山河大地一天一个样子,国人思想一年一个变化。邓小平所打破的这些上层建筑的牢笼,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此时的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主要用的是“放”,这种“放”是建立在新中国太“收”的基础之上,因为已经收得太死,所以一放就活。相比之下,唐朝初期的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更多的是“包容”,是国人自信、国富民强的顺势而为。
地大物博加人口稠密的中国,首先廉价的便是土地与自然环境、还有不可想象的廉价劳动力,经济特区的大量工厂,让当地政府炫耀了政绩、让国家引进了技术、让中国的青年有了零花钱,当然,更多的是让工厂老板们赚取了利润,无论后来我们怎么看这些冒着黑烟、流着毒水的工厂,一开始它们确实让所有人共赢,输的是输在多年以后。流水线让工人有了栖身之地,大型工厂的不断进驻,产品的快速更新,科技的超级转化,交通的日趋便利,让经济发展成为近三十年来的主题,唯一的主题,三十年后,中国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大宋,农民种田地不但不再征税,反而还有补贴。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源于工商业,土地再也约束不了人,当然,很多耕地若无人打理,很快便会荒芜,人离土地越来越远。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到同世界国家商业来往的状态,这对中国商人来说,意味着需要一次较为彻底的思维转变及商业转型,需要中国商人集体将自身提到新的高度,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对手都在靠近,而围墙你还得先推倒。
李鸿章曾说清朝末期的境遇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今天回望清朝,中国这将近两百年的历程,每时每刻都处在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经济基础在近几十年彻底的改变,在这种经济基础的剧烈变化之上,国门又在短时间内仓促大开,这就会形成薄弱经济基础所建立的脆弱上层建筑不堪一击,经济基础的薄弱让外来的上层建筑很快就占据了主流,于是汹涌的外来资本裹挟着的外来文化,很快就将中国现有上层建筑踩在脚下。本土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外来上层建筑充分混合下的我们,自然就表现得一惊一乍,极不稳定,精神状态总在自负与自卑之间剧烈的窜动。经济基础的薄弱让人在面对外来经济基础的雄厚时,会怀疑自己的上层建筑,就好像近现代流过洋的中国人回国之后,总是喜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以一种俯视的角度大加指责。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基础一直在快速发展,但是一开始随着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并非土生土长,这种不匹配、不协调让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脆弱、不规则、以及不可捉摸。在这种不协调下,就形成了中国的经济基础越丰厚,中国人就对现有上层建筑越不满,上层建筑越表现出混乱,中国人就对现有经济基础表示怀疑、加以指责的躁动境况。我们活得真诡异。
(未完,待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