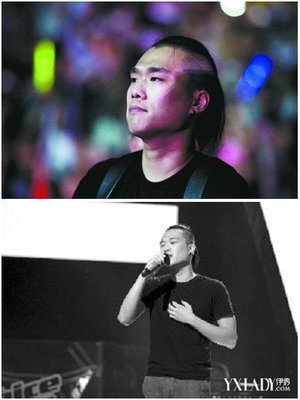因为是讲课提纲,未经本人许可,请勿直接使用、引用。
2012年4月6日
第五讲 在不可能性中给予宽恕
——德里达关于“宽恕”的思想解读
1,德里达的伦理学转向:
德里达后期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学转向,但德里达的伦理学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是混合了政治、哲学与宗教意义的伦理学。当然,如果处理解构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主题依然是一个难题,西蒙·克里齐里在《解构主义的伦理学》一书却认为,解构主义是伦理学,但这并不意味有一种解构主义的伦理学,伦理学不能源自解构主义。[1]更为明晰的做法则是标示出解构主义的伦理学转向。理查德·克尔尼就用《德里达的伦理转向》来描述德里达思想演化中的伦理学倾向。[2]在我看来,这样来理解解构主义或德里达的伦理学或政治学倾向都显得过于朴素和简单,如何从德里达的思想深处,他的立场和解构的出发点来理解,就可以看出那种解构思想是如何深深地浸含着伦理学内容,也许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解构浸含在伦理学的品质中。我们可以在德里达后期所谈论的一系列主题,宽恕和正义、法律与暴力、友爱的政治、死亡的礼物、动物性以及反对死刑等等,都可以看到那种伦理政治,这是一种新型的综合的人文学,也是后现代思想最具有建设性的未来面向。在这里,哲学、文学、政治批评、伦理学、乃至于宗教都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构是一种伦理政治;解构的本性就是一种伦理学。德里达讨论的“宽恕”主题,就可以看成是这种伦理政治的充分表达。
2001年9月4日,德里达到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的讲演。这个讲演不出所料,能够接受他的观点的人寥寥可数,现场大多数人表示了迷惑不解,甚至少不了还有表示极度怀疑的听众。[3]上世纪90年代末,德里达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开讲“宽恕”,这个概念居然讲了三年,虽然听者云集,但真能明白或接受他的观点的人比过去不会太多。德里达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谈论宽恕,他只是在哲学的纯粹意义上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贯穿着他的解构意图。他要谈论的恰恰是宽恕的不可能性,正因为此,宽恕才是可能的。这样的逻辑关系不能在辩证法的框架中来考虑,只有进入到德里达的思路中,才能得到理解。对于德里达来说,“宽恕”是一个哲学的、伦理学的,也是一个宗教学的问题(德里达对宽恕的讨论无疑与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有关),很显然,它又是被放在历史中加以阐释。德里达直接针对的对象,是波兰裔法国人杨凯列维奇关于“决不宽恕”的论述。德里达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当然也考虑了历史的和当时的国际政治的背景。宽恕不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策略问题,在德里达的探讨中,这是一个哲学的和伦理学的问题。而德里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联系起来考察。德里达试图更深入和更明显地切入到基督教传统和犹太教背景中去,这与列维纳斯后来转向关注《塔木德》也有相近之处。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中确实包含着伦理学的内容,他关于“宽恕”、死亡、馈赠以及友爱的政治等问题的阐释,都展示了解构思想独特的伦理学空间。当然,对于德里达的解构运思来说,并不会囿于单纯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态度总是与哲学、政治学结合在一起,但伦理学态度则构成了德里达后期思想的一种价值关怀,或者说一种价值导向。
德里达对“宽恕”概念的探讨尽管立足于很纯粹的哲学伦理学的立场,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999年12月,在接受法国《论坛报》的记者采访时,他就谈到,现在宽恕及其概念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指出,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舞台上频繁出现悔过、坦白、宽恕或道歉场面,要求宽恕的不仅有个人,而且还有团体、行会、教会神职代表,君主和国家首脑。这从二次大战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中国及东亚与日本的历史;南非的种族冲突;冷战后科索沃冲突……等等,都可看到这些要求道歉、悔罪和宽恕的背景。德里达说,他们用“亚伯拉罕式”的语言要求宽恕,这种语言已经成为法律、政治、经济或外交的国际方言,同时也是这一国际化的动因和症状。他说,这些悔过、要求宽恕之场面的激增可能宣告了记忆的紧急状况:即必须转向过去;这种回忆、自我起诉、悔过、出庭受审的行为应该被提交到司法和民族一国家的法庭以外去审视。这些现象和事件本身就是国际社会在某时根据其历史某一面而制造和准许的。无论真诚与否,这些场面上演着深切的宽恕,一个笼罩着我们的巨大的悔恨剧。[4]
初读德里达的这些说法,很容易认为他并不赞许这此曾经遭受创伤的民族—国家要求的“道歉”,通过那些犯罪国的悔过和受审,从而表达出他们的宽恕。德里达确实对这种做法无疑包含着一些怀疑,但他本人是犹太人,二次大战期间受到过排犹主义的迫害;他支持南非曼德拉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他和众多的反抗暴政的弱势群体社团坚定站在一起。他当然不会为那些犯罪民族、国家或集团辩护,德里达要做的是更深层的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思考,他既看到宽恕的不可能性,又力图去探讨宽恕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2,宽恕的二条公理:
在《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一文中,德里达对宽恕的阐发针对杨凯列维奇的观点。这就是杨氏出版过二本关于“宽恕”的书,一本题为《宽恕》,其后出版的名为《不受时效约束》。杨氏对德国纳粹在二战时期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表示了决不妥协的态度,他把赎罪、拯救、救赎和调解与宽恕联系起来,他认为,宽恕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实行宽恕。不应该宽恕。应该不宽恕。“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已经死亡”。德里达根据杨凯列维奇的观点,归结出二条关于宽恕的公理:其一,宽恕只有在被要求时,明确或暗含地被要求时才能同意;其二,当罪恶过于严重,当它超过了罪恶的极端的或人类的界限,那就不再谈得上宽恕。[5]
德里达对杨凯列维奇的批驳显示了他少有的明确风格,而且是以一种论战性的方式展开他的观点。紧接着对杨凯列维奇的归纳,他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
如果存在宽恕,它就只应该并只能够宽恕不可宽恕、不可补救者,即做不可能之事。宽恕可宽恕、可补救、可原谅,这是永远可能做的,这不是宽恕。[6]
看上去德里达与杨凯列维奇的观点有相近之处:他们都认为宽恕是不可能的。但杨认为“宽恕”是存在的,宽恕有一种真实意义的,但宽恕具有时效性,用在对德国纳粹的宽恕上,就不可能,就不应该。但德里达却是从根本上解构宽恕,他要阐明的是宽恕不可能存在,从来就没有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宽恕。有条件有目的宽恕,合情理的宽恕,都不是宽恕。宽恕应该是无条件的无目的超越历史时效的。但这样的宽恕是不可能的,因而宽恕根本就不存在。宽恕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对于不可能的宽恕的宽恕,在不可能性给予宽恕,这才是宽恕。不可能的宽恕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在理性和逻辑的结构中无法想象的事,无法实践的事情。当然,德里达的观点并非真的这么简明扼要,他依然要运用他的解构策略,运用他独特的推论方式,他不把问题搞复杂,搞得难于理解他当然不会罢休。德里达总是把问题推到极端,从那里开始思考。那是一种临界状态,在这样的临界线上,他总是能使问题暴露得更具有多面性。当然,这也就与简单明晰绝缘。因此,也就需要我们进入到德里达的具体思路中去仔细分辨他的观点。
3,解构不可宽恕的公理:从赠予与赦免开始
德里达的反驳从针对两条公理入手,其一,宽恕“被要求”,也就是其主体的确认是不可能的。其二,宽恕的时效性,它受到前提的限制,例如,当罪恶过大时,就不能宽恕。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总是发生在历史性的语境中,他既清除历史的特定性,又利用历史特定性。在起源的意义上,在事物存在的根基意义上,他清除历史的特定性,那些历史的起源,那些给定的优先性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可以解构的。另一方面,他在具体的分析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越过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区域,暴露这其中掩盖的历史构成谱系,从而使历史无法建构。在处理“宽恕”这一问题时,德里达一直在关注宽恕的历史时效性与非时效性,在这种结构中,使主体消解。宽恕的主体无法完成一种历史时效的建构,从而使主体失效。
针对第一条公理,德里达实际上在开篇分辨“赠予”与“宽恕”时就触及到这一问题。实际上,人们并不是因为有罪才请求宽恕,因为宽恕随时发生,请求宽恕也随时发生。赠予就与宽恕密切相关。人们不是因为赠予而要求别人感恩,相反,是因为我的赠予,我不能时刻赠予,我不能充分足够地赠予而请求对方宽恕。在这一意义上,宽恕与赠予构成了生活最基本的含义。不存在没有宽恕的给予,也不存在没有给予的宽恕。德里达说道:“人们应该先验地为给予本身要求宽恕,应该让别人宽恕他的给予,宽恕给予的至高权力或对给予的至高权力的欲望。”[7]德里达显然是要把事情推到极致,宽恕事先就占据了一种优势地位,一种居高临下的对权力控制的肯定。这种宽恕的优势、宽恕的权力是谁给予的呢?谁天然地拥有这样的权力呢?追问到这一步,这就是在触及基督教的人的原罪的思想。人生而平等,人都是有罪的,凭什么你就可以宽恕我?凭什么我就要得到你的宽恕?在宽恕对方时,势必包含着请求对方宽恕我的宽恕。
对于德里达来说,他并不是要刻意抹去宽恕包含的历史与主体的含义,他总是事先把事情推到极致来思考,给予事情以绝对抽象的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宽恕作为一种行为,总是有缘由,而这种缘由本身是历史性的,它有历史给定的意义。宽恕的主体与被宽恕的主体在历史中不可能都是同一的。德里达当然不会不注意到这点。但他在伦理的和哲学的意义上来看问题,则要追究到事情的根本出发点。赠予是一种在非历史化的语境中来思考的行为,同样,“赦免”也被德里达放到同样的语境中来思考。赦免也不是在被请求的前提下发出的行为,那也是至高权力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中,“赦免”无疑有其意义,它毕竟表达了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宽容。但德里达去除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抽象的意义来看,“赦免”表示了一种王权的恩泽,这种至高无上的来自王权的恩泽把宽恕的权力置于各种法则之上。德里达认为,在宽恕和恩泽之间,有着一种从深不可测的历史来到我们中间的类似性。“那是一种宗教的、唯灵的、政治学、神学—政治的历史,它应该是我们反思的中心问题。”[8]赦免使司法公正受到威胁,它使司法程序看得极其重要的那些规则变得微妙和模棱两可。德里达告诫说,我们应该不断思考的正是这种例外的逻辑,作为绝对例外的宽恕的逻辑,即无限例外的逻辑。德里达揭示出,至高权利有可能在最高层次上成为不公正的活动,没有什么比赦免更不公正了。德里达这里质疑的与其说是赦免,不如说是至高的王权。赦免确实包含了宽恕,但却是特殊的宽恕,是被窃取、垄断和劫持的宽恕,这是专有的宽恕。德里达这里几乎要对“宽恕”加入历史与阶级意识,德里达当然不会用左派的陈辞滥调,他只在事物的极限处思考其不可能性。赦免与其说是宽恕,不如说是王权的一种象征仪式,它不是用于恩泽罪犯,而是强调王权的威严。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它毫无仁慈的意义,在历史上的王权暴政统治下,司法腐败是司空见惯的事,赦免反倒是一个矫正王权暴政和司法残酷的一个偶然的机遇和措施。
把“被请求”作为宽恕的公理显然是不充分的,宽恕从来就不是被请求的结果,宽恕只是单方面的给予、赠予或赦免。但是主体何以有这样的资格和权力被请求呢?德里达反思宽恕所构成的双方关系,宽恕被理解为是一种给予和请求的双方关系,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真正蒙受罪恶伤害的主体并不存在,例如,在纳粹集中营死去的那些犹太人,谁能代表他们给予宽恕呢?德里达指出:“人们永远不应该以受害者名义宽恕,特别是如果受害者在宽恕舞台上彻底缺席,比如他已死亡的时候。人们不能向活着的人们、向幸存者们为受害者们为之受害的罪恶请求宽恕。”[9]
4,关于不可宽恕性与请求:
杨凯列维奇强调的是不可宽恕性,凡是请求宽恕的事件,都是不可宽恕的。在面对纳粹集中营屠杀犹太人这一事件而言,这是不可宽恕的。而德里达阐述的是宽恕的不可能性,只有不可能被宽恕的事件请求宽恕才叫宽恕。德里达使问题变得更加绝对,同时也使问题更为具体,那就是谁有这样说话的权力,那只有死者本人。别人无法代替给予宽恕。如此看来,所有的言说,要给予宽恕或不给予宽恕都变得不可能。杨氏认为,凡有不可补救的地方,就有不可宽恕,而凡有不可宽恕发生之处,宽恕就变得不可能。德里达带有反讽地评价道:这就是宽恕和宽恕历史的终结,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已经死亡。也就是说,死亡是不可补赎的,受难的犹太人在集中营中已经死去,他们的生命损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补救,他们也无法给予请求宽恕的人以宽恕,也没有人能代表他们要求德国人被宽恕。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不会放过把杨凯列维奇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杨凯列维奇既然已经说了宽恕的不可补救性,而且宽恕已经“在集中营中死亡”,但他又长期在等待一个请求宽恕的词。德里达指出,重要的不是这个词被说出,而是要被“意谓”。既然宽恕不可能,不应该宽恕,那么请求有什么意义呢?但这样的请求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请求宽恕”可以被意味,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赎罪、后悔、忏悔、对自我的指控、犯罪主体捶胸顿足的承认罪行等等。这个“意谓”也就是请求宽恕这个行为被历史定义,主客体的关系被建立,历史被建立,意谓就是一个历史意义的意谓。德里达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杨凯列维奇要求的宽恕不过是等待德国人的自我悔罪/羞辱仪式,并不是真的要等待一个请求,然后给予宽恕。
5,宽恕的异质性:
在德里达看来,宽恕的手段如果存在的话,就应该永远处在不定的两可的状态,宽恕在知识、理论上的决定性判断,没有适宜它的范围,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异质性的!宽恕是不可定义的,也就是说,宽恕是延异,是历史死亡的替补。
德里达委婉地提到策兰的诗《托特瑙山》[10],德里达认为,诗就是赠予,也就是宽恕。也许在德里达的观念中,宽恕可能的形式,只有诗,只有文字,文字的赠予是没有前提也没有时效的。也只有以诗性对事情的领悟才可能达成宽恕。当然,德里达这里谈策兰的诗显然是有直接目的,因为策兰的诗并没有表示对海德格尔的不满,言下之意,策兰似乎宽恕了海氏。这显然是德里达谈论宽恕绕不过去的一个障碍,如何面对海德格尔的纳粹历史,这是解构的伦理学最大的难题。1987年,西班牙人法里亚斯出版了《海德格尔与纳粹》,比利时人奥特温·德格雷夫发掘出保罗·德曼在二战时期为亲纳粹的报纸写过反犹文章,解构主义因为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渊源,因为耶鲁学派缘故,海德格尔与德曼的声誉仿佛与解构主义的声誉牢牢捆绑在一起。解构主义在这一年遭遇了强烈的攻击,但德里达挺身而出,他在1987年出版了两本谈论海德格尔的书(《论精神:海德格尔及其问题》,《心灵:另一个发明》)[11],1988年出版了《多义的记忆》。因为他的犹太人的背景,只有他可以站出来为这两个人言说。在这里,在谈论对德国人的宽恕问题上,德里达无法回避海德格尔。但他也无法直接为海德格尔辩护,德里达巧妙地引用了策兰的诗,而且在这里引述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经常连结思考和感谢而被认识。德里达说:“赠予与宽恕已经或没有发生,已经发生又被消抹,被带走,而我竟然没有作决定。”策兰的这首诗,始终让人们阅读、获取到——就像赠予和宽恕本身——一种在可能成为诗人的各种主题或希望落空的主题之前的赠予和宽恕。[12]
6,宽恕变成悼念:
在杨凯列维奇的阐述中,宽恕只能寄望于后代,新一代将使宽恕成为可能。但他同时认为这种宽恕是幻想和欺骗,不是真正的宽恕,而是症状,是哀悼活动、治疗遗忘、时间流逝的症状。德里达指出,宽恕和历史,和历史的连续过程联系在一起,即使宽恕在未来,在未来的一代那里实现,宽恕也不可能真正发生。因为这样的宽恕始终是虚幻的,不合法的,它与丑闻、暧昧的遗忘混淆在一起。在德里达看来,遗忘不是真正的宽恕,对罪恶记忆的死结依然存放在历史中。这只是一种悼念,是对历史终结的悼念,更严重的是,同时也是对宽恕的悼念——变成宽恕本身的悼念活动——宽恕把宽恕变成它自己的悼念。德里达告诫说:
“在历史的不间断的基础上,在毋宁说是无限的创作的深渊中,历史在不断继续。那创伤,在创伤形成的过程中,将始终并应该总是开放而又不可缝合的创伤。无论如何,这个夸张、疑难和悖论的领域,我们在对于宽恕的反思中应该经常对之加以关注并从中得到启发”。[13]

7,无条件的宽恕与不可能的宽恕:
德里达不能同意杨凯列维奇对宽恕设定的前提条件,也不同意他把宽恕寄望于未来的观点,德里达提出真正的宽恕就是无条件的宽恕,无条件的宽恕就是脱离了悔罪和宽恕请求的绝对无条件的宽恕。他说道:
如果存在宽恕的话,那只存在对“不可宽恕”的宽恕。因此,如果宽恕存在的话,它不是可能的,它并不作为可能而存在,它只有在脱离可能的规律之外、在被不可能化并无限忍受作为不可能的不—可能才存在,这就是它与赠与的共同点所在。……宽恕就如同不可能的赠与的不可能的真理。[14]
德里达的根本的观点在于,宽恕是对“不可能的宽恕”的无条件宽恕,如果是可能的宽恕,如果是有条件的宽恕,那就不是宽恕,那就是在交换原则下的算计,那是对宽恕的腐蚀。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来看,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履行的宽恕,都不是真正的宽恕,那只是一项悼念活动,同时也是对宽恕的悼念,也就是说,这样的宽恕实际不是宽恕,是宽恕的死亡。无条件的宽恕就是不要任何附加条件,它是一项赠与,而这样的赠与,也是对宽恕的请求。
8,为着正义的宽恕:
德里达最后提出:“我应该请求宽恕——为的是正义”。[15]尽管德里达是就自己的行为而言,并且他对正义还是作了更为复杂的表述,“正义”也总是包含可能不正义的风险,但德里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为了正义,为了成为正义的(事实)而要求宽恕。无条件的宽恕只有在正义的名义下进行,也应该在正义名义下的进行,在正义名义下也应该宽恕。
尽管德里达执着于对“宽恕”进行纯粹哲学和伦理学的探讨,在这一意义上,他的见解是独到而深刻的。但德里达的伦理学也具有现实的指向性,这与德里达过去的解构理论大相径庭,“宽恕”的阐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德里达反对宽恕的请求悔罪仪式,反对宽恕被国际政治利用,反对“宽恕”被历史化并以延宕的形式存留下去。“纯粹宽恕”在德里达的阐述中具有纯粹哲学的意味,甚至带有宗教的意识,带有没有宗教的宗教性的韵味。按照德里达的解释,那是来自基督教、犹太教甚至伊斯兰教的传统。它是一种宗教经验,是一种信仰和教义启示下的经验。这种经验不能被世俗化,也不能被现代国际政治所理解和实践。德里达对“宽恕”的设定也明确拒绝其现实实践性品格,他并不指望他的“宽恕”理论具有现实可行性。我们可以说现实并不都是正确的,但理论的意义还是要在实践的可能性中来理解和获得力量。要求悔罪、要求道歉,这对于曾经蒙受过创伤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来说,都是合理的,这些行为和仪式本身既是犯罪主体的悔改的证明,也是杜绝罪行重演的一种努力。你不能指望一个犯罪主体连道歉和认错都不愿意,如何保证他不再犯类似的罪行。如果犯罪主体毫无忏悔和悔改的表示,就无条件地宽恕对方,这样的宽恕只能说是愚蠢的自欺欺人。德里达所说的纯粹的宽恕并不具有实践意义,它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就这点,德里达反复强调过,他的宽恕概念要阐明的就是不可能性。德里达把那些国际间的争端排除出宽恕领域,他认为这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宽恕。就在那次北京大学举行的讲演中,德里达也有谈到日本与中国在二战结下的仇隙。纯粹的宽恕显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
9,中国与日本的经验:
日本在二次战后并没有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的领土,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仅仅南京大屠杀就杀死中国人三十多万。日本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这样的罪行,而且凭什么日本天皇就不能向中国人民道歉?日本对中国犯下这样的罪行,仅仅是要求日本的政客和天皇做一下道歉的姿势,表示一种态度就有伤日本天皇的尊严?那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被无辜地杀戮,这样的生命就没有尊严?就不能得到尊重?这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更不能同意的怪事。
确实,面对历史与现实经验,“纯粹宽恕”并不仅是与现实无关,问题在于,它与现实经验相违背。实际上,不能把“和解”看成是与宽恕无关,宽恕也并不是在极限处才真正发生或存在,并不是只有纯粹的宽恕才有意义。宽恕可以有现实性,可以在历史的延续中有序地进行,直到淡化和遗忘发生。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宽恕需要有实践,需要有国际性的仪式、运动,没有这些,宽恕不可能自发地发生。中国人民近年的行动,实际上是希望解开历史死结,希望了却历史恩怨,希望通过和解,通过在场的仪式埋葬历史,清除历史记忆。事实上,中国人民已经宽恕了日本人,几乎是无条件的宽恕。但日本的政客和媒体显然在这方面做得很差。近年来中国民间确实有些抗议行为,也有向日本提出赔偿的请求。这些行动与日本对中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管如何,这些历史不能被轻易地丢弃,它可以通过和解淡化和遗忘,但不能被廉价丢弃。因为日本并未真正认识到他的历史罪恶。日本的右翼势力还相当强大,军国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日本的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郞就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按政客的说法,是为安抚那些右翼的议员和选民。就此而言,就说明日本并没有认识到二战犯下的罪行,也没有把中国人民的感情当一回事。2004年,足球场上的球迷对日本球员有过不礼貌的行为,这本来不是一件多大的事,但日本的媒体却大肆渲染中国的反日倾向,把中国威胁论夸大到耸人听闻的地步。这种习惯势力左右下,日本当然不会向中国请求宽恕,也不会发自内心真诚地悔罪。中国又如何做到“无条件的宽恕”呢?
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以及她的人民可以轻易地放弃历史,遗忘历史。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记住历史,为的是正义,为的是反对不正义,杜绝不正义的重复发生。正义不会因为无条件而自然产生;不正义也不会因为无条件而消失。正义是什么?正义在哪里?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正义不能被具体化,也不能被现实化和实践化,但是,正义之所以具有弥赛亚性,它具有期待的来临,那就说明它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它可以在人类的共识基础上被理解,它总是可以在相对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被运用和被援引。尽管德里达所说的宽恕具有其纯粹的宗教或伦理学意义,但宽恕也应该具有现实实践性品格,也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显灵,并完成其历史真身。
10,宽恕的补充思考:
当然,要把德里达的思想颠倒回去是容易的。他对宽恕的理解,纯粹性、无条件性、非主体化、非仪式化、非政治化、非历史化……等等,完全可以颠倒回去。但问题在于,德里达的宽恕概念是建立在哲学和伦理学层面上的解构策略,其现实之不可能性德里达也已经说明,在我们现实经验中也不难理解这一点。但德里达对宽恕的阐释在学理上确实具有独到之处,有其值得深思的地方。而且他作为犹太人,直接冲击犹太人最难逾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问题,面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问题来思考,他敢于超过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去做纯粹的哲学思考,去寻求更为宽广的人类经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勇气的行为。他发展了列维纳斯的“他者的伦理学”,并且在新的国际政治的语境中提出他的颇富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很显然,他者、敌人,这都具有某种类同性,正如历史不具有本质性一样,他者、敌人也不具有本质性,他们只能历史地理解,在变异的历史中理解。宽恕的不可能性就在于它只能发生在不可能处,只有不可能的宽恕才是宽恕。德里达实际上还是倾向于去尝试做出不可能宽恕的举动。德里达后来谈到“友爱的政治”时,对施米特的朋友/敌人的政治哲学做出他的阐述,可以看出德里达的伦理思想更明确地表达出政治学的含义。
实际上,对于宽恕更为明确的含义,或者更具体的现实指向性,德里达的老师列维纳斯早在1963年就对杨凯列维奇有过回应。1963年的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犹太人学者年会上(那次年会讨论“宽恕”问题),列维纳斯就针对杨凯列维奇提出的要把杀人犯的后代钉在岩石上的说法,列维纳斯说,《塔木德》教导我们,不能强迫那些要求同等报复的公正者给予宽恕,它还教导我们,以色列不会对其他人的这种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提出异议。但是,《塔木德》尤其教导我们,如果以色列承认这种权利,不要为自己要求这种权利,也教导我们做个以色列人,就是不提这种要求。列维纳斯说,谦恭加上正义感和无功利的慈善行动还不足于做一个犹太人,公正本身必须已经与慈善交融——它是指向着承受“律法”严格性者靠近的这种慈悲特殊形式,这才是犹太人。列维纳斯写道:“在人类状况和正义本身晦暗的景象之后还存在的东西,高于理性秩序(或者说仅仅秩序本身)固有的残忍的东西,就是这种妇女、这位母亲、这位利斯巴·巴特·爱亚的形象,她为混杂在其他尸体中的自己的儿子们守灵达六个月之久,不让这些遗体遭受飞禽走兽的损害。他们是人和上帝铁面无私的牺牲品。在为不朽的原则流了那么多的血泪之后,留下的是个人的牺牲,在正义的辩证活力和矛盾转化当中,这种牺牲毫不犹豫地找出了一条端正而可靠的道路。”[16]
德里达关于“宽恕”的思想无疑也受了乃师列维纳斯的影响,他的观点和立场与列维纳斯相近,只是他的哲学辨识使他原本清晰的立场变得难以捉摸。实际上,在2001年与户迪内斯库对话时,他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宽恕可能性的思想。尽管真正的宽恕是无条件的和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中就放弃宽恕的努力。他指出,宽恕的概念包括了一些超出人类能力的因素。但不能把人类所不能及的事情都由上帝去做。无条件的宽恕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宽恕那些不容饶恕的行为是一种不可能的宽恕。但宽恕尽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宽恕那些不容宽恕的行为。“因此,宽恕那些不容宽恕的行为是人类理智的升华,或至少是将理智的原则具体化,这是一种人类心胸宽广的标志。宽恕就意味着自我超越。也许有人认为宽恕别人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不相信宽恕会真的存在。但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正是宽恕的可贵之处。如果人们不停地讲宽恕,并理解宽恕的含义,那就等于实现了人类能力之外的壮举。”[17]这是德里达的理想,还是天真?但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值得深思的观点。
[1]参见:西蒙·克里奇里:《解构主义的伦理学》(Simon Crichley,The Ethics of Deconstruction, Oxford: Blackwell,1992)。
[2]“Derrida’s Ethical RE-Turn” in :Working Through Derrida, Ed. Gary Madison,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8-51.
[3]本章节讨论德里达的这篇讲演依据的是杜小真和张宁编的《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收入的译稿,显然,德里达在北大的讲演不可能照这么长的稿子演讲,为了讨论的更全面,我在这里依据翻译稿。根据座谈会纪要,中国的学者还表示出相当的“宽容”,提问也平和学理化。座中一位美国人的提问显得情绪激动,他问道:如果“某人钟爱他的孙女们,但你强奸了他的一个孙女,并且还想强奸另外三个,那这个人他是否能够并且完全宽恕你呢?”(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4]德里达这次访谈刊载于1999年12月的法国《论坛报》月刊,中文稿转引自“中国学术城”网站,上网日期,2001年6月7日。
[5]参见:德里达:《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6]同上书,第14页。
[7]同上书,第4页。
[8]同上书,第18页。
[9]同上书,第19页。
[10]策兰曾经访问过海德格尔,他写了一首题为《托特瑙山》的诗,人们把这首诗读解为表达了策兰对海德格尔始终没有说出“道歉”的话而表示出的失望。德里达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策兰表达的是赠予和宽恕。
[11]De l'esprit: Heidegger et laquestion, Collection La Philosophie en effet, Paris: Galilée,1987. Psyché: Inventions de l'autre, Collection La Philosophieen effet, Paris: Galilée, 1987.
[12]同注40,参见第24—25页。
[13]同上书,第30页。
[14]同上书,第38页。
[15]同上书,第39页。
[16]参见: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37页。
[17]参见英文版:Elisabeth Roudinesco, ForWhat Tomorrow: A Dialogue, trans., Jeff Fort,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2004, pp. 164-5。
 爱华网
爱华网